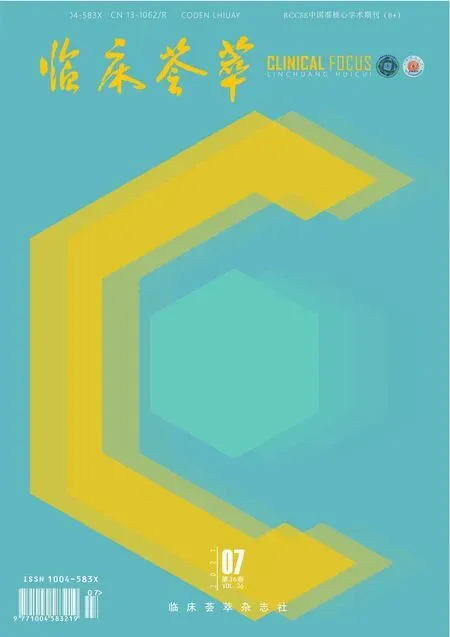不同劑量硫酸氫氯吡格雷對腦梗死患者血流動力學指標及血清miR-191、miR-18a水平的影響
陳禮龍,劉務朝,司秋艷,張建平,程 榮,吳 權
(1.上海市金山區亭林醫院 急診科,上海 201508; 2.上海市同濟醫院 急診科,上海 201508;3.上海市金山區山陽鎮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上海 201508)
腦梗死是因腦供血動脈閉塞或狹窄,導致腦組織供血不足而壞死的嚴重疾病,其致殘率、病死率居高不下,嚴重威脅患者的健康和生命。主要采用抗血小板、擴張血管等藥物保守治療。硫酸氫氯吡格雷是應用較多的抗血小板藥,能夠特異性下調二磷酸腺苷(ADP)與受體的結合,從而抑制血小板聚集,改善腦組織血流灌注[1]。但目前臨床對于硫酸氫氯吡格雷不同劑量的治療效果尚存在爭議。微RNAs(miRs)是機體組織與血液中的一類單鏈RNA,具有調控基因轉錄的重要功能,在多種疾病中表達異常[2-3]。Du等[4]研究報道,miR-191可影響神經組織細胞活力與凋亡。有研究報道,miR-18a可調節血管生成過程[5]。兩者均可作為腦梗死的診療靶標[4-5]。為進一步明確硫酸氫氯吡格雷的臨床療效,本研究在觀察常規血流動力學指標的同時,采用miR-191、miR-18a作為療效評估指標,比較常規劑量和低劑量硫酸氫氯吡格雷的療效,現總結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病例選擇 選取2018年1月-2020年1月收治的腦梗死患者60例,隨機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每組30例。觀察組男17例(56.7%),女13例(43.3%),年齡50~70歲,平均年齡(57.92±8.69)歲。對照組男18例(60.0%),女12例(40.0%),年齡55~75歲,平均年齡(58.26±8.47)歲。兩組性別、年齡、吸煙史、合并癥、血脂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
1.1.1納入標準 (1)均符合《中國急性缺血性腦卒中診治指南2018》[6]診斷標準,經影像學檢查確診;(2)均接受常規保守治療;(3)均接受硫酸氫氯吡格雷基因學檢測,不存在硫酸氫氯吡格雷抵抗問題。
1.1.2排除標準 (1)合并嚴重肝、腎功能不全;(2)合并惡性腫瘤;(3)合并血液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帕金森病;(4)合并急慢性感染、創傷者;(5)蛛網膜下腔出血、腦出血者;(6)治療期間轉院或死亡者。
1.2方法 兩組均給予常規治療(控制血糖、血壓,降低血脂,改善腦水腫,抗感染,維持電解質平衡,注意保護胃黏膜等),同時密切監測生命體征。在此基礎上,兩組均服用硫酸氫氯吡格雷(深圳信立泰藥業公司,國藥準字:H20000542),觀察組給予常規劑量(75 mg/次,1次/d);對照組給予低劑量(50 mg/次,1次/d)。兩組均治療28 d后評估療效。
1.3觀察指標
1.3.1血流動力學 采用德國DWL公司的經顱多普勒超聲診斷儀經顳窗探查大腦中動脈血流,觀察指標:收縮期峰值流速(PSV)、舒張末期血流速度(EDV)、平均流速(Vm)、搏動指數(PI)、阻力指數(RI)。
1.3.2miRs檢測 采集空腹靜脈血8 ml,靜置28 min后4 200 r/min離心8 min,分離血清置于-20 ℃冰箱中冷凍,然后采用TRIzol試劑提取樣本總RNA,進行純度、濃度檢測,確定樣本合格后采用逆轉錄試劑盒將總RNA反轉錄為cDNA, 再按照實時熒光定量PCR法的檢測程序進行PCR擴增與檢測,確定miR-191、miR-18a水平。
1.3.3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評分 采用 NIHSS評分評估不同時點間的神經功能狀況,評估項目包括視野、凝視、意識水平、感覺、運動等多個方面,總分0~42分,得分越高,表明患者恢復狀況越差、神經功能缺損越嚴重。

2 結 果
2.1血流動力學指標 兩組治療前血流動力學指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28 d兩組PSV、EDV、Vm均明顯升高,且觀察組高于對照組,PI、RI均比治療前降低,且觀察組低于對照組(均P<0.05),見表1。

表1 兩組血流動力學指標比較
2.2血清miR-191、miR-18a水平 兩組治療前miR-191、miR-18a無明顯差異(P>0.05),治療28 d兩組miR-191比治療前降低,且觀察組低于對照組,兩組miR-18a比治療前升高,且觀察組高于對照組(均P<0.05),見表2。

表2 兩組血清miR-191、miR-18a水平比較
2.3兩組NIHSS評分比較 兩組治療前NIHSS評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3 d、7 d、14 d、28 d兩組NIHSS評分均低于治療前(P<0.05)。兩組NIHSS評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5.424,P=0.009),且在不同時點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7.263,P=0.003)。劑量對NIHSS評分隨時間變化的趨勢有影響(F=4.963,P=0.011),見表3。

表3 兩組NIHSS評分比較分)
2.4不良反應 觀察組肝功能異常與嗜酸性粒細胞增加各2例、胃腸道出血1例,對照組嗜酸性粒細胞增加2例,肝功能異常1例,兩組不良反應發生率(16.7% vs 10.0%)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577,P=0.448)。
3 討 論
腦血管狹窄與血栓形成是腦梗死發病的直接原因。腦血管發生粥樣硬化后,受損的血管壁上黏附血小板,形成白色血栓,進一步誘發血小板聚集,啟動凝血瀑布反應,纖維蛋白迅速與紅細胞結合,形成紅色血栓,導致血流減慢,凝血反應更加嚴重,最終導致管腔完全閉塞,出現梗死且病變部位逐漸擴大。因此,其治療的關鍵是抑制血栓,改善血液黏滯狀態,建立側支循環,恢復血液供應。臨床可通過血流動力學評估血小板聚集性與血流灌注情況,從而判斷治療效果。
本研究結果顯示,治療28 d后兩組PSV、EDV、Vm均明顯升高,PI、RI均比治療前降低,這表明硫酸氫氯吡格雷具有良好的抗血小板聚集、活化作用,能夠明顯提高血流速度,恢復腦組織血流灌注。本研究中治療28 d后觀察組PSV、EDV、Vm以及PI、RI指標的改善程度均優于對照組,表明硫酸氫氯吡格雷的應用劑量對治療效果具有明顯作用,常規劑量用藥有助于提升療效,改善血流動力學指標。硫酸氫氯吡格雷作為噻吩砒啶類衍生物,屬于典型的前體藥物,其本身并無活性,進入人體后由小腸吸收,85%能夠經水解后排出體外,僅15%左右被吸收后進入血液循環,在肝臟細胞色素的參與下形成2-氧基-氯吡格雷,進而繼續發生氧化,成為具有生物活性的硫醇衍生物,與ADP競爭性結合血小板表面ADP受體,抑制血小板聚集[7-8]。由于該藥進入人體后被有效吸收、轉化的比例較低,其血藥濃度必須保持一定水平才能有效競爭性結合ADP受體從而發揮治療作用[9],因此采用常規劑量治療方案有助于提高治療效果。
在腦梗死早期,嚴重局部缺血可對中心病變部位造成不可逆損害,但由于存在側支循環,在缺血半暗帶仍有大量神經元存活,挽救缺血半暗帶是腦梗死臨床治療的關鍵,對于恢復神經功能、改善預后至關重要[10-11]。已有研究表明,高劑量硫酸氫氯吡格雷被人體吸收后,作用于缺血半暗帶,可有效促進該部位新生血管形成,改善側支循環,促進缺血腦組織血流供應,縮小梗死面積,減輕或逆轉缺血損傷[12]。另有研究指出,高劑量硫酸氫氯吡格雷的應用,還有助于減輕炎癥反應,刺激神經元活性,促進腦組織修復[13]。miRs是屬于非編碼單鏈RNA,在信號通路傳導、組織分化、細胞分裂與增殖等一系列生物學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功能性miRs被認為在腦組織缺血期間保護神經細胞與突觸可塑性中發揮重要作用,在創傷性腦損傷[14]、缺血-再灌注損傷[15]以及腦梗死[16]等中樞神經系統病變中表達失調,能準確反映上述疾病的病情變化與預后。Wu等[17]研究指出,miR-191 可與胱硫醚-β-合酶發生相互作用,加重組織再灌注損傷。miR-191在顱腦外傷患者中表達異常,可作為顱腦外傷診治與預后指標[18]。動物實驗發現,腦梗死大鼠接受電針治療后,miR-191表達下調,可提高神經細胞活性,減少神經細胞凋亡,縮小梗死面積,提高神經學評分;而miR-191表達升高則可加重神經細胞損傷,并降低電針治療的神經保護作用[19]。Yang 等[20]研究發現,三七總皂苷等藥物可通過上調miR-18a 水平,促進血管生成,進而改善心肌缺血癥狀。上述研究均證實,miR-191、miR-18a可影響缺血性疾病的進展。本研究結果發現,治療28 d兩組miR-191比治療前降低,且觀察組低于對照組,兩組miR-18a比治療前升高,且觀察組高于對照組,表明常規劑量硫酸氫氯吡格雷有助于調節miR-191、miR-18a水平,對預后產生良好作用。本研究對治療過程中患者神經功能恢復情況進行動態監測,結果顯示,治療3 d、7 d、14 d、28 d兩組NIHSS評分均低于治療前,兩組NIHSS評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且在不同時點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劑量對NIHSS評分隨時間變化的趨勢有影響,進一步證實常規劑量治療方案有助于促進神經功能的恢復,改善患者預后。且兩組不良反應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明常規劑量具有較好的安全性。
綜上,常規劑量硫酸氫氯吡格雷有助于提高腦梗死患者腦血流量,影響功能性miRs的表達,改善神經功能,提高治療效果,且不增加不良反應,值得臨床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