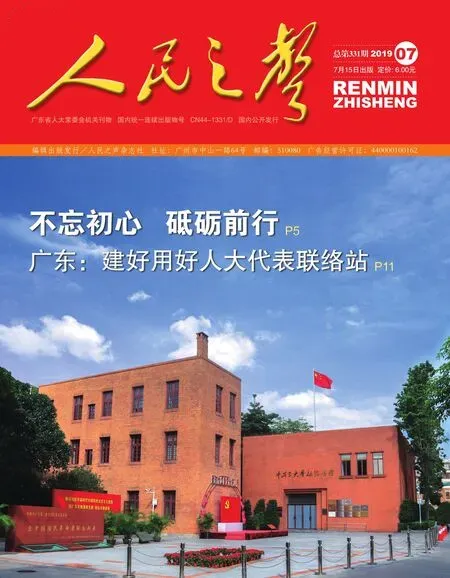代表建議辦理“快準穩”
/ 圖 陳 翊
潮州市潮安區庵埠鎮
電線脫落、大樹傾倒、水管破裂、水渠堵塞、路面破損、交通擁堵……日常生活中會遇到的問題林林總總,有事該找誰?2018年以來,潮安區庵埠鎮的人大代表密切聯系人民群眾,走基層,接地氣,更好履職盡責,助力當地一批民生問題得到解決。
快 急民之所急 迅速行動解民憂
“娘仔溪梅溪與仙溪交界段,下雨天積水嚴重,村民生產生活受到很大影響!需要盡快通知相關部門來退水!”今年4月19日,代表洪祥元發出信息,把梅溪村積水情況反映到庵埠鎮人大微信群里。鎮人大主席鄭衛斌看到后,立即聯系當地農口部門和環管站,加緊對淤塞溪段的應急清理,積水問題在當天得到有效緩解。隨后,鄭衛斌把相關落實情況反饋到群里,代表們倍受鼓舞。
4月10日,陳圖深代表向鎮人大反映,新亨路沒有路燈,給過往群眾夜間出行造成極大不便,希望能盡快解決。當晚,鄭衛斌帶隊前往新亨路察看,確定情況屬實后當即聯系鎮政府反映情況。翌日,鎮人大迅速與鎮規劃辦確定方案,由路燈辦安排人員開始路燈安裝工作。至12日,新亨路700米路段范圍內,38盞路燈已全部安裝完畢,前后僅用了不到3天的時間。
“問題處理好了,去跟反映的群眾們說,他們都說沒想到這么快就能處理好,還說以后發現有什么問題肯定第一時間就來找我。”陳圖深說。
準 問需于群眾 有呼必應暖民心
“雖然有些問題存留已久,加上鎮里財力有限,沒辦法一步到位的,大家也要多到基層問需問計,力求分步破解,給選民們有個交代。”在鎮人大代表的微信聯絡群里,鄭衛斌多次給代表們加油鼓勁。
鎮內“僵尸車”長期占用公共場地、文里村文里小學周邊交通時常堵塞、多個市場建設落后、部分路段路燈年久失修……數個存在已久的“疑難雜癥”,在鎮人大的推動與督辦下層層破解。
經摸查,全鎮存在33輛達到報廢年限的“僵尸車”,今已被強制拖離報廢,鎮區面貌得到提升。
文里小學前亨利北路在交通高峰時段改為單行行駛,并由交警部門派員疏導交通,城管中隊及文里村派員協助維持秩序,交通環境明顯改善。
鎮政府投入資金300多萬元,新建龍坑市場、文里市場,改造提升中心市場、中山市場,市場衛生環境大為改觀,群眾買菜更加便利。
鎮內中山路、萬德路等10多條路段已完成路燈鋪設,其中新安裝305盞,維修139盞,亮化夜間交通環境,保障群眾夜間出行安全。
……
經年沉疴一朝除。鎮人大圍繞黨委中心工作,助力鎮政府推進各項民心工程建設,大大提高群眾生活質量,贏得各方廣泛好評。“去年10月,我們代表到各人大代表活動室述職,有的代表一開始還不好意思,后面是越說越有自信,就是因為有成績,得到群眾認可,所以底氣越來越足。”鄭衛斌說。
穩 代表熱情高 健全機制保長效
隨著一件件民生實事落到實處,工作得到群眾點贊,代表們的履職熱情越發高漲。去年至今,庵埠鎮人大共收到代表建議及群眾反映熱點問題共77份,現已辦結66份,其他建議及熱點問題也已轉達相關部門進行處理。
如何看待這樣的成績單?鄭衛斌認為,關鍵是健全機制。首先是要始終堅持黨的領導,確保正確政治方向。要緊緊圍繞鎮委中心工作,服務全鎮發展大局。其次是要健全主席團成員聯系代表和代表聯系人民群眾的“雙聯系”機制。庵埠鎮通過搭建聯絡平臺,以8個人大代表聯絡室為點,以全鎮163名代表主動走訪群眾為線,織緊織密民情民意網絡。此外,代表述職評議制度、重點建議督辦機制、人大主席團向鎮黨委請示匯報工作制度等多項制度機制,都是鎮人大深化推進基層人大工作的重要方式方法。■

庵埠鎮人大代表調研鎮區破損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