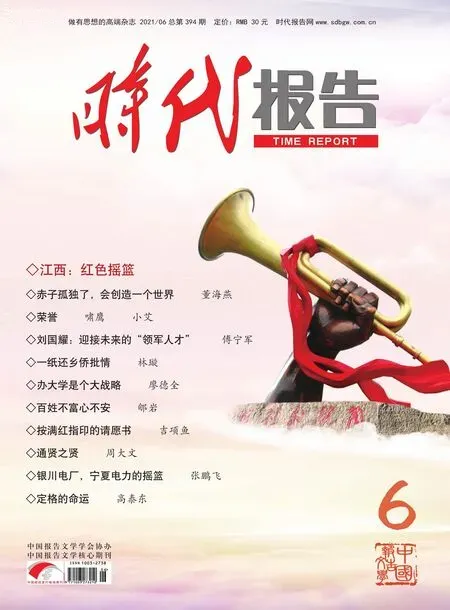朱家澗扶貧紀事
趙永剛


在蒼莽的黃土塬上,朱家澗村只是黃土高原千溝萬壑間一個小小的褶皺。這里山山相連,一條澗河靜靜地流淌,日深年久,群山和澗河擋住了朱家澗人致富的道路。
沒有一個冬天不會遠去,正如沒有一個春天不會到來。在寒冬沉寂過后,精準扶貧猶如一縷春風悄然吹到朱家澗,讓這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朱家澗村的群眾下山出川上樓,開啟了美好新生活。
朱家澗的變遷,只是甘肅省平涼市涇川縣脫貧攻堅工作的一個縮影。
2021年元旦,朱家澗村舉行“移民新村話變遷”新年聯歡活動,這讓朱家澗村的群眾熱血沸騰。他們敲起了威風的鑼鼓,扭起了歡快的秧歌,唱起了特色的民俗小曲,甭提有多高興了!
在活動現場,一個個住上新樓房、種上大棚菜的村民走上舞臺,興奮地講起了他們生活發生的種種變化。
“我們咋老覺得像在做夢!”對于眼前的幸福生活,朱家澗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曾經一方水土難養一方人
人們都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然而,朱家澗村的一方水土,卻難養一方人。
連綿的群山,狹長的澗河,朱家澗村就夾在這個山旮旯里。
關于朱家澗的來歷,原村黨支部書記朱存錄略知一二。他聽老輩人口口相傳,得知自己是明代韓王的后裔。
明代朱氏韓王就藩平涼二百多年,其子嗣長期在平涼繁衍聚居。清朝同治年間,原居住于平涼白沙石灘的朱氏在家族遭遇戰亂,為躲避戰亂,一部分逃難至崆峒區的花所鄉,一部分上塬逃到崆峒區的王寨鄉。后來,戰亂不息,花所這脈只得沿著涇河一路東逃,輾轉就來到了現在的朱家澗。山大溝深,景色秀奇,他們被這世外桃源所吸引,便隱藏于此,落地生根。又因這里有一條緩緩流淌的澗河,索性取名朱家澗。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那個僅停留在溫飽的年月,朱家村也曾風光過。
雖然山地貧瘠,但地廣人稀,只要人勤快,養家糊口基本沒有問題。那個時候,和朱家澗相鄰塬上村子里的女子,都愿意嫁到朱家澗村。
可是,任誰也不能阻擋發展的車輪。進入新世紀,人們開始不為溫飽發愁。
自此,朱家澗便風光不再。
“上山驢馱下坡溜,七梁八坡山套山”,阻擋朱家澗人致富的便是這羊腸子般的山路。
“百十戶人家,稀稀落落分布在十多個山頭上,最南邊的塔山組和最北邊的段家山組相距13里路。”朱存錄說。
吃過的苦,遭過的罪,42歲的朱軍建一輩子也忘不了。
5歲生病的經歷至今都讓朱軍建心有余悸。“1983年,我那時候就5歲多吧,有次發高燒,燒得抽風了。剛好趕上連陰雨,澗河水漲,四五天都出不了門。那次差點要了命啊,等到雨過天晴都是一周之后的事情了,到鎮上的衛生院才把病看好,也就是我命大啊,不然……”
還有一次,他生病許久不見好,求醫無果,最后尋到了一張藥方,可是缺一味無法入藥。加上數天陰雨,父親擅自將自己在山上挖的一味藥加了進去,誰料,就是因為這劑藥,他瞳孔放大,險些失明。
“我9歲就開始擔水了,剛開始擔半桶水,稍微長大點,就要擔多半桶水。”朱軍建頓了頓說。有一次挑水走到半坡,他實在沒有力氣了,就想緩一緩,誰知一個趔趄,桶里的水灑了不說,水桶哐當就滾到溝里了,人也傷得不輕。
說到這里,他眼眶有點濕潤:“往事不敢想啊,這搬了出去,現在的娃娃真的太幸福了,水龍頭一擰,自來水花花淌;背柴拾牛糞都是過去式了,天燃氣直接通到廚房,女人再也不用煙熏火燎地做飯了。”
“為了吃水,當時可真把苦受了。”朱軍建說。1991年,村民朱來銀為了節省時間,不再去河溝擔水,就在自家院子里挖井。挖到井深17米的時候,不小心滑了一腳,直戳戳摔下了井底,落了個渾身是傷。那時候路還不通,都是泥濘土路,等到村民們用擔架抬了2個小時將他送到醫院急救時已經晚了,最終醫院鑒定為腰神經受傷,一級殘疾,從此之后,朱來銀后半輩子只能靠輪椅生活。
1990年,12歲的朱軍建上小學5年級。
村里是一所4年制初小,3間土木結構的教室,窗戶四處漏風,舊報紙糊滿了玻璃。
他說,到了冬天,教室里取暖用土爐子。當壘起土爐子時,每個孩子就會輪流從家里帶柴火生爐子。每逢生爐子的那天,他們就會格外高興,因為生爐子可以多烤一會火,噼里啪啦的爐火烤得渾身舒坦。
五六年級時,朱軍建和同村小孩去臨近的章村小學上學。清晨五六點,雞還沒打鳴,他們就要出門了。十多里的崎嶇山路只得用細碎的小步緩緩前行,中午也沒時間、沒精力回家,在教室里啃冷饃、喝冷水就算是午餐了。
朱軍建說,上初中到了鎮上,需要住校,一周回一次家。住校反而輕松了許多,但是每周末去學校又成了老大難問題。去學校必經一座吊橋,所謂吊橋,其實就是用鐵絲連起來的洋槐椽。人走上去,搖搖晃晃,比水中的浮萍還要輕淺。倘若暈水,往下看一眼,那一定吃不消,更別說過橋了。
朱存錄說,因為村里的教學條件太差,公辦教師大多都不愿意來。漸漸地,就連生源也越來越少,加之一部分戶外遷,到2011年的時候,村上的小學只剩下4個學生。2013年,小學撤并。
如今,對于朱家澗村的孩子來說,崎嶇難行的山路已成為過去。
朱軍建高興地說道:“現在搬到鎮上,中心小學和幼兒園就在安置樓后面,娃娃上學十幾分鐘就到了!”
二、做夢也想離開這個地方
因為窮,年輕的小伙娶不上媳婦;因為窮,有的孩子沒上完初中便輟學了;因為窮,出門在外的人的戶口都落在了外地!
當無力改變自己的周圍環境時,離開也許是最好的辦法。
在朱家澗村,但凡有能力的人,做夢都想逃離這個地方。
杜富國是朱家澗村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家里2個兒子。杜富國說,2個男娃娃,簡直是要老命咧,在我們村給男娃找對象比登天還難,村里不僅彩禮高,還沒有女娃愿意嫁進來。
杜富國在銀川打工,他早早就做打算,在銀川賀蘭縣落了戶,徹底告別了這里。
“不走沒辦法,孩子找不下對象,這是我們老兩口的一塊心病呀。”“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任誰在這地方生活了半輩子,也會不舍離開,可又有什么辦法?
朱存錄說,1997年他進村班子的時候,他們村上有160多戶700多口人,村上的小學少說也有七八十名學生,還有6個教師。
從1998年開始,村民開始外出打工,村上的人越來越少。
“十多年的時間,我們村流失了一半人口。”朱存錄扳著手指頭算起來,有十多戶遷到了同縣的黨原鎮,三四戶遷到了平涼市崆峒區的索羅塬上,遷到王村二十里鋪、劉家溝、王村的有15戶,還有一部分直接把戶口遷到了銀川。
“遷戶可不是誰想遷就能遷的,為了遷戶口,想離開這里的人啥辦法都想到了。”朱存錄嘬了一口茶,慢慢說道:“為了遷戶有當上門女婿的,有給人當干兒子的,有直接買戶口的,還有進城買房的。”
朱喜成家里兩口子,一兒一女,日子倒也過得去。可是兒子找不到對象成了他的隱憂,于是他早早就尋思著要把戶口遷了。
“當時,做夢都想著離開。”朱喜成說起話來,臉上總是堆滿了笑容,“當時離開挺高興的,現在一看留下的人住上了樓房,就有些后悔。”
他還補充了一句:“人眼前的路都黑著哩。”
在朱喜成的心里,不走,兒子可能就要打光棍。
他最終還是離開了這里。
朱喜成的妻姐在黨原鎮城坳村,經過她的牽線搭橋,把戶口也遷到了這個村。
為了遷戶,他也費了好大力氣,鄉上村上和派出所同意后,還要遷入村的全體村民同意。村上召開群眾代表大會,經過商議,朱喜成家每個人掏5000元的遷戶費,給他家每口人分二畝地。
朱存錄說:“當時朱喜成遷出去的時候,村里人都挺羨慕的,都說先走的人家有辦法,都搬到塬上了。”朱存錄還清晰地記得,朱喜成搬走的當天,他笑得眼睛都瞇成了一條線,見到男人就發煙、見到女的就給糖……
住在大山深處,朱家澗人要逃離這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看病是他們最為頭疼的一件事。
朱存錄說,以前村上有個村醫,名叫李根成,治個頭疼腦熱還可以,但若是誰家得了大病,就只能用架子車拉著,到鎮上的衛生院去看病。
“當年,我老伴在鄉上的衛生院做了結扎手術,回村的時候只能坐架子車。由于砂石路顛簸,傷口讓她疼得直哭。沒有辦法,只能找了兩個人用擔架徒步把她抬回家里。”這件事,朱存錄一輩子也忘不了。
2017年10月的一天,村民王金峰的媳婦胃出血,叫了救護車。上山路實在無法通行,只得停在山腳下。可是,病人性命危在旦夕,根本經不起耽擱,救護車上的3名大夫和王金峰火速用擔架把病人抬上救護車,一路奔忙才到了縣醫院,經過救治,病人脫離了危險。
“我們村離鎮上比較遠,路又不好,看病很不方便,一些小病就一拖二磨,直到捱不住了才去鎮上和縣上。”王金峰說。
易地扶貧搬遷不僅讓朱家澗人住上了新房,還讓當地群眾享受到了完善的醫療衛生服務,在一系列惠民政策的支持下,實現了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朱德娃是位慢性病患者,需要長期服藥。他笑著說,以前在老家的時候需要到十幾公里以外的鎮上買藥,自從搬到移民新村后,小區門口就是新建的村衛生所,從安置樓到鎮衛生院最多也就十分鐘的路程,看病、買藥還可以用合作醫療報銷,再也不犯難了。
搬到新的安置小區后,為了解決群眾看病難問題,讓群眾就近就醫、及時就醫,村上在小區門口配套建成了社區服務中心,針對老弱病殘,采取上門服務。
“以前我們是大老遠找大夫,現在是大夫上門找我們。”66歲的朱秉笑呵呵地說。
三、搬遷離開并不那么容易
2015年,中央經過反復論證,決定“十三五”期間對不具備生存條件地方的約1000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實施易地扶貧搬遷。
朱家澗被夾在山旮旯里,300多口人分別居住在8個山頭上的窯洞里,實在難以生存。因此,他們就成了這次搬遷的一部分。假如沒有這樣一個惠民政策,也許他們還要在這里年復一年地延續悉如平常的生活。
然而,當幸福來得太突然的時候,他們甚至不適應、不理解。
在這個類似世外桃源的地方,他們平靜地生活,窮慣了,懶慣了。
政府決定花大氣力動員群眾挪窮窩,進行易地扶貧搬遷。
有人公然反對,不愿意搬。
朱存錄說,當時搬遷的事定下來以后,村上在老村部召開群眾代表大會,就像炸鍋了一樣。
一聽到他們這里要修水庫,要搬出去住樓房,群眾議論紛紛。“住樓房,我們吃啥喝啥呢?城里人發工資,我們喝西北風嗎?”
“聽說我們村上要修水庫,國家補助了幾個億讓我們搬,是不是每家每戶都要補助幾十萬元呢?”
“我們祖祖輩輩都生活在這里,要搬出去,說起來容易得很,好得很么!”第一次群眾代表大會在嚷嚷聲中散場了。
為此,包村領導王村鎮人大主席郭建忠和幫扶干部、村組干部上門挨家挨戶做群眾的思想工作。
走進農家小院,和群眾坐在同一條板凳上,郭建忠才覺得搬遷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搬遷的群眾顧慮重重,有的群眾說,就算住樓掏1萬塊錢不多,可是搬出去收入哪里來;有的群眾說,住樓房不方便,還不如住在土窯里“散舒”;有的想搬遷,東拼西湊也湊不齊1萬塊錢;村里的年輕人想搬,老年人卻安土重遷。
郭建忠知道,要做通群眾的思想工作,只有解了后顧之憂,搬遷才有希望。
他們針對群眾提出的問題,挨個想辦法,逐戶做工作,經過一系列磨合,群眾心里的疙瘩才疏解開。
為了讓搬出去的群眾有收入,鎮上和村上整合了王村的土地,計劃建設蔬菜園區。腿腳不便的群眾住樓不方便,他們就給村里的孤寡老人、殘疾戶修平房。有的群眾湊不夠搬遷的1萬塊錢,村里就先墊著……
村里的人還不放心,郭建忠就租了一輛中巴車,把群眾代表拉到搬遷安置區的施工現場轉了一圈,群眾才打消了顧慮。
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到安置區轉了一圈的人都回來說:“新建的移民新村比老村子條件好多了,搬出去美得很。”
俗話說,窮家難舍,故土難離。
盡管大多數群眾同意搬遷,但還是有一部分老人不同意。
村里的大部分人都搬出去了,推土機開進老村子,對廢棄的舊窯洞進行墾復。
就在這個時候,66歲的朱秉站了出來,他擋在推土機前面,不讓墾復。
“我祖祖輩輩都生活在這里,這些窯洞和房屋都有我們的心血與感情,不能推。”鎮村干部耐心地勸說,答應暫時不墾復,他們用小車把朱秉接到新樓房看了一下,到新建的蔬菜園區轉了一圈,才讓這個倔老頭思想上轉過了彎。
“政府為我們啥心都操到了。”身體殘疾的朱來銀對搬遷有顧慮,他害怕住樓房,“住到樓上不方便,我一天下不了樓,那就像坐監哩。”
為了打消朱來銀的顧慮,村上在安置樓前面修了一排平房,朱來銀分到了40平方米的兩間房。為了他的輪椅上下院子方便,鎮上還在他家的門口專門修了小斜坡,縣殘聯還為他專門安裝了馬桶扶手。
“搬出來好著咧!”朱來銀說,現在他和母親生活,妻子在西安看領孫子,現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
四、幫扶傾心只為一個目標
縣委、縣政府決定實行整體搬遷后,幫助朱家澗村走出了困境。
搬遷工作實施以來,幫扶力量、幫扶資金、幫扶項目向朱家澗村傾斜。
朱家澗成了受益最大的村子,也成了鎮上最熱鬧的地方。
對口幫扶的天津市武清區,先后落實東西部幫扶資金700多萬元,在朱家澗移民新村建成了蔬菜園區、日光溫室。建成的300座鋼架大棚,朱家澗的群眾每家每戶都分到了。
位于京濱工業園區的天津大禹節水公司,捐贈了價值31.67萬元的滴管設施;武清區泗村店鎮倉上村援助幫扶資金10萬元,購置飼草收割車,武清和平之君服務中心針對28戶未脫貧群眾開展微捐助……拳拳愛心,匯聚起了幫扶的磅礴力量。
大棚建起來后,針對朱家澗村產業基礎薄弱、群眾發展產業能力不足的情況,武清區選派2名蔬菜產業種植方面的專業技術人才,全天在蔬菜園區手把手教農民科學種菜、種瓜。
對武清區的幫扶,朱家澗村的群眾交口稱贊:“為咱們想的很周到,真心實意為咱們辦實事。”
42歲的朱軍建初中畢業以后,就開始打工,近幾年一直在銀川開出租車。村里搬遷后,他回到村里開始種瓜菜,他分到了1個拱棚,父親分到了2個拱棚,又流轉了6個拱棚,開始種甜瓜。
朱軍建聰明又踏實肯學,他白天在瓜園里忙活,晚上拿著手機看直播學技術,他精心侍弄著自己的瓜園。看著瓜秧一天天往上竄,一個個潔白的甜瓜一天天變大,他笑得合不攏嘴,渾身有使不完的勁。
2020年五一過后,朱軍建的甜瓜陸續上市。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甜瓜賣不出去,出現了滯銷現象,朱軍建急得團團轉。
甜瓜種植大戶朱惠平,望著滿棚新鮮的甜瓜,滿面愁容:“甜瓜沒人要,爛在地里,可咋辦呢?”
朱家澗村駐村第一書記兼幫扶工作隊隊長、平涼市工信局干部楊蒼龍了解到這一情況后,立即和村上的干部在鎮上的知青記憶園景區門口擺攤設點,當起了推銷員,幫助瓜農銷售甜瓜。
小打小鬧始終解不了燃眉之急。
2020年5月27日,涇川縣黨政代表團到武清區對接精準扶貧工作。
王村鎮黨委書記劉小平,提出了朱家澗的甜瓜滯銷的困難后,武清區政府立即啟動了應急響應,開展消費扶貧和愛心義購,動員全區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通過食堂用餐、工會會費等“以銷代捐”。
返回涇川后,劉小平第一時間將消息告訴朱家澗的群眾,這才讓他們吃了定心丸。
為確保運往天津武清區的甜瓜品質,劉小平當起了甜瓜分揀的監督員,他忙完手頭的工作,就一直盯在甜瓜分揀現場。
“6月5日,第一批2萬斤甜瓜裝車發往武清區。”楊蒼龍對這一天記得特別清楚,“那一天鎮上的干部、幫扶干部和村組干部忙完都4點多了。”
為了加快裝車進度,讓武清區市民吃上新鮮的甜瓜,王村鎮機關干部、駐朱家澗村扶貧工作隊,招募扶貧志愿者共計40余人,與朱家澗村群眾一道,晝夜不休進行采摘、分揀、包裝、裝車。直到6月19日,總價值106萬余元的18萬斤甜瓜全部送達武清。
天津武清區的甜瓜送完后,楊蒼龍并沒有閑下來,他仍然忙得像陀螺。
47歲的楊蒼龍,皮膚黝黑,說話聲音大,干練利索,干起工作來風風火火。他半個多月沒回家了,老婆意見特別大,電話里總問他:“到底啥把你吸引著不著家?”
他知道,只有甜瓜賣出去,變成現錢,他心里才踏實。
“2020年,我利用私人關系,幫助村里群眾賣了15萬元的甜瓜。”說話間,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滿滿的成就感。
元旦前,楊蒼龍忙著給群眾算瓜賬,他手里捏著一沓厚厚的發票;“這些都是為企業消費扶貧、個人愛心義購的瓜菜開的票據。”他笑著說:“群眾不容易,辛辛苦苦一年,種的瓜菜賣不出去,就白忙活咧。”
“今年我的甜瓜,楊書記給我聯系賣出去2萬多元,多虧了楊書記。”徐虎林嘿嘿一笑,一邊和楊蒼龍對賬一邊說。
朱家澗的群眾笑了,甜瓜讓他們的腰包鼓了起來;因為群眾笑了,楊蒼龍和幫扶隊員也笑了,他們的辛苦付出沒有白費,一切都是值得的……
五、如今幸福生活像花兒一樣
今年45歲的朱惠平和妻子李海玲補拍了一張婚紗照,掛在他們臥室的正中央,臉上笑開了花。
“生活條件好了,今年收入也可以,就和妻子補照了一張婚紗照,也趕一回時髦,幫妻子圓了一個心愿。”朱惠平撓撓頭,有點不好意思。
對朱惠平來說,他的高興事還不止這一樁。
就在全縣召開的經濟工作會議上,他還被評為村上的種菜能手,登上全縣的領獎臺,披紅戴花受到表彰獎勵。
朱惠平說,種了10個大棚甜瓜,甜瓜賣完后加上種菜的收入,一年下來能收入5萬多元,這是原來在老村子幾年的收入。
“搬出來,只要人勤快,就不愁掙不到錢。”他說。最近幾天他早上4點多起床,5點把前一天晚上摘好的西紅柿和菠菜拉到平涼崆峒區的新陽光蔬菜批發市場進行批發,最近一連幾天,收入天天過千元。
說起新年的打算,他笑著:“希望正在上高三的女兒,能考一個好的大學;自己把瓜菜種好,攢點錢,為在西安工作的兒子買樓房,交個首付。”
“原來在老村子,沒有想這么多,種菜買樓房,想也不敢想。”朱惠平憨笑著,憧憬著美好的生活。
遷到移民新村后,群眾的生活好了,收入高了,近兩年村里買了10多輛小汽車。
朱存錄說:“搬出來,人心齊了,覺悟高了,過好日子的人多了。
原來住在山里頭,封閉頑固,思想落后,抬杠的人多,說閑話的人多。現在搬出來,眼界寬了,心態好了,都會過日子了,都爭著比,看誰家的日子過得紅火,看誰家能買個小車。”
王等祥家就在2020年國慶節前買了一輛十多萬元的小轎車,村里的人都趕著去道賀。
以前走的是彎彎曲曲的山路,別說開車了,就連跑個三輪車都困難,村里的大多數人都得騎摩托。如今,寬闊的柏油路,時新的SUV汽車一路“小跑”,笑聲不絕于耳。
對于眼前的幸福生活,53歲的郭小蘭打心眼里高興:“原來條件差,到處都是山,山高路遠,吃水一直要用驢馱。家里種的大蔥、糧食一年到頭也就賺萬把塊錢。搬出來以后,有了自家的大棚,還能在知青記憶園里務工,日子越過越好了。”
郭小蘭的丈夫朱成懷在村里的蔬菜專業合作社上班,有了固定收入,每月能領到3000元的工資,一年收入3萬多元。他說,種一個大棚比種10畝糧食還劃得來,他家那3頭紅牛還在合作社入了股,每年分紅3650元。
說起住上樓房,信小玲笑著說:“以前在窯里做飯,煙熏火燎,二三月的天氣,做飯的時候打倒煙,窯里全部是煙。現在好了,天燃氣開關一擰,做飯不到半個小時呢。”
當時搬遷的時候,朱秉老人不同意,搬出來卻滿心歡喜:“我活了60多歲,沒想到能住上這么好的房子,打心里里感謝黨和政府!”
搬出來并沒有像當時朱秉所顧慮的那樣要喝西北風,相反,他和老伴都找到了新工作。朱秉在村上的扶貧車間打零工。67歲的老伴楊蓮珠,在鎮上的川湘情飯館揪面片,每月凈收入2000多元。
最讓朱存錄高興的是,村里娃娃找對象難的頭疼問題解決了。以前10年沒有娶進一個新媳婦,搬到移民新村,2019年一年就娶進了3個新媳婦。
“現在村里都沒有大齡男娃娃了,再也不為這事犯愁了。”朱存錄說話時,臉上笑出了褶。
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如今的朱家澗村建成了設施蔬菜園區、紅牛養殖場,安置區斜對面建起的知青記憶園旅游景區,進入旅游旺季,人氣爆棚。易地扶貧搬遷讓朱家澗村群眾告別了窮窩窩,如今,他們的生活和大棚里的蔬菜一樣生氣勃勃,和甜瓜一樣芳香四溢,和紅牛一樣牛氣沖天!
幸福的笑容洋溢在朱家澗人的臉上,他們的生活像花兒一樣綻放……
責任編輯/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