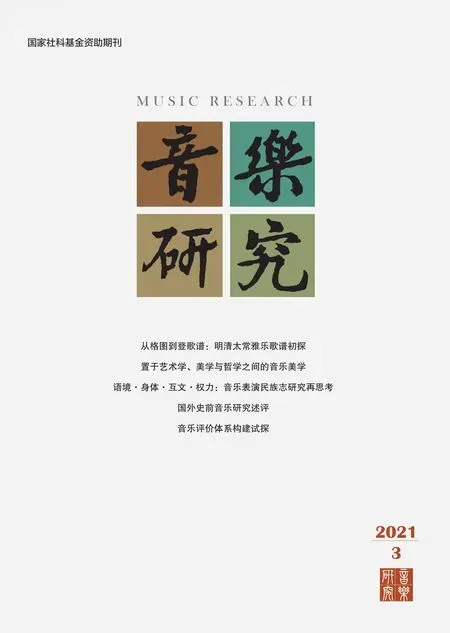兩晉南北朝時期廂樂制度研究
文◎尹 蕾
兩晉南北朝近四百年,中原地區局勢動蕩,致使國家禮樂陷入窘境。但統治者并未放棄禮樂建設,“永和十一年,謝尚鎮壽陽,于是采拾樂人,以備太樂,并制石磬,雅樂始頗具。太元中,破苻堅,又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于是四廂金石始備焉。”①[唐]房玄齡《晉書》,中華書局1974 年版,第698 頁。所謂“四廂金石”,就是這一時期形成的,即以“廂”為單位的禮樂制度。
一、“廂”與“廂懸”
“廂”字在一些古代史籍中均有記載,如《漢紀》載:
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②[東漢]荀悅《漢紀》“孝惠皇帝紀卷第五”,載《兩漢紀》,中華書局2002 年版,第62 頁。
《后漢書》載:
乘輿自東廂下……退坐東廂……御坐東廂。③[南朝宋]范曄《后漢書》,中華書局1974 年版,第2301 頁。
張衡《東京賦》載:
是時稱警蹕已下凋輦于東廂。④[南朝梁]蕭統《昭明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108—109 頁。
《漢書》載:
見王路堂者,張于西廂及后閣更衣中,又以皇后被疾,臨且去本就舍,妃妾在東永巷。壬午,烈風毀王路西廂及后閣更衣中室。⑤[漢]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4159 頁。
從上述記載可知,“廂”字多用于表示“廊”或“房屋”之意,并未與宮廷禮樂制度聯系在一起。
晉以來,“廂懸”開始出現于史料記載。泰始十年(274),中書監荀勖、中書令張華等討論宮廷用樂問題:“案《周禮》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是故造鐘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后施于廂懸。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鐘磬之均,即為悉應律也。至于饗宴殿堂之上,無廂懸鐘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弦歌皆從笛為正,是為笛猶鐘磬,宜必合于律呂。”⑥同注①,第482 頁。“廂懸”就是將金石樂懸置于“廂”中而形成的一個稱謂,“至于饗宴殿堂之上”,表明“廂懸”一詞所適用的場合。這一用詞上的細微改動,反映出當時在禮樂律調、樂器等方面的變化。與此同時,“四廂樂”“四廂樂歌”等,也開始頻繁出現于史籍。
二、四廂樂
周公旦制禮作樂,將禮樂制度發展成為嚴密的體系,規定著帝王至士大夫不同階層享用金石樂懸的資格。春秋戰國時期,禮樂制度的壁壘被打破,但禮樂觀念早已根深蒂固。兩晉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戰亂,使禮樂建設受到較大沖擊,但人們對禮的認識卻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五禮制度得到重新解讀和確立,配合禮的“樂”自然也有所變化。人們以“廂”懸設鐘磬于賓、嘉之禮等儀式場合,逐漸形成“四廂樂”這種特殊的禮樂形式,“廂樂”由此承擔起宮廷儀式樂的職責。
(一)晉之四廂樂
“五禮”最早出現在《周禮》,內容與后世有所不同,兩漢時期以“士禮”為制,真正的五禮制度至魏晉時期才逐漸確立,并對晉時四廂樂的產生和使用起到了推動作用。史載晉武帝在先正一日儀式用樂時就使用了四廂樂:
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導皇帝升御坐,鐘鼓止,百官起。……太樂令跪請奏雅樂,樂以次作。……謁者、仆射跪奏“請群臣上”……四廂樂作,百官再拜。……陛下者傳就席,群臣皆跪諾。侍中、中書令、尚書令各于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又行御酒……太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具御飯……太樂令跪奏“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案遍。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樂”。樂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眾妓”。……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群臣北面再拜,出。……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于黃帳外,奏房中之歌。⑦同注①,第650—651 頁。
這段史料較完整地記載了晉時先正一日宮廷朝會宴饗的儀式過程,儀式分為三個階段:儀式拜會、燕饗宴飲和晝會,三個階段都有“樂”相隨,但引領者和作用不同(見表1)。

表1
《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晉詩》歌辭中四廂樂歌的數量最多,包括正旦大會行禮歌、上壽酒歌、食舉東西廂歌等,說明當時在太樂令引導的奉觴、上壽酒、行百官飯等階段中,都是以四廂樂相隨,在當時屬雅樂范疇,伴隨著燕饗儀式進行。
(二)南北朝前期
南朝宋、齊及北魏幾朝,也使用“四廂樂”,記載多見于史冊,是當時賓嘉儀式場合中重要的禮樂。伴隨著不同儀式場合有序的進程,禮樂既可四廂共作,也可四廂分別設樂,廂別選擇隨儀式環節及等級的不同而變化。
1.宋之四廂樂
宋時,四廂樂在使用范圍和場合等,較晉時已明顯擴大:
凡遣大使拜皇后、三公,及冠皇太子,及拜蕃王,帝皆臨軒。其儀,太樂令宿設金石四廂之樂于殿前。……謁者引護當使者當拜者入就拜位,四廂樂作。將拜,樂止。禮畢,出。⑧[梁]沈約《宋書》,中華書局1974 年版,第341 頁。
大使拜會及皇太子冠禮等賓、嘉之禮,開始普遍使用四廂樂。《宋書·樂志》載,宋時除登歌需別用金石之外,四廂樂在行禮、上壽、食舉、歌舞等諸多儀式環節中普遍使用,且廂別不同(見表2)。

表2
其中,《法章》《九功》是兩廂樂(太簇、姑洗),行禮、上壽、食舉、歌舞為一廂樂(廂別不同),《肆夏》樂歌則四廂同作。《肆夏》是古代樂章名,《魯語》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⑨《國語·魯語(下)》,載徐元誥《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 年版,第178 頁。宴饗開始先用四廂作《肆夏》,也是天子用樂禮制。在宋正旦大會中,“廂樂”使用頻繁,以器樂為主,有時有歌。晉時前舞歌、后舞歌,需“別用金石”,至宋則固定使用南廂,即蕤賓廂。
2.齊之四廂樂
齊承晉宋之制,在元會大饗禮儀中繼續使用四廂樂:
元會大饗四廂樂歌辭,晉泰始五年太仆傅玄撰……齊微改革,多仍舊辭。其前后舞二章新改。……右一曲,客入,四廂奏。……右一曲,皇帝當陽,四廂奏。皇帝入變服,四廂并奏前二曲。……右二曲,皇帝入變服,黃鐘太簇二廂奏……右二曲,姑洗廂奏。……右一曲,黃鐘廂奏。……右三曲,別用金石,太樂令跪奏。……右黃鐘先奏《晨儀》篇,太簇奏《五玉》篇,余八篇二廂更奏之。⑩[梁]蕭子顯《南齊書》,中華書局1972 年版,第185—188 頁。
齊之四廂歌辭,多是對晉之“舊辭”稍加改革而直接使用,在歌辭名稱和使用廂別上,也與宋之四廂樂幾近一致。?在“皇帝入變服”一環節中,劉宋為“四廂振作”,而齊則是黃鐘、太簇二廂作樂。
3.北魏之四廂樂
北魏在建國初,就將中原舊曲及清商樂納入殿庭燕饗:
初,高祖討淮、漢,世宗定壽春,收其聲伎。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荊楚四聲,總謂《清商》。至于殿庭饗宴兼奏之。?[北齊]魏收《魏書》,中華書局1974 年版,第2843 頁。
祭祀則備四代之樂:
樂制既亡,漢成謂《韶武》《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鐘,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同注?,第2839 頁。
這里提到的奏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四律,以祭祀天地、五郊明堂、四望山川及宗廟,與晉宋四廂樂宮調結構完全相同,卻與周之樂懸相殊。《魏書》也直言不諱:“依魏晉所用四廂宮懸,鐘、磬各十六懸,塤、篪、箏、筑聲韻區別……元日備設,百官矚瞭。”?同注?,第2839 頁。坦言受魏晉禮樂制度及中原地區禮樂文化影響,設四廂宮懸用于元日大會。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政權,統治者需要通過禮樂獲取轄內漢人的文化認同,因此,禮樂建設也以漢族固有傳統為范本。
兩晉至南北朝前期,四廂樂已在朝廷賓、嘉禮中普遍采用。從四廂樂使用場合看,晉宋齊魏幾代主要用于“元日大會”、拜會及冠禮等賓、嘉之禮,配合皇帝、王公大臣及賓客的儀式活動進行;從表演內容看,則為前代雅樂和舊曲。這表現出,在民族大融合的歷史背景下,漢族和異族政權對權力合法性的共同追求。
(三)南北朝后期
南北朝后期,由于梁武帝對雅樂的厘正,胡樂、俗樂、絲竹樂的盛行,政權交替加劇等因素,四廂樂這一存在了兩百多年的禮樂形式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1.南朝之梁、陳
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502 年4 月30日),蕭衍登基,“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用齊典。”?[唐]姚思廉《梁書》,中華書局1974 年版,第34 頁。梁武帝本身精通音律,在沿用齊制的前提下,他進行了禮樂改革:
天監初,則何佟之、賀蒨、嚴植之、明山賓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兇軍賓嘉五禮,凡一千余卷,高祖稱制斷疑。?同注?,第96 頁。
又,天監元年秋八月丁未(502 年10月8 日):
上素善鐘律,欲厘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為“通”。……又制十二笛……先是,宮懸止有四镈鐘,雜以編鐘、編磬、衡鐘凡十六虡。上始命設十二轤鐘,各有編種、編磬,凡三十六虡,而去衡鐘,四隅植建鼓。?[宋]司馬光《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56 年版,第4606—4607 頁。
同時,梁武帝還是一位篤信佛法的帝王:“不飲酒,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同注?,第97 頁。太清元年(547),梁武帝“輿駕幸德陽堂,宴群臣,設絲竹樂”?同注?,第92 頁。。從“稱制斷疑”到“厘定雅樂”,非宗廟及大會饗宴不作樂,其他宴會場合也常設絲竹樂,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四廂樂不見于史籍。
陳時,情況大抵相同,高祖霸先常以儉素自律,歌鐘女樂不列于前。同時,絲竹樂、胡樂盛行于宮廷和上層社會,陳大將章昭達:“每飲會,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盡羌胡之聲,音律姿容,并一時之妙。”?[唐]姚思廉《陳書》,中華書局1972 年版,第184 頁。宣帝太建八年,將士凱旋饗宴文武,也設絲竹之樂,未見四廂。
2.北朝之周、齊
北朝前期雖戰亂不斷,但北魏內部卻相對穩定。至北朝末年,政權交替頻繁,北魏分裂為東魏、西魏,后又被北齊、北周取代。統治者雖有禮樂需求,殘存一些吉禮用樂活動,但頹勢已成,無法形成完備的禮樂體系。
西魏宇文泰革漢魏舊制,仿《周禮》設六官,禮樂隨之而變,以周之“六代樂”重新取代魏晉以來的“四代之樂”。天和元年冬十月甲子(566 年11 月18 日),“初造《山云舞》,以備六代樂。”至建德二 年 冬 十 月 甲 辰(573 年11 月21 日),“六代樂成,帝御崇信殿,集百官觀之。”[21][唐]李延壽《北史》“周本紀下”,中華書局1974 年版,第353 頁。這畢竟只是一種政治追求,真正的周禮面貌并未恢復。北齊直到建國十年后的皇建元年九月壬申(560 年10 月28 日),才開始討論吉禮宗廟用樂問題,其他賓、嘉等禮樂并未涉及。
與此同時,胡樂興盛于北朝,對禮樂形成沖擊。史載“后周武帝在云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22]同注[21],第1878 頁。。太建十一年十二月戊午(580 年1 月3 日),二十一歲的周宣帝宇文赟禪位于七歲的長子宇文衍(也作宇文闡),自稱天元皇帝。“周天元以災異屢見,舍仗衛,如天興宮……甲子,還宮,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外命婦,大列伎樂,初作乞寒胡戲。”[23]同注?,第5401—5402 頁。武平七年(576),北齊幼主高恒自彈胡琵琶演唱當時盛行的《無愁之曲》,“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24][唐]李百藥《北齊書》“帝紀第八”,中華書局1972 年版,第112 頁。,胡樂在北朝宮中盛況可見一斑。
南北朝后期,為數不多的國家吉禮活動延續著鐘磬金石之樂,宴饗則常雜用絲竹樂、伎樂、胡樂,四廂樂在北齊、北周及梁、陳二朝不見于記載。梁滿倉在《魏晉南北朝五禮制度考論》一書中認為:在以儒學為主體的各種學說與社會思潮不斷碰撞和融合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對以禮治國的意識日趨強化,實行了與兩漢禮制不同的五禮制度,它孕育于漢末三國,發育于兩晉與宋齊,成熟于蕭梁時期。[25]梁滿倉《魏晉南北朝時期五禮制度考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版。這一推論與“四廂樂”的發展歷程基本一致,說明四廂樂的產生與禮制變化密切相關。
三、四廂樂歌
四廂樂在兩晉及宋齊賓嘉儀式中的繁盛,使士大夫文人階層也參與到四廂樂的創作中,并留下了大量“四廂樂歌”歌辭。[26]有關“四廂樂歌”的研究,有王福利《南朝齊四廂樂歌辭考辨》(《中國詩歌研究》2008 年第1 期),許繼起《樂府四廂制度及其樂歌考》(《文學遺產》2015 年第5 期)等成果。《晉書》《宋書》《隋書》《樂府詩集》《文獻通考》《南齊書》《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等涉及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史料,都收錄有四廂樂歌辭。這些歌辭也從另一方面證明四廂樂在當時的重要性。僅《晉書》所載“四廂樂歌”就有:成公綏《正旦大會行禮歌》;荀勖《正旦大會上王公壽酒歌》《食舉樂東西廂歌》;張華《冬至初歲小會歌》《宴會歌》《命將出征歌》《勞還師歌》《中宮所歌》《宗親會歌》《正德舞歌》《大豫舞歌》等。四廂樂歌的歌辭,三言、四言均有,多為對統治者和朝廷的頌揚之言:
大哉皇宋,長發其祥,纂系在漢,統源伊唐。德之克明,休有烈光。[27]同注⑧,第594 頁。
登昆侖,上層城。乘飛龍,升泰清。冠日月,佩五星。揚虹霓,建篲旌。披慶云,蔭繁榮。覽八極,游天庭。順天地,和陰陽。序四時,曜三光。張帝網,正皇綱。播仁風,流惠康。[28]同注①,第684 頁。
四廂樂歌在兩晉南北朝時期主要用于宮廷燕饗禮儀并具有重要地位。以《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的《晉詩》一卷為例,其一,該卷歌辭分為郊廟歌辭、燕射歌辭、鼓吹曲辭和舞曲歌辭四個部分,四廂樂歌列為燕射歌辭類(見表3),表明主要用于賓嘉燕饗等禮儀,包括行禮、上壽、食舉等不同環節和內容,輔助儀式進行,兼具一定的娛樂性。

表3
其二,在四類歌辭中,四廂樂歌是《晉詩》中數量最多的一類,共61 首,幾乎相當于其他三類的總和。
四、廂樂制度
兩晉南北朝前期朝會、燕射等禮中的四廂樂,以廂別區分儀式,并具有固定的宮調結構、樂器組成、音樂內容和等級差別,成為當時宮廷的一種禮樂制度,我們可稱其為“廂樂制度”。這種制度承襲周禮的基本原則,但在宮調結構、樂隊編制、等級觀念及適用范圍方面,又有著不同于周禮的特殊性。
(一)律調結構
四廂樂依方位而設,由北廂黃鐘之宮,東廂太簇之宮,南廂蕤賓之宮,西廂姑洗之宮組成。
1.陽律為宮
四廂樂所用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四律皆為陽律,這一“陽律為宮”的用樂制度,可以在《周禮》“奏黃鐘,歌大呂”[29][明]吳興凌、杜若校刊《周禮》,朱墨套印,第63 頁。的史料記載中找到源頭。《周禮》載祭祀所“奏”的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律,便皆為陽律。漢以來,祭祀對象在原來天、地、山川、四望、先妣、先考六種基礎上進行了合并重組,表現為:天地合一,山川四望合一,先妣先考合為宗廟,增加了五郊與明堂。于是,周“六代之樂”隨之變為“四代之樂”:
奏黃鐘,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祀圜丘、方澤,群廟祫祭之時則可兼舞四代之樂。[30]同注?,第2839 頁。
周代禮樂本來就有“賓祭同用”的觀念:“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31]同注[29]。,除“牲出入”時所奏的《昭夏》不用于燕饗等賓禮之外,其他都與祭祀用樂相同。四廂樂雖然多用于賓嘉之禮,歌辭也屬燕射歌辭類,但是仍然保持著與吉禮樂制的一致性。四廂樂以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四律為宮,正是這種“如祭之儀”的“賓祭同用”禮樂觀念在樂調結構上的體現。四廂樂“四陽律為宮”的樂調觀念,在制度上是清晰的,但實際應用上四宮并不完備。北魏閔帝普泰元年(531):“太樂令張乾龜答稱芳所造六格:北廂黃鐘之均,實是夷則之調,其余三廂,宮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樂人尚存;又有姑洗、太簇二格,用之后宮,檢其聲韻,復是夷則,于今尚在。”[32]同注?,第2837 頁。北廂本應用黃鐘,實際卻是夷則,姑洗、太簇廂竟也用夷則調,并且律調宮商不和、名實有差,徒有廂樂之名。
2.四廂律笛
兩晉南北朝時期,律笛尺寸時常發生變化。
黃鐘廂笛,晉時三尺八寸。元嘉九年,太樂令鐘宗之減為三尺七寸。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又減五分,為三尺六寸五分。(列和云:“東廂長笛四尺二寸也。”)太簇廂笛,晉時三尺七寸,宗之減為三尺三寸七分,縱又減一寸一分,為三尺二寸六分。姑洗廂笛,晉時三尺五寸,宗之減為二尺九寸七分,縱又減五分,為二尺九寸二分。蕤賓廂笛,晉時二尺九寸,宗之減為二尺六寸,縱又減二分,為二尺五寸八分。[33]同注⑧,第219 頁。
協律中郎將列和提出:“太樂東廂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34]同注⑧,第213 頁。荀勖曰:“謹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之法,制十二笛象。”其中“黃鐘之笛,正聲應黃鐘,下徵應林鐘,長二尺八寸四分四厘有奇。[35]同注⑧,第215—216 頁。
太簇之笛,正聲應太簇,下徵應南呂,長二尺五寸三分一厘有奇……姑洗之笛,正聲應姑洗,下徵應應鐘,長二尺二寸三分三厘有奇……蕤賓之笛,正聲應蕤賓,下徵應大呂,長三尺九寸九分五厘有奇。”[36]同注①,第485 頁。(見表4)

表4
這一時期的律度量衡變化較為頻繁,律笛長度不斷加長,加上社會動蕩的局面,使得律調制度混亂無依。甚至太樂東廂(太簇廂)笛長四尺二寸,正聲卻應蕤賓之律,樂工只識尺寸,竟不能辨其律:“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而令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37]同注⑧,第212 頁。北魏普泰元年(531)“北廂黃鐘之均,實是夷則之調,其余三廂,宮商不和,共用一笛……又有姑洗、太簇二格,用之后宮,檢其聲韻,復是夷則”[38]同注?,第2839 頁。。北魏孝武帝永熙二年(534)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奏:
太和中,命故中書監高閭草創古樂,閭尋去世,未就其功。閭亡之后,故太樂令公孫崇續修遺事,十有余載,崇敷奏其功。時太常卿劉芳以崇所作,體制差舛,不合古義,請更修營,被旨聽許。芳又厘綜,久而申呈。時故東平王元匡共相論駁,各樹朋黨,爭競紛綸,竟無底定。及孝昌已后,世屬艱虞,內難孔殷,外敵滋甚。永安之季,胡賊入京,燔燒樂庫,所有之鐘悉畢賊手,其余磬石,咸為灰燼。普泰元年,臣等奉敕營造樂器,責問太樂前來郊丘懸設之方,宗廟施安之分。……而芳一代碩儒,斯文攸屬,討論之日,必應考古,深有明證。乾龜之辨,恐是歷歲稍遠,伶官失職。芳久殂沒,遺文銷毀,無可遵訪。[39]同注?,第2837—2838 頁。
可見,兩百多年間,經歷了從高閭草創古樂未就其功,到公孫崇續修卻“體制差舛,不合古義”,再到劉芳厘綜以“爭競紛綸,竟無底定”告終,以及后之“胡賊入京,燔燒樂庫”“其余磬石,咸為灰燼”“歷歲稍遠,伶官失職”“遺文銷毀,無可遵訪”。種種舊事足以說明,當時的禮樂建設面臨著極大的困境。如此,四廂律調徒有其名也在情理之中。
(二)樂器構成
四廂樂使用編懸類樂器,在樂器選擇及樂隊編制方面,都顯示出與周代宮懸一脈相承,證明四廂樂為禮樂之用的樂類性質。
1.對周禮樂器的繼承
《隋書·音樂志》載:
又晉及宋、齊,懸鐘磬大準相似,皆十六架。黃鐘之宮:北方,北面,編磬起西,其東編鐘,其東衡大于镈,不知何代所作,其東镈鐘。太簇之宮:東方,西面,起北。蕤賓之宮:南方,北面,起東。姑洗之宮:西方,東面,起南。所次皆如北面。設建鼓于四隅,懸內四面,各有柷敔。[40][唐]魏征《隋書》,中華書局1979 年版,第291 頁。
四廂在樂器數量、種類及排列上完全一致,只是宮調不同。所設編鐘、編磬、大于镈、镈鐘和柷敔等俱為編懸樂器,表明四廂樂與周代禮樂制度之間的淵源關系。
2.對非雅樂器的排斥
漢魏以來,隨著越來越頻繁的文化交流,外來樂器不斷進入中原宮廷。然而,統治者對于樂器的雅、胡身份,有著明確認識和嚴格區分。《宋書》中有“今有胡篪,出于胡吹,非雅器也”[41]同注⑧,第558 頁。的記載,將源于北方少數民族的樂器冠以“胡篪”[42]這里的“胡篪”并非“篪”,應是這一時期傳入中原的類似篪的一種吹管樂器。之名,不納入具有禮樂性質的四廂樂。此外,還有琵琶“并未詳孰實,其器不列四廂”[43]同注⑧,第556 頁。。這些都表明四廂樂所具有的禮樂性質。
3.四廂樂隊編制
四廂所用樂器種類與周禮幾近一致,但在編制數量上卻時常變化無定制。從史料記載看,晉及宋齊編制基本相同,每面各設編鐘、編磬、大于镈、镈鐘各一架,四面共十六架。但“魏、晉已來,但云四廂金石,而不言其禮,或八架、或十架、或十六架……后魏、周、齊皆二十六架。建德中,復梁三十六架”[44][后晉]劉昫《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 年版,第1080 頁。。可以看出,各朝各代在編懸數量上常有變化,并無嚴格規制,其中十六架較為常見。這應與當時禮樂建設所面臨的困境有關,樂工散失、樂器流沒,樂隊編制只能因時、因勢而立。
(三)等級觀念
禮樂制度自周以來已深入人心,雖歷經禮崩樂壞、戰亂紛擾,但等級觀念猶存。《左傳》載有仲叔于奚辭封邑請曲縣(三面宮懸,即軒懸)事件,[45]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 年版,第788 頁。可知“樂懸”的重要地位,甚至比封邑更為要緊。“廂樂制度”的等級觀念,在皇太子用樂規格上有著明確的體現:
(晉)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升在三恪上。[46]同注⑧,第344 頁。
“三恪”是指恪禮,是針對前朝的末代帝王及其后裔的特殊制度,他們在國家滅亡后被封爵、封邑,成為世襲的特殊貴族。這種禮儀宣示了本朝的正統地位,是中國古代特有的政治和文化現象,屬賓禮之一。魏晉以來,皇太子一應禮制與三恪大致相當,低于皇帝而在王公士大夫之上。皇帝使用四廂樂,皇太子便用三廂樂。張敞《晉東宮舊事》載:“皇太子大小會,庭設三廂樂,舞六佾。”[47][唐]徐堅《初學記》“儲宮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商務印書館(中國臺灣),第15 頁。這顯然與周代諸侯軒懸之制相符。
然而,廂樂制度雖然能夠體現一定的等級觀念,但是遠遠沒有達到周代金石樂懸的嚴密程度。更多時候,廂別選擇僅僅用于不同的儀式階段和場合,而不是體現等級差別。史籍所錄四廂樂,常是在客入、皇帝當陽、皇帝入便服等環節使用。其他環節,或兩廂更作,或一廂振作;有時庭設兩廂樂,有時則為三廂樂、四廂樂。這表明,四廂樂雖有一定之規,卻沒有形成完備的體系。
五、廂樂制度與周代樂懸之異同
廂樂制度是兩晉南北朝時期依周禮而建的一種禮樂制度,在等級觀念和樂器使用上,體現出與周禮樂懸制度共有的一些特征,在適用范圍、樂制、樂調等方面,與周禮又存在差異。這由兩晉南北朝時期特有的社會文化屬性決定。
(一)共 性
其一,禮樂功能。廂樂多用在元會、燕饗、冠禮等賓嘉禮儀中,配合奉觴、上壽酒、行百官飯、客入、皇帝當陽、皇帝入便服等儀式。禮制儀式決定用樂的內容和標準,不同儀式類型又有著不同的音樂類型。廂樂制度與周代樂懸,均是禮樂相須為用,是為禮樂功能的典型特征。
其二,雅樂性質。中國古代的禮樂涵蓋范圍很廣,鼓吹樂、金石樂懸等同為禮樂范疇,但其內容與形式卻各不相同。魏晉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時期,中原固有文化受到很大沖擊,但人們心中仍然存有華夏正聲的理想和追求。從四廂樂的音樂內容看,《東觀漢記》有漢明帝時期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的記載,漢魏時期杜夔所傳的舊雅樂四曲中也有《鹿鳴》。晉時,每當正旦大會,這首前代流傳下來的雅樂都由東廂雅樂郎進行演奏。除了前代流傳下來的之外,四廂樂還有本朝創制的新歌辭,內容都是贊頌之言,句式整齊,文辭優雅,均為文人士大夫所作。四廂樂尚雅的音樂內容,以及“非樂懸不用,非雅器不用”的特點,昭示著它的雅樂性質。
其三,等級觀念。雖歷經禮崩樂壞、社會動蕩,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禮樂建設已經很難再有周代禮樂的規模。但四廂樂仍然在制度上體現出等級差別,在一定程度上遺緒了周代樂懸的等級觀念。
(二)差異性
其一,律調結構不同。周代宮懸十二律皆備,而四廂樂只用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四律,后被隋文帝認為是“六律不具”之樂:“著晉、宋史者,皆言太元、元嘉四年,四廂金石大備。今檢樂府,止有黃鐘、姑洗、蕤賓、太簇四格而已。六律不具,何謂四廂?”[48]同注[40]。四廂樂的這種宮調結構,源自當時的祭祀用樂,兩晉南北朝的祭祀儀制發生了變化,由天、地、山川、四望、先妣、先考六種,合為天地、山川四望、宗廟、五郊明堂四種,配合禮制所用之樂自然也要做出相應調整,律調結構也必然與周禮有異。
其二,使用群體不同。周代禮樂雖等級有別,但士大夫以上階層普遍享有禮樂形式。然而秦漢以來,樂懸基本局限在宮廷,除非皇帝特許或賜予,王公大臣及士大夫不再普遍享有金石樂懸。從許多史料記載來看,皇帝作為禮物賞賜給有功之臣的“樂”,都為鼓吹樂和女樂。由編鐘、編磬、建鼓、镈鐘等金石樂器組成的四廂樂,從未用于宮廷之外。廂樂的用樂規模取決于儀式場合和環節,而不是用樂對象的身份、地位和社會等級。四廂樂所體現出的等級觀念已明顯弱化。
其三,應用范圍不同。周代禮樂廣泛用于吉、賓、嘉等禮儀場合,尤其是祭祀。可以說,周代的禮樂制度,在士以上階層的吉禮中得到最充分、最典型的展示。而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吉禮用樂,雖然也備有樂懸,但是“簡宗廟廢祭祀”的情況時有發生,即使逢祀“宿懸”,也常“懸而不樂”。反倒是僅用于賓、嘉禮儀的四廂樂,伴隨著朝會、元日大會、冠禮等,在晉及宋齊間廣泛應用。這一點從《晉詩》中留存的諸多四廂樂歌便可見一斑。
結 語
“禮樂”,是中國古代統治階級的重要之事。統治者在獲取政權后都要制禮作樂,在昭示正統地位,彰顯文治武功的同時,更重要地是尋求國家和百姓的文化認同。即使兩晉南北朝時期近四百年的社會動蕩和民族融合,禮樂建設也沒有完全停止。戰亂和割據反而使人們對“禮”、對華夏正聲的渴望日趨強化,作為少數民族的北魏也不例外。在這樣的歷史與文化背景下,新的五禮制度在這一時期孕育發展,它與先秦五禮、兩漢士禮有著不同的內容;與禮密切相關的“樂”,自然出現了新的特點,人們將吉禮祭祀用樂原則稍加改變用于賓嘉之禮,形成四廂樂制。
四廂樂以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四律,演奏前代保留下來的雅樂及士大夫創作的四廂樂歌,成為兩晉南北朝時期宮廷賓、嘉之禮中的重要禮樂形式,承擔著特殊的禮儀任務,也發揮著特殊的儀式功能。它是兩晉南北朝時期對周禮樂懸的一種“新解讀”,滿足當時統治階級對禮樂理想的向往和追求,顯示出別具一格的時代面貌和時代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