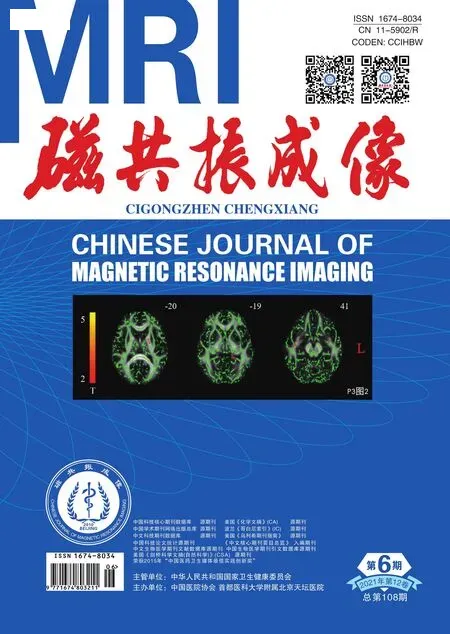1型發作性睡病非快速眼動睡眠期腦網絡拓撲特征及其與認知行為評價的相關性
朱曉宇,倪坤林,譚慧文,劉奕姝,曾尹,郭啟勇,肖莉,3,于兵*
1型發作性睡病(narcol epsy t ype 1,NT1)是一種典型的中樞性睡眠疾病,以白天不可抗拒的嗜睡、猝倒、睡眠幻覺、睡眠癱瘓、夜間睡眠紊亂為主要臨床特點,是一種慢性神經系統疾病[1]。NT1患者通常會出現猝倒和神經肽or exin A(hypocr et in 1)的腦脊髓液濃度急劇下降,這是由于下丘腦中產生or exin的神經元大量丟失所致[2]。
目前針對NT1的多項精神病學研究表明,這些患者具有多種認知缺陷,包括異常的情緒學習[3]、主觀感知的注意力缺陷[4]、缺乏毅力[5]、激活注意和喚醒相關區域的能力不足[6]。
為了探索NT1合并認知障礙的神經機制,最近十多年內開展了多項神經影像學研究,這些研究發現NT1患者雙側海馬、杏仁核[7-10]及左側緣上回[11]存在明顯異常,雙側小腦半球、雙側丘腦、胼胝體和左側顳前內側也存在異常[12-14]。基于腦間連通性的功能磁共振成像(f unct ional magnetic r esonance imaging,f MRI)研究表明,NT1患者的執行注意網絡存在損傷[15]和異常功能連接[16-17],且存在一個能控制情感對情感挑戰反應的替代神經回路[18]。NT1患者皮層神經網絡參與了獎賞和情緒的處理[19],較低閾值[20]或過度激活與猝倒有關[21-22]。另有研究發現,NT1患者大腦連接性和區域拓撲結構的改變與嗜睡、抑郁和沖動行為有關[23]。但是這些研究結果不完全一致,并且評估NT1患者全腦神經網絡整體拓撲特性的研究很少。另外,上述研究尤其是f MRI的研究都是在清醒狀態下完成的。f MRI睡眠狀態下NT1患者腦功能網絡特性研究目前未見報道。
同步腦電-功能磁共振成像技術(el ect r oencephal ogr aphy-f unct ional magnet ic r esonance imaging,EEG-f MRI)提供了一種在睡眠狀態下研究腦功能的無創方法[24]。EEG數據可用于睡眠分期,f MRI數據可以幫助深入了解不同睡眠階段的神經活動[25]。
本研究的目的是采用非侵入性同步EEG-f MRI方法分析NT1患者睡眠狀態下腦功能網絡的網絡拓撲屬性的特征性變化,及其與神經行為異常的關系。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是前瞻性研究。本項研究從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盛京醫院睡眠中心招募了36名右利手NT1患者(男∶女=21∶15;年齡10.0 ~27.0 歲),診斷標準按照國際睡眠障礙分類-第3版(International Cl assif ication of Sl eep Disorders,3rd edit ion,ICSD-3)[26]。另外從社區招募了33名健康對照組(男∶女=19∶14;年齡11.7 ~28.6 歲)。本研究排除了19名參與者:4例NT1患者和3名志愿者退出了夜間多導睡眠圖(noct ur nal pol ysomnogram,nPSG)檢查;7例患者和5名志愿者未能入睡、無法進入N2期睡眠或因頭部運動過大導致無法獲得包含完整睡眠階段的f MRI數據。本研究經過本單位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批準文號:2019PS178J),受試者均已簽署知情同意書。根據赫爾辛基宣言,在研究前所有參與者均簽署了知情同意書并同意參與試驗。
NT1患者的入組標準如下:依據發作性睡病的國際睡眠障礙分類標準,睡眠專家根據持續3個月的白天過多睡眠和明確猝倒史的臨床表現做出診斷。通過nPSG和多次睡眠潛伏期試驗(mul t ipl e sl eep l at ency t est,MSLT)做出最終診斷;利用Epwor t h嗜睡評估量表(Epwor t h Sl eeping Scal e,ESS)測量發作性睡病患者和健康對照組的白天過度嗜睡程度(excessive daytime sl eepiness,EDS)嚴重程度。在ESS測量中,要求參與者從0~3分來描述在8種不同情況下入睡的可能性大小,若總分≥10,則診斷為白天過度困倦[26]。
NT1患者和健康志愿者的排除標準如下:其他睡眠障礙;現患有或既往患有嚴重的軀體或神經系統疾病;常規磁共振掃描發現腦部異常(腫瘤、出血、梗死灶);直系親屬中有嚴重的精神或神經系統疾病史;現患有或既往患有抑郁、焦慮、物質濫用等精神系統疾病;先天性、遺傳性疾病;存在MRI檢查禁忌證。
所有的受試者包括NT1患者和健康志愿者在進行MRI掃描之前均進行了全面的神經系統檢查,用于排除周圍神經系統疾病和中樞神經系統疾病。在開始掃描前,向每一位受試者解釋該研究的全部流程、目的、臨床意義及注意事項。所有參與本研究的NT1患者和健康志愿者均簽署了知情同意書。
1.2 Epwor t h嗜睡評估量表
使用ESS來測量NT1組和健康對照組的日間嗜睡程度。在ESS測量中,要求參與者從0~3分描述在8種不同情況下入睡的可能性大小,若總分≥10,則診斷為白天過度困倦[26]。
1.3 夜間多導睡眠圖與日間過度嗜睡的評估
在參與該研究之前,要求所有患者在一天內禁止喝咖啡或酒精飲料。在MRI檢查前一天,nPSG記錄在呼吸電子系列生理監護系統(Al ice 6,飛利浦,美國佛羅里達州莫里斯維爾)上。nPSG記錄時間為22:00~06:00,包括腦電圖、眼電圖、心電圖等。根據美國睡眠醫學學會指南,記錄標準腦電圖(額區、中央區、枕區腦電圖:F4/M1、C4/M1、O2/M1,備用F3/M2、C3/M2、O1/M2),下頜肌電圖(3個下頜電極和右脛骨前肌中部的肌電圖),眼電圖(EOG位于角膜和視網膜),還有心電圖。記錄口腔和鼻腔氣流、打鼾、胸腹呼吸、血氧飽和度和體位,以及總睡眠時間、睡眠潛伏期、睡眠效率、覺醒和呼吸事件。根據美國睡眠醫學學會手冊,氣流減少≥90%且持續至少10 s定義為阻塞性呼吸暫停,與持續的呼吸努力有關;氣流減少≥30%且持續至少10 s定義為低通氣,并伴有4%或更高的氧氣飽和[27]。呼吸暫停低通氣指數是根據每小時睡眠經歷的呼吸暫停和低通氣事件總數的平均值計算的。所有患者均在nPSG監測后第二天完成臨床MSLT檢查。參照美國睡眠醫學學會特別工作組批準的修改[28],從早晨初醒后2 h開始,每隔2 h安排小睡一次。如果患者在20 min內沒有睡眠,則結束小睡試驗,并記錄睡眠潛伏期為20 min。如果患者在20 min內發生睡眠,則起始時間定義為從熄燈到第一個睡眠時期(包括階段1)的時間。為了評估快速眼球運動(rapid eye-movement,REM)睡眠的存在,在入睡后繼續監測≥15 min。如果REM睡眠存在,則也記錄了REM的潛伏期。然后計算MSLT中5個小睡的平均睡眠潛伏期和REM睡眠潛伏期。
由一位經驗豐富的技師對PSG數據和EEG數據進行分析,其不了解參與者的臨床和人口學狀況。隨后,由一名資深醫生對分析的結果進行核實。依據美國睡眠醫學協會(Amer ican Academy of Sl eep Medicine,AASM)標準,對參與者的睡眠根據睡眠和相關事件的分期進行評分,比如大腦皮層的喚醒和覺醒。各睡眠階段的總睡眠時間(t ot al sl eep t ime,TST)和百分比TST(TST%),非快速眼動(non-r apid eye movement,NREM)(包括N1~N3階段和REM),連同覺醒指數(ar ousal index,A指數,表示觀察到睡眠中斷)。
1.4 北京版蒙特利爾認知評估
使用北京版蒙特利爾認知評估(The Beij ing version of the 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CA-BJ)評估所有被試認知功能[29]。測試包含視空間與執行能力(5分)、命名(3分)、注意力與計算力(6分)、語言(3分)、抽象能力(2分)、延遲回憶(5分)、定向力(6分)等認知領域,總分30分,耗時10 min。得分<26分被認為是認知障礙。
在MoCA-BJ測試期間,斯坦福大學嗜睡量表(St anf or d Sl eepiness Scal e,SSS)[30]用于評估嗜睡程度。在測試前后,所有參與者都填寫了量表。NT1患者在測試前平均得分為1.7 (SD=0.9 ),之后平均得分為1.9 (SD=1.1 )。健康對照組的平均得分在測試階段之前為1.1 (SD=0.5 ),在測試階段之后為1.4 (SD=0.7 )。
1.5 EEG-MRI掃描
在多導腦電圖監測后1周內采集同步EEG-f MRI數據。EEG數據采集采用EGI公司的GES300核磁兼容腦電系統,按照Hydr oCel Geodesic Sensor Net 32 v1.0 系統鹽水電極記錄皮層放電,采樣率為250 Hz,頭皮電阻均小于5 kΩ,連續記錄EEG信號并進行離線處理,并同步使用心電記錄儀記錄心電圖。使用飛利浦Phil ips Ingenia 3.0 T超導磁共振掃描儀進行MR圖像采集。受試者以舒適仰臥位平躺在磁共振檢查床。佩戴防噪音耳塞,并使用泡沫填充固定受試者頭部以減少頭動。本研究中睡眠損害的數量與以前的研究處于同一范圍[31]。為排除腦內明顯的器質性病變,對所有發作性睡病患者和健康對照者均先進行常規軸位T2WI掃描,以聽眥線為掃描基準線,由一名有經驗的放射科醫師在掃描結束后現場閱片。在掃描前告知被試詳細掃描時間,囑咐其在整個掃描過程中不要抗拒睡眠,盡量保持頭部靜止狀態。當被試發出信號表示他們不能再在掃描儀中睡覺時,終止掃描。
使用梯度回波平面回波序列采集f MRI數據,TR=20 ms,TE=30 ms,空間分辨率=3.5 mm×3.5 mm×4 mm,矩陣大小=64×64,FOV=220 mm×220 mm,翻轉角=79°,敏感度編碼因子=2,掃描層數=32層,間距=0 mm。采集的連續體積運行次數為1200次,并在f MRI掃描開始時應用額外的虛擬掃描(持續時間1/8 s)以穩定磁場并消除化學位移偽影。因此,每段的f MRI掃描持續時間為40 min 8 s。
1.6 EEG數據預處理與睡眠分期
使用Net St at ions 5.4 軟件包,去除EEG數據中的梯度和脈沖偽影。按照AASM標準,在不重疊的情況下對預處理的EEG數據進行睡眠分期,每段連續30 s,再由經驗豐富的神經生理學家將其與標準睡眠蒙太奇進行比較。
1.7 f MRI數據預處理
在MATLAB版本R2016a平臺上使用SPM12軟件包對f MRI數據進行預處理。首先對不同層面的f MRI數據進行時間校正。然后將圖像重新對準到第一層圖像以進行頭動校正,并估計每個方向的頭部運動參數(平移和旋轉)。然后將生成的圖像空間歸一化到蒙特利爾坐標系統(Mont r eal Neur ol ogical Inst it ut e,MNI),重采樣的體素為:3 mm×3 mm×3 mm。將高斯核的半高全寬設為6 mm,對歸一化圖像進行空間平滑;對空間平滑后的圖像進行時間濾波(0.0 1~0.1 5 Hz)。最后,使用腦成像數據處理與分析(t he Dat a Pr ocessing and Anal ysis of Br ain Imaging,DPABI)軟 件 包[32](ht t p://r f mr i.org/dpabi)回歸出頭部運動參數、腦室信號和腦白質信號。然后將預處理的數據劃分為連續30 s的段。由同步獲取的EEG數據確定每段對應的特定睡眠階段。對于受試者的每個睡眠階段,f MRI數據的最小可接受長度為8段(4 min)。
1.8 腦網絡結構與圖論分析
使用圖論網絡分析工具箱Gr et na進行拓撲學性質分析,以構建腦功能網絡[33],根據解剖自動標記(anat omical aut omatic l abel ing,ALL)模板將整個大腦劃分為90個皮質和皮質下區域[34],并提取了90個區域的平均時間序列。對所有90個區域的平均時間序列計算每對區域的皮爾遜相關系數,利用Fisher的Z變換將數據轉化為認為具有正態分布的Z值。然后根據相關矩陣的選定閾值范圍,構造一個正二進制向量連接較少的通用網絡。轉換后,將每位受試者分配給相同睡眠階段的Z評分相關系數平均(圖1)。

圖1 參與者的腦網絡構建Fig.1 Construction of brain network in the participants.
使用圖論分析來評估全腦的拓撲和組織特性,分別計算全局效率(gl obal ef f iciency,Egl ob)、局部效率(l ocal ef f iciency,El oc)[35]和小世界屬性[36]。稀疏度用作相關系數閾值范圍的相關度量,相關系數閾值范圍定義為圖中可用邊緣的數量除以最大可能邊緣的數量。根據先前的研究[35],與具有最小數量的隨機網絡相比,將功能網絡的稀疏性和Pear son相關閾值都設置在0.0 5~0.5 (以0.0 5步長)的范圍內,以獲得更有效的泛在網絡。
1.9 數據分析
本研究使用IBM SPSS 17.0 版軟件對常規數據、認知數據、腦功能網絡數據及睡眠監測數據進行分析。使用Kol mogor ov-Smir nov檢驗對連續變量進行正態假設檢驗。首先進行描述性統計。具有正態分布的連續數據表示為均值±標準差,非正態分布的數據以四分位數區間的中位數表示。這些數據包括年齡和問卷得分,根據這些變量的正態性和同方差,在NT1患者組和健康對照組之間使用t檢驗或Mann WhitneyU檢驗進行比較。采用χ2或Fisher精確檢驗,比較不同群體之間的性別比例。退出的受試者的人口統計學特征與留下來的受試者的人口統計學特征也進行了比較。采用t檢驗或Mann-Whit neyU檢驗比較兩組睡眠期間的PSG數據和腦功能網絡的拓撲參數。采用Hol m-Bonf er r oni法對多重比較進行校正,校正后P<0.0 5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Spear man的相關分析用于探討NT1患者MoCA與腦f MRI功能網絡的網絡拓撲屬性之間的關系。P<0.0 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本研究包含25例NT1患者和25名健康志愿者(共50名參與者)的人口統計學、PSG、MoCA-BJ量表和影像學數據。兩組在年齡、性別和受教育年限上相匹配。健康對照組:年齡(22.5 ±3.8 )歲,男性15人,受教育年限(12.5 ±5.0 )年;NT1患者組:年齡(22.4 ±6.9 )歲,男性16例,受教育年限(11.9 ±4.7 )年。NT1患者組的MoCA-BJ評分(25分)顯著低于對照組(30分)(P<0.0 01)。
2.1 PSG數據
與對照組相比,NT1組在TST期間N1和N2的百分比顯著較高(t=8.4 79,校正后P<0.0 01;t=3.4 26,校正后P=0.0 01),而在N3期的TST%顯著降低(t=4.6 55,校正后P值<0.0 01)。NT1患者的A指數明顯高于對照組(t=10.6 30,校正后P<0.0 01)。但與對照組相比,NT1組的TST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 5)(表1,圖2)。

表1 NT1組和對照組夜間睡眠各參數比較Tab.1 PSGdata in NT1 participa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圖2 組間TST%和腦拓撲參數的比較。A:與對照組相比,NT1患者在TST期間N1和N2的百分比顯著較高(t=8.4 79,校正后P<0.0 01;t=3.4 26,校正后P=0.0 01),在N3期間的TST%顯著降低(t=4.6 55,校正后P<0.0 01);B:與對照組相比,NT1患者的整體效率和小世界屬性明顯降低(Bonferroni correction,P<0.0 5)Fig.2 Comparisons of TST%and cerebral topological parameters between groups.A: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atients with NT1 disorder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percentage of N1 and N2 during TST(t=8.4 79,Pcorrected<0.0 01;t=3.4 26,Pcorrected=0.0 01)and significantly lower TST%during N3(t=4.6 55,Pcorrected<0.0 01);B: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atients with NT1 disorder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global efficiency and small-world attributes(Bonferronicorrection,P<0.0 5).
2.2 圖論分析
與健康對照組相比,NT1患者的全腦全局效率以及小世界性明顯降低(P<0.0 5,表2)。在N2睡眠期,NT1患者的全腦全局效率,發病時間與MoCA-BJ得分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r=-0.5 89,P=0.0 02;r=0.6 32,P<0.0 01)(圖3)。

表2 NT1組和健康對照組的腦功能網絡參數Tab.2 Brain functional network parameters in NT1 participa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圖3 NT1患者全腦功能網絡全局效率,發病年限和MoCA評分之間的關系。A:NT1患者全腦功能網絡全局效率與N2睡眠階段的疾病持續時間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B:N2睡眠期NT1患者全腦功能網絡全局效率與MoCA評分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Fig.3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lobal efficiency of the whole brain functional network,and years of onset,and MoCA score in NT1 participants.A: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global efficiency of the whole brain functional network,in patients with NT1 disorder,and disease duration in the stage N2 sleep;B:There was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global efficiency of the whole brain functional network,in patients with NT1 disorder,and MoCA score in the stage N2 sleep.
3 討論
本研究發現在nPSG監測中,NT1患者的N1期和N2期比例較高,這與以前的研究一致[37]。由于嘈雜的環境,參與者難以在MRI掃描過程中到達N3期,并且本研究只有f MRI掃描的N2期數據能夠分析,因此本研究僅分析了N2睡眠期的f MRI數據。
3.1 研究發現
本研究發現,NT1患者在N2期睡眠期間全腦全局效率以及小世界性低于正常對照組。數據表明,全局效率與發作時間呈正比,并與認知障礙的嚴重程度相關。由于腦功能網絡的整體效率主要受網絡內長距離連接的影響,因此筆者推測,睡眠期間腦網絡的拓撲效率降低可能主要是由于長距離功能連接異常所致。這些腦網絡拓撲效率的異常可能與先前在靜息狀態研究中發現的幾個腦網絡之間的連接異常有關,包括執行網絡和顯著性網絡的連通性改變[16]、默認模式網絡的破壞[38]、視覺網絡的功能連通性增加以及顯著性網絡和默認模式網絡的重構[23]。之前的研究發現,大腦在靜息態下感覺運動網絡,包括體動網絡、視覺網絡、聽覺網絡以及協會網絡,包括默認模式網絡、背部注意網絡、腹部注意網絡、語言網絡、額頂網絡、硬腦膜網絡、顯著網絡、頂葉記憶網絡、內側顳葉網絡、頂枕網絡始終表現出恒定的神經功能活動[39]。因此,NT1患者的睡眠狀態下腦功能網絡的低效率很可能導致睡眠狀態下信息處理能力的下降,進而擴展到清醒狀態,導致認知障礙。
本研究發現,NT1患者在N2期睡眠狀態下全腦功能網絡低效,而且這種低效與發病時間的長度呈正比,與認知功能障礙的嚴重程度相關,這可能是由疾病的進展或疾病造成的睡眠異常而引起的。考慮到大腦在睡眠狀態下依然有恒定的神經活動,所以NT1患者睡眠狀態下腦功能網絡的低效很可能導致睡眠狀態下信息處理能力的下降,進而延續到清醒態,導致認知功能障礙。
3.2 局限性
盡管本研究提供了睡眠期間NT1患者腦功能網絡異常的初步證據,但該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1)NT1疾病患者的數量有限,結果的可靠性有待加強。(2)患者的年齡分布較大,結果的代表性有待提高。(3)本研究僅分析了N2睡眠階段的f MRI數據。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NT1患者在N2睡眠期全腦功能網絡效率降低,而這種全腦功能網絡效率降低可能與他們的認知障礙有關。
作者利益沖突聲明:全體作者均聲明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