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氣味
莫 言
我喜歡閱讀那些有氣味的小說。我認為有氣味的小說是好的小說,有自己獨特氣味的小說是最好的小說。能讓自己的書充滿氣味的作家是好的作家,能讓自己的書充滿獨特氣味的作家是最好的作家。
一個作家也許需要一個靈敏的鼻子,但僅有靈敏的鼻子的人不一定是作家。獵狗的鼻子是最靈敏的,但獵狗不是作家。許多好作家其實患有嚴重的鼻炎,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寫出有獨特氣味的小說。我的意思是,一個作家應該有關于氣味的豐富的想象力。一個具有創造力的好作家,在寫作時,應該讓自己筆下的人物和景物,放出自己的氣味。即便是沒有氣味的物體,也要用想象力給它們制造出氣味。
當然,僅僅有氣味還構不成一部小說。作家在寫小說時應該調動起自己的全部感覺器官,你的味覺、你的視覺、你的聽覺、你的觸覺,或者是超出了上述感覺之外的其他神奇感覺。這樣,你的小說也許就會具有生命的氣息。它不再是一堆沒有生命力的文字,而是一個有氣味、有聲音、有溫度、有形狀、有感情的生命活體。我們在初學寫作時常常陷入這樣的困境,即許多在生活中真實發生的故事,本身已經十分曲折、感人,但當我們如實地把它們寫成小說后,讀起來卻感到十分虛假,絲毫沒有打動人心的力量。而許多優秀的小說,我們明明知道是作家的虛構,但卻能使我們深深地受到感動。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我認為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我們在記述生活中的真實故事時,忘記了我們是創造者,沒有把我們的嗅覺、視覺、聽覺等全部的感覺調動起來。而那些偉大作家的虛構作品,之所以讓我們感到真實,就在于他們寫作時調動了自己的全部的感覺,并且發揮了自己的想象力,創造出了許多奇異的感覺。這就是我們明明知道人不可能變成甲蟲,但我們卻被卡夫卡的《變形記》中人變成了甲蟲的故事打動的根本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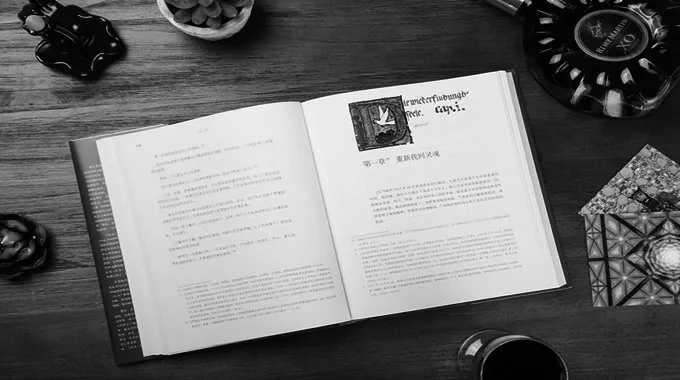

自從電影問世之后,人們就對小說的前途滿懷著憂慮。五十年前,中國就有了小說即將滅亡的預言,但小說至今還活著。電視機走進千家萬戶后,小說的命運似乎更不美妙,盡管小說的讀者的確被電視機拉走了許多,但是依然有很多人在讀小說,小說的死期短時間也不會來臨。互聯網的開通似乎更使小說受到了挑戰,但我認為互聯網僅僅是提供了一種另類的寫作方式與區別于傳統圖書的傳播方式而已。
作為一個除了寫小說別無它能的人,即便我已經看到了小說的絕境,我也不愿意承認;何況我認為,小說其實是任何別的藝術或是技術形式無法取代的。即便是發明了錄味機也無法代替。因為錄味機只能錄下世界上存在的氣味,而不能錄出世界上不存在的氣味。就像錄像機只能錄下現實中存在的物體,不可能錄出不存在的物體。但作家的想象力卻可以無中生有。作家借助于無所不能的想象力,可以創作出不存在的氣味,可以創造出不存在的事物。這是我們這個職業永垂不朽的根據。
當年,德國作家托馬斯·曼曾經把一本卡夫卡的小說送給愛因斯坦,但是愛因斯坦第二天就把小說還給了托馬斯·曼。他說:人腦沒有這樣復雜。我們的卡夫卡戰勝了世界上最偉大的科學家,這是我們這個行當的驕傲。
那就讓我們膽大包天地把我們的感覺調動起來,來制造一篇篇有呼吸、有氣味、有溫度、有聲音、當然也有神奇思想的小說吧。
讓我們把記憶中的所有的氣味調動起來,然后循著氣味去尋找我們過去的生活,去尋找我們的愛情、我們的痛苦、我們的歡樂、我們的寂寞、我們的少年、我們的母親……我們的一切,就像普魯斯特借助了一塊瑪德萊娜小甜餅回到了過去。
我國的偉大作家蒲松齡在他的不朽著作《聊齋志異》中寫過一個神奇的盲和尚,這個和尚能夠用鼻子判斷文章的好壞。許多參加科舉考試的人,把自己的文章拿來讓和尚嗅。和尚嗅到壞文章時就要大聲地嘔吐,他說壞文章散發著一股臭氣。但是后來,那些惹得他嘔吐的文章,卻都中了榜,而那些被他認為是香氣撲鼻的好文章,卻全部落榜。
臺灣的布農族流傳著一個故事,說在一個村莊的地下,居住著一個嗅覺特別發達的部落。這個部落的人善于烹調,能夠制作出氣味芬芳的食物。但他們不吃,他們做好了食物之后就擺放在一個平臺上,然后,全部落的人就圍著食物,不斷地抽動鼻子。他們靠氣味就可以維持生命。地上的人們,經常潛入地下,把嗅味部落的人嗅過的食物偷走。我已經把這個故事寫成了一部短篇小說。在這篇小說中,我是一個經常下到地下去偷食物的小孩子。小說發表之后,我感到很后悔,我想我應該站在嗅味部落的立場上來寫作,而不是站在常人的立場上來寫作。如果我把自己想象成一個嗅味部落的孩子,那這篇小說,必然會十分神奇。

(選自《小說的氣味》,春風文藝出版社2003年8月,有刪節)
【作者鏈接】
莫言,中國當代作家,首位中國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鄉土情懷是他文學作品中所關切的情感體驗;從文學之旅中尋根,是莫言通過小說創作所獲得的歸屬感。受六朝志怪、唐傳奇、明清筆記的中國本土魔幻傳統影響,莫言的文學創作以奇人異事的魔幻現實主義手法,用象征、意識流、荒誕的故事情節將復雜的社會現實深刻解剖,構筑起一個神秘又具有鄉土氣息的文學世界。


【思維魔方】
莫言在談論小說的氣味時還說過,“作家的創作,其實也是一個憑借著對故鄉氣味的回憶,尋找故鄉的過程。”這是以作者的角度肯定了小說之于作者的獨特價值。而托馬斯·福斯特在《如何閱讀一本小說》中則站在讀者的角度,與莫言的觀點不謀而合,他認為:“閱讀小說可以讓我們遇到另外一個自己,也許是我們從未見過或不允許自己成為的那類人;可以讓我們身處一些我們不可能去到或未曾關注的地方,又不必擔心回不了家。”
我們為什么仍然需要小說?正如傳達文字的媒介隨著科技發展不斷更迭,影像技術豐富著我們的精神生活之時,我們對小說的閱讀卻沒有停止一樣。“虛構是小說的價值所在”,小說的“出逃”,不僅在于小說世界之于現實的超然或反抗,更在于小說中的文字世界能夠最大限度地跨越時間界限、壓縮時空距離,去聯結作者的回憶與想象,去填補讀者的已知與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