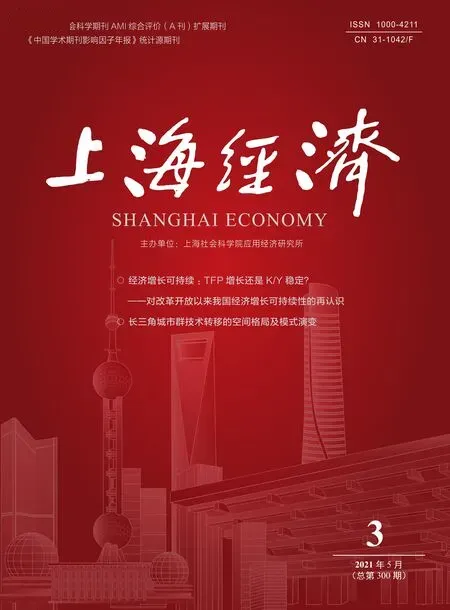經濟增長可持續:TFP增長還是K/Y穩定?
——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再認識
唐雪梅 譚雨欣
(1.同濟大學浙江學院,嘉興 314051;2.中國石油大學(華東)經濟管理學院,青島 266580)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但近年來,經濟增長率出現了較長時間的持續下降,由2007年14.2%的持續下滑到2019年的6.1%(見圖1),持續時間已經超過改革開放后歷次經濟增長率下降時間總和。2019年6.1%的增長率已經低于上輪經濟衰退的谷底增速(7.7%),但仍然高于20世紀80年代兩次衰退的谷底增速(5.1%和3.9%)。中國經濟增長率將會繼續下降,還是可能觸底反彈,或者穩定在目前的增長率,實現L型穩定?這是國內外都非常關心的問題。

圖1 改革開放后我國歷年的經濟增長率(1978—2019)
國外一些學者基于國際經濟增長收斂的框架(Pritchett & Summers,2014;Barro,2016)預測中國經濟增長率可能迅速下降到3%左右。經過幾十年的高速發展,我國已經成功由低收入國家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DP于2020年成功突破了1萬美元大關,但是仍然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挑戰,維持較高經濟增長速度仍然有必要,因此“保增長”也成為我國宏觀經濟的重要目標之一。國內不少學者對中國經濟增長將繼續大幅下降的觀點進行了反駁。劉培林(2015)從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較大的角度,認為中國仍然具有較高速度增長的潛力;蔡昉(2016)雖然承認中國經濟增速下降是因為潛在增長率下降,但認為從供給側進行改革,中國潛在增長率仍然有上升到較高速度的潛力;陶新宇等(2017)認為中國雖然與東亞模式一樣可能經歷“結構性減速”,但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經濟還有更大的增長空間。然而,這些學者雖然強調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但都沒有在理論與實證上分析,如果沒有有效的政策支持,中國經濟目前6%左右的增長率是否具有可持續性。
事實上,預測經濟增長率是否可持續是一個理論與實踐難題。在蘇聯高速增長時期,1961年薩繆爾森在其經典教科書中曾預測,蘇聯將于20世紀80年代超越美國成為第一經濟大國;但蘇聯不僅沒有超越美國,還解體了。相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Krugman)在1994年時就預言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不可持續,但此后中國經濟卻實現了舉世震驚的持續高速增長。正因為判斷經濟增長是否可持續是個難題,也激發了大量的研究。根據索洛(Solow,1956)的增長模型,通過加速資本積累以提高人均資本不可能實現長期增長,只有技術進步才能實現人均收入持續增長。因此,研究經濟增長可持續的框架主要是進行經濟增長因素的核算與分解,從而確定增長因素中可持續與不可持續的比重,進而分析經濟增長是否可持續。目前有兩種基本的增長因素核算方法:一種是基于索洛(Solow,1957)的增長因素核算法。該方法試圖分解技術進步與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并用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簡稱TFP)的增長率代表技術進步率。根據TFP增長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判斷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另一種是基于Klenow and Rodriguez-Clare(1997)的核算方法。該方法重點分解有效人均資本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與非有效人均資本提高的貢獻。在具體經驗測算時,通過將產出增長分為勞動力增長、技術進步與資本產出比(K/Y)三部分的變化,其中K/Y上升反映有效勞均資本提高,重點強調有K/Y上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是不可持續的。
關于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研究主要是受到國際上關于東亞四小龍(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和韓國)增長可持續性研究的影響。多數文獻采用第一種核算方法,即主要考察TFP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東亞是二戰后經濟發展最成功的地區,世界銀行(World Bank,1993)對東亞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進行了總結與推薦,東亞四小龍是東亞地區發展最快最成功的經濟體。但是Kim and Lau(1992)和Young(1995)對東亞四小龍在高速增長期的增長因素進行核算的結果卻表明,它們的TFP增長并不出色,并不優于同期蘇聯的相關結果。克魯格曼(Krugman,1994)因此批評東亞增長只是大量要素投入的結果,與蘇聯的快速增長沒有本質區別,是不可持續的。Young(2003)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因素也進行了核算,得出了與東亞四小龍類似的結果。國內學者對中國的TFP測算的結果也與此類似(顏鵬飛、王兵,2004;鄭京海、胡鞍鋼,2005;郭慶旺、賈俊雪,2005)。受此影響,長期以來,國內學術界的主流觀點是我國經濟高增長的可持續性不足,一直呼吁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劉國光、李京文,2001;吳敬璉,2006)。但是,也有不少學者對TFP增長能否正確測度中國經濟的技術進步表示懷疑(易綱、樊綱、李巖,2003;林毅夫、任若恩,2007)。其實,Barro and Sala-i-Martin(2004)在其經典教材中也指出,TFP即使在測度上沒有問題,也會嚴重低估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還有學者(鄭玉歆,2007;林毅夫、蘇劍,2007)認為,即使TFP正確反映了技術進步而且測度正確,也不能僅根據TFP的增長判斷經濟增長方式是否合理,他們認為經濟增長方式是否合理的關鍵在于是否符合經濟的資源稟賦條件;唐雪梅、林善浪、黎德福(2014)利用新古典增長模型證明了,對于勞動力剩余經濟,沒有TFP增長可能才是合理的增長方式。
Klenow and Rodriguez-Clare(1997)指出TFP增長率判斷經濟增長是否可持續,不符合索洛(Solow,1956)增長模型的原意,并提出了新的核算方法。但是,用這種方法分析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文獻并不多,黎德福、陳宗勝(2007)應用該方法計算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經濟增長,表明效率提高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Zhu(2012)應用同樣的方法也得出類似的結論。但是還沒有文獻用這種方法分析我國近年經濟增長持續下降之后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本文將從理論與案例的角度證明,這種方法比索洛(Solow,1957)的核算方法能更有效地識別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因此將用這種方法作為分析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的工具。
本文后面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對兩種判斷經濟增長可持續的方法進行理論比較分析;第三部分,利用國際案例比較兩種方法的有效性;第四部分,對中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進行具體分析;第五部分,對中國經濟增長偏離穩態的原因與對策進行分析。
二、判斷經濟增長可持續:K/Y與TFP的理論分析
首先,有必要對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概念進行說明。在現有文獻中,包括兩個含義根本不同的可持續概念:一個是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可持續,另一個是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可持續。討論經濟增長是否可持續,首先應該明確討論的是哪種可持續,因為不同的可持續概念需要不同的分析框架,也有不同的判斷標準。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可持續,強調不可再生資源與環境容量對經濟長期增長的限制,主要關注代際公平。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可持續則指由于資本邊際報酬遞減,經濟必然收斂到穩態。只有穩態時的增長率可持續,非穩態時的增長率不可持續。可持續發展理論強調的資本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本,而新古典增長理論的資本是可再生的人造資本。可持續發展理論認為要實現可持續的關鍵是自然資本如何不被持續消耗,而新古典增長模型認為增長可持續的關鍵是如何確保資本不斷積累且回報率不下降。
本文要討論的是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可持續,因為克魯格曼(Krugman,1994)批評東亞經濟增長不可持續,是指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不可持續,而國內學者基于TFP分析中國經濟增長是否可持續,討論的也是新古典增長理論概念中的可持續。另外,雖然滿足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可持續不一定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可持續,但是如果不能滿足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可持續,則一定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可持續。本部分要說明的是,判斷經濟增長從新古典增長理論角度是否可持續,應該依據K/Y是否穩定,而不是TFP增長率的大小。
(一)新古典增長模型的穩態與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模型的核心動態方程是:

(2)式給出了新古典增長模型的核心結論:由于資本的邊際報酬遞減,隨著時間的推移必然有,此時經濟達到穩態,代入(1)式得。(2)式表明,(1)式中是不可持續的部分,是可持續部分。這是新古典增長模型和增長因素核算討論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理論基礎。
(二)K/Y的增長率是經濟增長可持續的判斷依據
從新古典增長模型來看,一個經濟的增長率是否可持續,關鍵在于該經濟是否處于穩態增長路徑,即(1)式中第三項是否等于零。現實中,該項不可能恰好等于零,因此,增長核算的主要任務就是測算出的大小。如果它接近于零,表明經濟處于穩態附近,經濟的增長率是可持續的;相反,則表明現有的增長率中不可持續的部分比較大,目前的經濟增長率是不可持續的。

將(3)式代入(1)式可得:

(三)TFP的增長率可能誤導增長方式是否可持續的判斷
另一方面,以TFP的增長率作為判斷經濟增長是否可持續,可能誤導對實際增長可持續性的認識。盡管存在不同的測算方法估計TFP,但原則都與索洛(Solow,1957)殘差法一致,即如下(5)式:


表1 兩個假想經濟的增長因素 (αK=0.5)
基于索洛(Solow,1957)的核算方法強調TFP增長是經濟增長中可持續的部分,基于Klenow and Rodriguez-Clare(1997)的方法強調K/Y增長是經濟增長中不可持續的部分,原則上二者似乎應該沒有優劣之分。但是,由于資本積累并不完全是外生的,而是內生決定于技術進步與勞動力增長,因此,雖然TFP增長的貢獻部分是可持續的,但要素投入部分并不是完全不可持續的。對于發展中經濟,結構變化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因(王弟海,2021;王海海等,2021)。由于結構變化和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利用,勞動力增長也會誘致大量資本積累。這部分無論從理論還是現實來看都是可持續的。因此僅根據TFP增長的貢獻會嚴重低估發展中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部分,高估不可持續的部分。如果重點核算K/Y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能比較準確地測度出經濟增長中不可持續的部分。
三、判斷經濟增長可持續:K/Y與TFP的國際案例比較
前面理論分析的核心結論是,經濟增長是否可持續的關鍵不是TFP的增長速度,而是K/Y是否穩定。歷史已經表明,蘇聯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西方七國集團成員作為最發達經濟體是經濟增長可持續的典型代表,東亞四小龍(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和韓國)作為落后地區經濟發展最成功的典型,經濟增長是否可持續曾引起爭論。本節通過基于同樣的基礎數據,比較K/Y是否比TFP更能識別經濟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一方面檢驗前面的理論分析,另一方面澄清對東亞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爭論。
(一)蘇聯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蘇聯經濟也曾經有過比較高的增長速度,但后來越來越難以為繼,并最終走向了崩潰。什么原因導致了蘇聯經濟最終走向崩潰是一個大問題,經濟學試圖通過增長因素核算給出某些信息。Ofer(1987)對蘇聯的增長因素進行了比較詳細的分析,本文按照(4)式對Ofer(1987)的數據進行重新計算,報告在表2。

表2 蘇聯經濟增長方式的增長因素構成
表2的結果表明,蘇聯經濟在1950—1970年之間,(4)式中的,也就是(1)式中的,占總產出增長中的比重一直很高,在經濟高速增長的1950—1960年為40.86%,1960—1970年為33%,此后進一步上升,到1980—1985年已經達到131.77%。此后,蘇聯資本生產率持續下降,而且以越來越快的速度下降。根據新古典增長模型,蘇聯的經濟不是由非穩態路徑向穩態路徑越來越近,而是越來越遠。因此蘇聯經濟增長即使在快速增長時期,也有近一半是不可持續的。如果不是計劃經濟體制不計資本回報率地增加投資,蘇聯經濟的增長可能根本不會拖延到20世紀80年代還勉強維持2%左右的增長。
蘇聯經濟的TFP的增長率在1950—1970年還不算低,占產出增長率的比例也在30%左右,遠高于后面的東亞地區。克魯格曼(Krugman,1994)因此認為東亞模式與蘇聯沒有本質區別的原因,但本文認為這只表明TFP的增長無法從根本上區分兩種經濟的增長模式。
(二)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可持續性
西方七國集團(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英國、美國)是世界最發達經濟體的主要代表,經濟增長方式常被視為技術進步驅動的典型代表。本文也按照(4)式對這七國二戰后的經濟增長因素進行分解,結果報告在表3。

表3 部分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方式的增長因素構成(1965—1995年)
表3的數據表明,盡管整體上發達國家的TFP增長對產出增長的貢獻要遠大于蘇聯,但是大部分國家的絕對值也不是很高,比如美國和加拿大在1965—1995年期間的增長率甚至比蘇聯在1950—1970年時還要低,對產出增長率的貢獻率也比較低,加拿大只有15%,美國只有24%。但是,從K/Y來看,發達國家整體都在穩態均衡附近,產出增長率中不可持續的部分,七國平均值為0.60%,占產出增長率的比重只有13.07%,只有英國超過了30%,其他六國都在30%以下。特別是加拿大和美國,從TFP角度來看似乎是七國集團中最粗放式的增長,但距離穩態均衡最近。美國增長率中不可持續的部分只有總增長率的-3.62%,加拿大也只有14.49%。為什么加拿大和美國的TFP比較低?原因是它們的勞動力增長率非常高,遠高于除日本之外的其他發達國家,二者在此期間的勞動力增長率分別達到2.12%和2.08%。
(三)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增長可持續性
東亞四小龍是二戰后東亞地區發展最成功的代表,也是全世界落后地區發展最成功的代表,是世界銀行(World Bank,1993)推薦東亞模式的樣板。但是克魯格曼(Krugman,1994)依據Young(1995)的增長因素核算結果,認為它們與蘇聯的模式沒有本質區別,不可持續,并由此引發了關于東亞模式的爭論。但本文認為,這只是暴露了聚焦于TFP的增長核算的缺陷,基于K/Y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表4基于Young(1995)同樣的數據,但按(4)式對東亞增長方式進行重新分解。
表4的數據表明,正如Young所說,東亞四小龍在高增長期的TFP的增長率與世界其他經濟相比并不起眼,不僅不優于發達國家,甚至不優于蘇聯1950—1970年的情況。特別是新加坡,TFP的年均增長率只有0.2%,韓國也只有1.7%,即使增長率相對較高的中國臺灣與中國香港地區也分別只有2.6%和2.3%,與高達8.93%的產出平均增長率相比,的確非常不起眼。但是,東亞四小龍的高速增長一直處于穩態均衡附近,產出增長率中不可持續的部分平均只有1.39%,占產出增長率的比重平均值15.38%,與發達國家沒有本質區別,與蘇聯則有本質區別。4個經濟體中,只有新加坡距離穩態距離比較遠,不可持續部分接近30%,而其他3個經濟體的不可持續部分則都只有10%左右,與發達國家的情況非常接近。

表4 東亞增長方式的增長因素構成(1966—1990)
總之,通過對發達國家、蘇聯以及東亞四小龍的增長因素進行比較,可以清晰地驗證前面的理論分析。根據K/Y的變化,可以清晰地看出,蘇聯經濟增長中不可持續部分占比很大且越來越大,發達國家與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增長中不可持續部分都比較小。因此蘇聯經濟增長的確不可持續,但東亞四小龍應該與歐美屬于一類,是可持續的。如果根據來觀察,雖然發達經濟總體比較高,但是美國與加拿大在發達經濟中不僅低,占產出增長率的比例也低,也應該歸于與蘇聯一樣的模式,是不可持續的,顯然違背事實。因此K/Y比TFP更能識別經濟增長是否可持續。
克魯格曼根據TFP增長的貢獻,雖然正確地指出蘇聯僅依靠資本積累等要素投入不可能實現持續增長,但忽視了發展中經濟與發達經濟的重要區別,從而對東亞四小龍與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給出了錯誤的預測。如果采用Klenow and Rodriguez-Clare(1997)的方法,根據K/Y的變化率,不僅能夠識別蘇聯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而且能識別東亞經濟增長的可持續。從而能夠既避免薩繆爾森的錯誤,也避免克魯格曼的錯誤。因此,本文將用此方法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進行分析。
四、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基于K/Y的再認識
在前面的理論分析與國際比較的基礎上,下面根據K/Y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可持續性進行分析。我們關注的問題是,中國經濟是否一直處于穩態附近?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經濟增長是變得越來越接近穩態,還是越來越遠離穩態,也就是越來越可持續,還是越來越不可持續?
根據前面的理論分析,K/Y或資本生產率的變化是觀察經濟增長是在穩態附近還是遠離穩態均衡的關鍵。圖2描繪了1952—2019年中國歷年的K/Y。

圖2 中國歷年的資本產出比(K/Y)(1952—2019)
圖2表明,改革開放前,我國的K/Y持續上升,改革開放初期出現了緩慢下降,1994年后再次溫和上升,但1978—2008年整體變化不大,在2.0~2.5之間波動,然而2008年之后,出現了持續地快速上升,由2.5上升到接近4.0。因此,圖2表明,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在1978年前后和2008年前后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但2008年之后出現的顯著變化似乎還沒有引起國內學術界的足夠重視。表5反映了按照(4)式對中國改革開放后增長因素的分解結果。

表5 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增長因素構成(1978—2019)
從表5的數據可以得出以下幾個重要結論:
首先,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整體來看,中國經濟的增長一直處于穩態路徑附近。K/Y上升使產出增長率年均提高1.46%,對產出增長率的貢獻率只有16.32%,與東亞四小龍和發達國家相似,與蘇聯有本質區別。因此中國經濟能夠持續高速增長近40年。同時,TFP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是觀察經濟是否可持續的有效指標。TFP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1978—2019年均值只有32.87%。
其次,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在2008年之后發生了重大變化,但不是更接近穩態,而是更遠離穩態。因此,表5的數據表明,把改革后作為一個整體會掩蓋不同時期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重大差別,特別是2008年之前與之后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有重大不同。首先,盡管1978—1990年TFP的提高并不快,但是增長中不可持續部分很小,只有-0.45%,說明經濟增長基本在穩態路徑。1990—2000年不可持續部分只有3.99%,2000—2008年不可持續部分有所上升,但也只有15.50%。然而,2008—2019年,不可持續部分急劇上升,達到53.24%。這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可能產生不利的影響,應該予以足夠的重視。
這個結果與長期以來國內學術界對我國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認識顯著不同。長期以來,國內學術界的主流觀點是我國經濟處于不可持續的粗放式增長,并一直要求加快轉變。然而,K/Y卻表明,在2008年之前,我國經濟增長非常接近于穩態,不可持續部分非常小。但是2008年之后,經濟距離穩態較遠,不可持續部分較大,卻沒有得到足夠地重視。如果不采取有效政策進行調整,經濟內在力量將可能使經濟增長率進一步下滑,從而影響我國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
五、中國經濟增長偏離穩態的原因與對策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國經濟近年來資本產出比K/Y快速上升,經濟增長中不可持續的部分迅速上升,并占整個經濟增長率的50%以上,表明我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面臨較大風險。而2020年爆發的全球性的新冠疫情對包括我國在內的全球經濟又進一步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盡管部分國家疫苗接種推進速度較快,但廣大發展中國家疫苗獲取困難,而且病毒仍然在不斷變異,世界經濟何時能夠走出疫情的影響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雖然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我國的疫情防控取得了決定性的成功,我國也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正增長的國家,但是疫情之后,如何克服我國經濟中存在的不可持續因素,使經濟重新回復到較高的可持續增長,仍然是一個重要挑戰。
為此,我們認為,首先要對我國經濟增長存在較大不可持續的因素予以高度重視,然后,分析導致中國經濟偏離穩態增長的原因,并采取相應的政策,那么實現較快的持續增長仍然是可能的。我們認為導致我國經濟偏離穩態增長,不可持續部分上升,既有短期性的因素,也有長期性的因素,因此應該同時從短期與長期的角度采取相應的對策。
(一)中國經濟增長偏離穩態的原因
首先,短期因素。主要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及我國應對危機的刺激政策的副作用。在金融危機之前,我國經濟主要通過融入發達國家占主導的國際經濟循環,通過外需拉動經濟,實現了快速增長。但2008年起源于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對發達國家產生了重大影響,導致發達國家的進口能力下降,我國經濟的外部需求急劇下降,使我國經濟的生產能力利用率急劇下降,產出水平嚴重低于潛在產出,從而導致資本的生產率急劇下降。另外,為了應對危機的沖擊,我國政府采取了以“四萬億”為代表的投資拉動內需的緊急應對措施,雖然使我國經濟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快速復蘇,但也導致資本積累進一步加快,資本生產率進一步下降,K/Y在危機后繼續上升。
其次,長期因素。導致資本產出比上升的長期因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我國勞動力由高增長進入了低增長,并在2017年達到頂峰,2018年和2019年已經連續兩年進入負增長。改革開放以來,兩個重要的結構轉換效應基本結束,由于農業部門就業比重已經低于30%,且以老年勞力為主,使農業勞動力向非農部門轉移帶來的結構轉換效應大幅下降;二是隨著體制改革進展,國有部門占比大幅下降,且國有企業效率提高,生產要素由傳統低效率的國有部門向非國有部門轉移帶來的結構轉換效應迅速下降。
(二)促進中國經濟向較高增速的穩態增長收斂的政策
基于中國經濟增長偏離穩態的原因,本文認為使我國經濟收斂到較高的穩態增長路徑,可以從短期和長期分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一方面通過擴大內需,加快構建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發展格局,提高已有生產能力的利用率,提高資本的生產率。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一帶一路”發展倡議帶來的合作機會,與沿線國家進行產能合作,提高國內過剩產能的利用率,從而提高資本的生產率。通過擴大國內國際市場,提高產能利用率,在提高經濟增長的同時降低經濟增長中不可持續的部分。
其次,從長期因素著手,提高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提高資本的生產率,降低經濟增長中不可持續部分。具體措施有:一是進一步利用結構轉換升級的作用。雖然傳統的農業向非農業轉移和國有向非國有的結構轉換效應已經不大,但是我國經濟結構仍然比較初級,各產業內部的結構轉換空間仍然非常大,工業內部由低技術的工業部門向高技術的工業部門轉移,服務業內部由低端服務業向高端服務業轉移,以及農業內部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移的結構效應都具有巨大的潛力;二是雖然所有制的體制結構轉換的潛力已經不大,但是反壟斷和提高營商環境的潛力還很大;三是雖然勞動力數量增長的潛力已經式微,但是通過教育提高勞動力的質量,通過科研體制改革激發科研人員的創新熱情,潛力還很大。
總之,本文通過采用新的方法進行實證研究,揭示在2008年之后,由于國際金融危機以及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我國經濟增長偏離了可持續的穩態路徑,如果不予以重視,經濟增長率有可能進一步下降。但是,只要充分認識到存在的問題,并充分發揮我國的制度優勢,采取有效的短期與長期調控政策,進一步發掘我國經濟增長的有利因素,我國經濟完全能夠重新收斂到較高的可持續增長路徑,繼續實現較快的可持續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