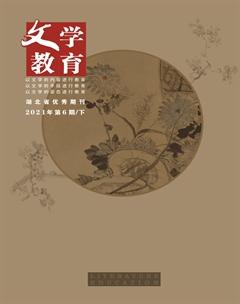杜甫詩中的隱居思想
曾鈦
內容摘要:杜甫曾在唐肅宗乾元二年避亂甘肅秦州、同谷,其間流露出的隱居思想,較以前的淡淡之思大為不同,表現出相比強烈明顯生存意識。本文擬論述詩人此時的隱居思想,兼談其隴右之行。
關鍵詞:杜甫詩歌 隱居思想 隴右紀行 前后對比
杜甫(712-770)是八世紀唐代偉大詩人,他的詩歌創作客觀地反映了時代面貌,被稱之為“詩史”;他的入世思想積極地關心著廣大民眾,后人尊其為“詩圣”。
杜甫身處動亂的年代,加上個人的坎坷經歷,使其詩作有一種命途多舛與懷才不遇的感傷:無論記述生民疾苦、思鄉懷友情念;還是描寫自己窮愁、反觀古今潦倒,大都深邃憂思,雄闊悲憫。特別是中年以后的詩,更蘊含著一種積真聚厚的感情。而這其中所反映出的隱居情思,緩慢深沉,低回起伏,于憂國憂民之外,加有個人的得失不遇。本文擬以杜甫隴右詩作管窺其一二。
天寶十五載(公元756年)前,杜甫過著較為安穩的生活。十五載五月,安史叛軍逼近陜西潼關,打破了這種安穩的生活,詩人被逼逃難,顛沛流離,歷盡艱險,九死一生。八月,杜甫聽說肅宗在靈武即位,便只身北上投奔,至德二載(公元757年)任左拾遺,后改任任華州司功參軍。
乾元二年(公元758年),杜甫在立秋次日作《立秋后題》,其中“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化用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中“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句,含蓄表達辭官歸隱的愿望。是年七月,杜甫因對肅宗信心不足,再加生計艱難,遂辭去官職,遠奔秦州投依族侄,打算過隱居的生活。由此,詩人再一次帶領家眷,踏上漫漫的隴右山路,尋求歸隱夢園。
秦州,即今甘肅天水,位于六盤山支脈隴山的西側,唐時屬隴右道,距今陜西華州一千多里。這里物產豐富,人事雜稠,自古為西北重鎮,東西要沖。杜甫的理想是,在秦州附近的山野,找個幽靜的地方安居度日。“更議居遠村,避喧甘猛虎。足明箕穎客,榮貴如糞土。”(《貽阮隱居》)既贊美隱士阮肪安貧的美德和清高的詩才,更是嘆慨詩人看淡榮華富貴虛名的認識,追求隱逸恬淡生活的情懷。
當時,杜甫的族侄杜佐住在秦州城東南六十里的東柯谷,聽說族叔來到,親來城中拜訪,并邀杜甫前往東柯谷暫住。杜甫雖也心有所動,卻未能找到合適的田宅而作罷。隨后,他又去附近的西枝村勘察可供建宅的地基,也未能如愿,只好客居城中一所簡陋的房屋。這前后奔波中,杜甫目睹廣大人民無論貴賤高低,都身處險地的艱難處境,留下八十余首紀實詩篇。這些詩作大致分兩類:記事懷人和逸情遣興。
在秦州,杜甫以組詩形式,留下大量情感難表現、思緒頗復雜的佳作,較為集中地表現了詩人當時的隱居心境。以《秦州雜詩二十首》為例說明:“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遲回度隴怯,浩蕩及關愁。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其一)寫詩人因戰火生悲,無奈遠游,打算旅居秦州的客觀原因及其愁苦心思。“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對門藤蓋瓦,映竹水穿沙。瘦地翻宜粟,陽坡可種瓜。船人近相報,但恐失桃花。”(其十三)詩人想象東柯谷幽靜安詳,食宿無憂,并將此地比作陶淵明所記的桃源勝地,希望留居此處。“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何時一茅屋,送老白云邊?”(其十四)祈愿一茅屋養老得終;“阮籍行多興,龐公隱不還。”(其十五)借古代隱者說自己惆悵;“野人矜絕險,水竹會平分。采藥吾將老,兒童不遣聞。”(其十六)意在將老隱居,安度余年。以上可見杜甫寓居秦州的隱居思想。
再以這時期的《遣興》詩為例。杜甫在秦州創作旺盛,共存97首詩,其中以《遣興》為題的有十八首之多,如果加上《遣懷》一首,共計十九首,占秦州全詩近五分之一。《遣興二首》:“君看渥洼種,態與駑駘異。不雜蹄嚙間,逍遙有能事。”“渥洼”是傳說產神馬之處,也指代神馬;駑、駘都是劣馬,比喻低下的才能;“蹄嚙”本指馬用蹄踢或用嘴咬,亦引申劣馬,以此代指世俗之人。再借逍遙喻指隱逸。杜甫以此二者相比,傳達自己的清高之性。而“昔者龐德公”“襄陽耆舊間”“陶潛避俗翁”“賀公雅吳語”“吾憐孟浩然”(《遣興五首》)句,以近乎鋪排之筆,列舉“龐德公”“襄陽”“陶潛”“賀公”“孟浩然”等隱逸之士,極力宣揚隱者生活,也正是這種隱居思想的完全流露。
應該說,杜甫在詩中流露的這種隱居思想,正是詩人在安史之亂中屢受生死脅迫,并深為親友的存亡所困現實的必然產物,具有人性的普遍意義。或者說,杜甫的隱居思想并非庸俗消極思想。聯系其先前遭遇,可知詩人其實特想以積極的入世態度來拯救黎民百姓,匡扶危難時局,但在當時混亂殘酷的形勢下,他無法施展才華報復,又不愿同流合污,只有保全生命,隱居觀望。
古代文人大多都有功成身退的隱居思想,杜甫也不例外。但杜甫在秦州時的隱居思想,與這之前大不相同。先以隱士茅屋為例。安史之亂以前,杜甫也寫隱逸之士,“故人昔隱東蒙峰,已佩含景蒼精龍。……鐵鎖高垂不可攀,致身福地何蕭爽。”(《玄都歌壇寄元逸人》)為杜甫給好友隱道士元丹丘所作,全詩從元逸人的住居著筆,先借傳說中仙界典籍意象,描述隱者所居玄都壇的景色,贊揚其修行,再述其服仙家之食,居仙人之居,處于逍遙自得福地,稱頌其超塵脫俗的道行。再讀天寶六載(公元747年)的早期七言古詩:“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友人孔巢父淡薄功名利祿,意在離開長安,求仙問道,堅決歸隱。詩人以縹緲恍惚的語言,濃郁的浪漫主義,贊揚友人高風亮節,表達作者依依不舍之情。這兩首詩雖然都寫山野之景,但都充溢著“凌云之氣”,仙味十足。再結合杜甫后來所作《憶昔行》《昔游》等詩,追憶早年尋仙訪道,欲學長生之術,可見他年輕之時,受時代風習影響,對仙丹靈芝及長生仙界頗感興趣,這與后來的因生活所迫,退而歸隱的思想,迥然不同。
同是寫茅屋,秦州時所做:“塞上得阮生,迥繼先父祖。貧知靜者性,白益毛發古。車馬入鄰家,蓬蒿翳環堵。”(《貽阮隱居》)“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罄舊間,處士節獨苦”“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遣興五首》)等詩中卻看不到一點仙氣,滿篇只有隱者生活的困苦難堪。且在這種困苦的隱居生活中,要達到的目的,也僅僅是謀求在亂世動蕩中保全身家性命,渴望在平凡人世間過上正常生活而已,這絕對與道化神仙的思想是截然相反的。
綜上,杜甫在秦州與以前所表現的隱居思想的不同,也體現了他生存意識的加強,這種思想,對秦州以后的生活和詩歌創作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詩人后來遷移短居同谷,以及后來營建成都草堂,便是這種以生存為主想法的體現。
時光不止,歲月不留。隆冬已迫近,生活愈煎熬。這年十月,幸在秦州南面的同谷縣,有位“佳主人”來信相邀,杜甫遂滿懷希望地放棄秦州,攜家踏上南行之路。同谷,即今甘肅成縣,而邀請杜甫的正是同谷縣令。從秦州到同谷,二百多里的艱難路程,山重水復,迂回曲折。詩人沿途寫成的一組十二首紀行詩,客觀真實地記錄了每一步的艱辛痛苦,并每每由自己的不幸,聯想到戰亂年代流離失所的百姓和生死難料的士兵,憂思不斷地悲吟著“窮年憂黎元”的哀歌,終于到達同谷。
現實,往往比人想象的更加殘酷。盡管杜甫的生活一直不富裕,從“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投簡咸華兩縣諸子》)約略可以概括他十載長安的困頓生活。但與安史之亂前相比,更困頓的階段,則是由華州棄官寓居秦州,再流落同谷的時候。
等杜甫到同谷之后,那位“佳主人”僅待之一飯,就因詩人的落泊,再也避之不見,把杜甫推到更加不堪的流浪境地。詩人無奈地啼饑號寒:“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發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皮肉死。呼呼一歌兮歌亦哀,悲風為我從天來。”(《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白頭亂發的可憐詩人,在白雪茫茫的山野搜撿黃獨(一種可食的土芋),卻往往空手而歸。這種流亡式的生存脅迫,讓詩人對生命意識的加強,對人間的眷戀,自然與一般隱逸閑適的思想完全不同。
理想的樂土,一次次在現實中消失。盡管“平生懶拙意,偶值棲遁跡。去住與愿違,仰慚林間翮。”(《發同谷縣》)十一月初,杜甫迫于生計,只得離開傷心處,“冬季攜童稚,辛苦赴蜀門。”(《木皮嶺》)繼續向成都漂泊。又一路山水行程,險象環生,古老的秦嶺,巴蜀棧道上,留下了詩人的聲聲嘆息、曲曲悲歌。或許,這是他一生當中過的最為艱難的一段日子,他把所歷艱險也吟成一組紀行詩,同樣為十二首。
帶著無限的遺憾,杜甫離開了悲苦漂泊的秦州大地,寂寞無助的同谷山林,也結束了詩人的隴右大地隱居的行程。
參考文獻
1.馮至《杜甫評傳》百花文藝出版社
2.傅庚生《杜詩散譯》陜西人民出版社
3.蕭滌非《唐詩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
(作者單位:甘肅省白銀市白銀區水川學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