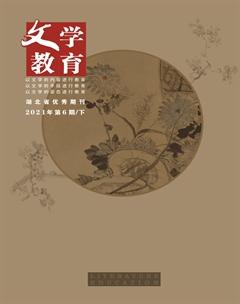荷蘭學界的卞之琳研究語料分析
張天驕 姚穎
內容摘要:卞之琳是重要的中國現代詩人,同時在西方又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以漢樂逸為首的荷蘭學界對卞之琳有深入透徹的研究,出自卞之琳的詩歌充滿東方魅力,但語言又位于西化詩歌的最前沿,這種混搭效果讓讀者深感與眾不同。
關鍵詞:卞之琳 荷蘭 語料分析
《卞之琳》是由詹姆斯·梁(James C.P.Liang)和漢樂逸(Lloyd Lewis Haft)主編的《現代中國語言與文學》(Moder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系列叢書的第三本,主要面對中高級漢語水平的老師和學生。該系列叢書由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研究所(Sinological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Leyden)負責,在歐洲的影響力較大。
一.荷蘭學界對卞之琳詩作風格的評價
卞之琳的一生,與他同時代的許多中國現代文學家一樣:出生并成長于民國初期,脫胎自中產階級,聰明且又年輕。他決意要打造一個新的中國文學和新的中國社會,但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下卻難以得志。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詩人也許是最不幸的,相較于任何其他文學形式,詩歌總是離大眾更遠。在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里,最好的結果也無非就是,詩人得以面對有限的聽眾發表講話。詩歌很少能獲得廣泛的讀者群,除非其已經上升到國際性這一層次,不過每一個國家都多少有幾首詩歌能獲得普遍的贊譽,從而作為國家文化知名度的標志。某些撰寫中國詩人的英文書籍在國外之所以受到歡迎,就是因其得到了外國讀者的認可。
卞之琳經常被拿來與聞一多、徐志摩等新月派詩人相提并論,但他無論在時代劃分還是詩歌發展史上都屬于下一代。漢樂逸所作有關卞之琳的專著最初來自于其博士論文,經過多輪學院式研討,最終將這一實驗性研究濃縮進一本專著中。書中竭盡全力提供了所有可能的信息來源,以供學術界進行任何形式上的審查,同時為了照顧普通的大眾讀者,書中對于早期中國文學中最普遍的典故進行了詳細闡述。漢樂逸的論著結合了文學批評家的話語風格和學院派的語言氣質,他在第49頁“主題和意象”一節中直言不諱:“同樣的思想或同一條邏輯線,在不同的細節尺度上重新表述,就變成了一種自身的類比,在看似不相容的層面上,暗示著經驗之間的形而上學的關系。”就像是許多現代主義詩歌一樣,從廣泛且不同的經驗中獲得隱喻,在沒有傳統詩歌中所期望的那種鏈接情況下,彼此交錯,這無疑是卞之琳詩歌中的一個重要特征。但卞詩本身卻具有一種看似簡單、口語化、甚至是隨意性的特點,這使得詩歌具備了一種獨特的韻味,該方面值得學者作進一步探討。
如果帶著釋然的心情,從權威性的角度解讀卞之琳在20世紀50年代的生活,便會發現其中充滿可讀性和啟發性。漢樂逸認為自50年代末起卞之琳接觸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并開始了對文言詩的改良,且當時的時代主旋律主張參與中國革命的詩人應該多進行白話詩創作。其實這一觀點早在1919年之前就已經產生,朱自清在其1940年的詩集中就有過類似描述。不過在先鋒詩人時代,也有人建議中國現代詩應該重拾文言詩的形式及風格。如同漢代后期五言詩的興起一般,在回歸舊體詩風貌的過程中,詩歌得以迸發出驚人的活力。在20世紀50年代,新詩的創作轉向以西方詩歌為模板,并在發展中獲得了壓倒性的力量。在西化的都市知識分子眼中,于中國革命時期獲得巨大發展的白話詩符合中國傳統文化,因其接地氣的特點在底層民眾中頗得人心,諸如魯迅等知識分子正是借助白話詩在作品中嚴厲地鞭撻當時的舊社會層面。卞之琳在之一時期的詩歌創作中,已經兼具中西特點且貫通古今。漢樂逸建議喜愛卞詩的讀者可以去閱讀古老的樂府民歌,從中了解到卞之琳詩歌創作的靈感來源,同時也須關注通俗易懂的語言表達方式,就好比流行音樂在腦海中浮現一般。出自卞之琳的詩歌充滿東方魅力,但語言又位于西化詩歌的最前沿,這種混搭效果讓讀者深感與眾不同。
在進行創作的時候,卞之琳的詩歌呈現出晦澀難懂的特點,似乎深受其個人經歷的影響。當時的各類公共事件或社會變革吸引了很多同時代詩人關注,但這些主題卻未引起卞之琳的興趣。卞之琳從未公開地詳述其個人經歷,漢樂逸也沒有在闡釋詩歌時做過深入探討。有關卞之琳人生的記載全都是基于可查證的史實和已發生的事件,對于這樣一位內向的詩人來說,人們對其的印象只能浮于表面,這實屬不可避免。
二.漢樂逸筆下的卞之琳
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現代作家與西方學術界的直接接觸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帶來了新發展。遺憾的是,國內研究中存在的制約因素與西方研究中的種種不足,共同招致這一發展中的大部分仍未實現。漢樂逸一直想弄清楚對于這樣一位新中國的知名作家,是否能找到一個獨特的視角去修訂、核實和鞏固其作品。漢樂逸是全面研究卞之琳生平和詩歌的西方第一人并從中受益匪淺,這非常值得稱贊。卞之琳幫助漢樂逸在多個問題上澄清事實并解釋創作技巧,由此漢樂逸才有把握宣稱對卞之琳的評價敢于負全部責任。漢樂逸回憶與卞之琳會面時,卞始終保持其一貫的作風:對事實和細節一絲不茍,同時又小心翼翼地拒絕把自己對詩歌的詮釋強加于人。除了與卞先生的私人討論和書信往來外,漢樂逸還查閱了北京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的重要館藏。毫無疑問,漢樂逸作為一個詩人的實踐經歷也有助于他欣賞卞之琳作品中的優雅和神秘莫測。其結果是,細致且全面的研究打造出一個學習中國現代詩歌所不可或缺的教材。
在序言中,漢樂逸把卞之琳描述為二十世紀中國詩歌界最持久最獨特的詩人之一,認為卞的詩歌解讀難度大,其內涵尚未被完全挖掘。當然這也有其他的原因,卞之琳的一生并沒有受到什么明顯的政治或歷史因素影響。他沒有遭遇過政治壓力,也沒有掌握過重要權力或造成影響。大部分具有他個人特色的作品幾乎都沒有涉及社會因素,他也不鼓勵在文學領域之外進行探究。另一方面,漢樂逸也關注卞之琳作品中的美學品質,并深入研究卞的生活,只是為了探究這位詩人是如何在那個動蕩的時代中生存下來。簡而言之,卞的作品是為數不多的幾本真正關于文學的中國現代文學書籍之一。
論著的前三章描述和分析了截止到20世紀30年代末,卞之琳的詩歌生涯和全部作品,這是該書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在這一時期,卞之琳確立并實踐了白話詩學的美學原則,這是他對白話新詩學的重要貢獻。但卞之琳的詩歌和創作原則在其有生之年影響甚微,不是因為缺乏內在價值,而是歸咎于文學之外的因素。漢樂逸的論述分為兩個部分:文學形式與主題意象。前者是現代漢語英譯本中最詳盡的敘述,更新和完善了徐志摩的開創性工作;后者是漢樂逸所秉持的一個特別有啟發性的分析:詩人的靈感來源是基于人類普遍意識加上其本人的生活經歷總結。西方(特別是法國)象征主義和佛教、道教的形而上學,都引用了卞之琳最優秀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這些章節還簡要介紹了卞之琳的早期生活和所處時代,特別強調了日益增長的日本侵略威脅。在這一背景下,人們可能想更多地了解卞之琳在1935年對日本進行為期五個月的訪問的情況,也有中國學者認為其目的是為抵抗日本帝國主義。
剩下的三章描繪了卞之琳從一個詩人到一個文人的轉變,該部分中最重要的一節是關于20世紀50年代針對詩歌形式的爭論。漢樂逸詳盡地敘述了這場公開的辯論,但對推動這場辯論的派系和個人之論述仍顯不足。1949年之后中國的意識形態斗爭逐漸明朗并凸顯出其復雜性,相關研究在麥克法夸爾(MacFarquhar)的兩卷書和拉格瓦爾德(Ragvald)的著作中有所表述。漢樂逸對該研究中的不完善深表遺憾,因為他沒有向卞之琳仔細詢問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個人生活細節。但即便詢問卞之琳,也不太可能會引起更多回應,同理對于20世紀50年代的權力博弈,也可能同樣問不出什么結果。
漢樂逸的研究對象涉及到各種背景的人,涵蓋比較文學和一般文學,因此在正文中引用的詩歌及其他材料都附有中英對照版本,在參考文獻和附錄中也包含有完整的詩歌引證文本,可供其他漢學家參閱。卞之琳的作品在論著中被多處引用,極具參考價值。除卻論著的優秀框架外,漢樂逸的書受歡迎之處在于其推介了一個被有意無意忽視的中國詩人,相關評價經過深思熟慮且又一針見血,同時又揭示了卞之琳作品在本國和外國文學環境中的定位,并激發了其他學者更多類似的研究。
參考文獻
[1]Liu,Taotao.Reviewed Work:Pien Chih-lin, a Study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by Lloyd Haft[J].The China Quarterly,Jun.1985,(102):346-348
[2]McDougall,Bonnie S.Reviewed Work: Pien Chih-lin: A Study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by Lloyd Haft[J].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1985,1(2):269-270
基金項目:2020年度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項目“關于卞之琳研究的中外語料庫建設”(項目號2020SJA2399)
(作者單位:南通大學杏林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