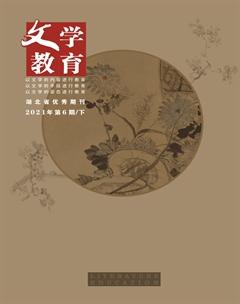從三重人格結構理論解讀《此情可待》
李劉陽
內容摘要:法籍華裔作家程抱一的小說《此情可待》講述的是一幕愛情悲劇。關于愛情,主人公道生和蘭英在不同階段做出了不同的選擇。因此,本文試圖借助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結構理論:“本我”、“自我”、“超我”來分析男女主人公的愛情選擇。
關鍵詞:《此情可待》 本我 自我 超我 愛情選擇
《此情可待》是被譽為“中國和西方文化間永不疲倦的擺渡人”——法籍華裔作家程抱一所作的長篇小說。這部小說以明末清初為時間背景,以男女主人公道生和蘭英的愛情經歷為主線,講述了一則凄美的愛情故事。本文借用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結構理論,通過文本細讀的方法來解析男女主人公道生和蘭英的心路歷程以及他們所做出的愛情選擇。
一.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結構理論
弗洛伊德,奧地利精神病醫生,著名的心理學家。作為醫生,他在臨床實踐中創立了精神分析療法,獲得很大的成功,并在此基礎上創立了精神分析學說。[1]弗洛伊德在20世紀20年代后對他早期的理論進行了修正,提出了三重人格結構學說。這一理論的基本觀點是,人格也由三個部分組成:伊德(id,本我)、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伊德完全是無意識的,基本上有性本能組成,按“快樂原則”活動;自我代表理性,它感受外界影響,滿足本能需求,按“現實原則”活動;超我代表社會道德準則,壓抑本能沖動,按“至善原則”活動。[2]當本我、自我、超我處于一種和諧狀態時,人格才會健康發展;反之,人的心理就會失常。弗洛伊德指出,能夠使這三者協調具有健康人格的人可謂鳳毛麟角。日常生活中,人類的潛意識本能地追求享樂,當“本我”處于支配地位時,就會不惜一切代價來滿足本身的需要,往往無視一切道德規范;而在藝術活動或文學創作中及其他精神活動中,“自我”尤其是“超我”便占據了支配地位,人便會用道德來約束本能。[3]因此當這三重人格結構中的一種占據上風時,人的選擇就會做出相應的改變,去順應其原則活動。
二.本我之下——道生不計后果追求愛情
伊德(id,本我)不受理智和邏輯的法則約束,也不具備任何價值、倫理和道德的因素。它只受一種愿望的支配,就是遵循快樂原則,滿足本能的需要。任何伊德的活動過程只可能有兩種情形。不是在行動和愿望滿足中把能量釋放出來,就是屈服于自我的影響,這時能量就處于約束狀態,而不是被立即釋放出來。[4]在《此情可待》中,男主人公道生的最初選擇體現出了“本我”人格。
三十年前,盧家老太爺慶祝七十大壽,道生作為樂隊班子成員之一參加演出。在演出過程中,道生對盧家小姐蘭英一見鐘情,從此道生對蘭英念念不忘。三十年后,道生本可以在道觀里靠著占卜和醫術的本領安穩度過此生。但道生心中那顆愛情種子使得他的“本我”人格浮現,并且占據主導地位。道生在“快樂原則”的主導下,拋棄道觀的安穩生活,毅然選擇去尋找蘭英。道生在決定離開道觀時:“此次離開,他不知何時能再回來,也不知是否會再回來。”[5]以及道生在趕往縣城的路上時:“道生的腦中掠過了這樣的念頭:他,一個五十多歲的人了,現在仍然活著,他不畏懼再一次游蕩,雖然他直覺地感到這將是此生最后一次了。那位他要看望的人兒是否仍然在世?”[6]在“本我”快樂原則的驅動下,他不再理智,甚至不清楚自己能否找到蘭英,一切對道生來說都是未知數,但他還是毅然啟程,去努力滿足自己的愿望。
道生找到蘭英后,他的“本我”人格仍在持續。“每天中午,道生都到趙家莊園后門領食。每次他都可以看到他珍愛的面孔,盡管那張面孔經常帶有一層憂傷的白霜,在他眼里有時竟顯得更加動人。每天其他時辰,他都處于等待此特殊時刻的耐心中。”[7]英娘每日的施食行為給道生提供了短暫的窺視機會。道生在窺視英娘的過程中滿足快樂的需求。此時道生全然不在意自己的生活,他每天都去窺視這位有夫之婦,其余時間則一直處在等待中。“本我”人格占據了主導,道生的生活軸心是蘭英。在尋找蘭英的過程和每日短暫的窺視中,道生的快樂需求得到了滿足。
三.自我之下——道生和蘭英的愛情選擇
自我不同于本我,按“現實原則”活動,它受外界影響,充當著本我與外在世界的媒介,起調節作用。自我位于人格結構的中間層,其作用是調節本我與超我之間的矛盾。自我的目標就是以一種合理的方式在最大程度上滿足本我的快樂需求。道生和蘭英的“自我”人格在兩人近距離接觸之后得以浮現。
因為蘭英病重,在大和尚的幫助下,道生被舉薦到趙家為蘭英問診。這一次道生與蘭英更近了,但道生并沒有在“本我”的刺激下失去理智,做出喪失倫理道德的舉動。此時道生的“自我”人格意識浮現。當道生第一次幫蘭英診脈時:“他不發一言的品嘗著觸覺的清涼的感受,不發一言,也不間斷。此時此刻,他是主宰者。所有的一切均出自他的意愿,雖然他確切地知道何處是不可超越的界限。”[8]此刻,對道生來說,他美夢成真,終于體會到了“本我”的快樂。他成為了兩者之間的主宰者,甚至認為他所做的一切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但受到“自我”的調節,即使他此刻占據了天時地利人和,道生也沒有借以診病為由做出逾矩的行為。經過幾次診脈后,蘭英和道生這兩位在三十年前就一見鐘情的有情人終于得以相認。兩人并沒有因情愫復燃喪失理智,而是在最大程度上利用每次診脈的機會合理地去體驗這來之不易的相聚給他們帶來的快樂。道生和蘭英“自我”人格浮現,使兩人不能不顧及倫理道德去放縱他們內心的情感。“每次會見,蘭英的手從帳中伸出,無克制地與道生的手會合。這是他們所能做的一切。他們所做的確為膽大無邊,這是他們知道的。”[9]此時的兩人,一方面做出了膽大無邊的親密行為:緊握對方的手;另一方面他們的“自我”人格意識又不斷地起調節作用,以至于他們并沒有深陷其中,迷失自我。他們的情感僅限于此,這就是他們所能做到的一切。此時在“自我”的調節既滿足了他們的快樂需求,也沒有讓兩人完全淪陷其中。
兩人相認之后,在“自我”的主導下,道生和蘭英學會了如何去把握愛情中的“度”。縱使在熱戀期,因為道德規約,他們不得不克制自己。他們在“自我”的調節下,按照“現實原則”,合理地享受這來之不易的重逢。
四.超我之下——道生和蘭英的愛情升華
“超我”處于人格結構中的最頂層,代表著最理想最完美的部分。“超我”一部分是從“自我”發展起來,常分為良知和理想。“超我”受道德原則的支配,其職能在于指導“自我”、抑制“本我”,努力達到人類最崇高的至善和最終的理想而不是快樂或現實。[10]在道生和蘭英為愛情做出最后決定的時刻,“超我”的“至善原則”指導他們做出選擇,他們的愛情注定是場悲劇,但他們卻因此都走向了最理想的“善”。
蘭英的丈夫趙二爺發現了道生和蘭英的秘密,但此時趙二爺命不久矣,因此他想一同帶走蘭英。在殺害蘭英的過程中,趙二爺死了,蘭英卻被道生救活了。此時,沒了愛情的絆腳石,他們今后就可以好好在一起了。然而在這個轉折點,蘭英的“超我”人格浮現。在趙二爺死后,蘭英并沒有選擇和道生在一起,而是選擇去庵里過活。英娘開口了:“我這就去觀音谷的庵里過一段日子。這段日子里,我不見人的。”“我懂的。過一些時,我也回到山里去,我在那里等待。”“是啊,等待。中秋我們發過誓,這一生,以至來生,我們都要重逢。什么時候呢?我還不知道,得耐心等待。當前,什么皆不可能,到時上天會做出安排。”道生感到一陣心酸,低聲應道:“是。”“耐心等待。到時候我會捎信給你。那之前。什么也不要做。”“是。千萬要保養你自己。”蘭英眼圈紅了。她沉默了一會,克服了感情,說道:“道生,我這就走了。日出,日落,月缺,月圓,我們一刻也不相忘啊!時時刻刻都在一起啊!”[11]此時道生的“超我”人格也促使他尊重蘭英的選擇。他們各自在“超我”的影響下,都遵循著“至善原則”行動。在這段感情處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時候,蘭英選擇去庵里平心思考。在“超我”的主導下,當唾手可得的愛情變成了無止境的等待,道生做出了最至善的回應——不強求而是耐心等待。
在“超我”的主導下,道生和蘭英雖然至死都沒有再次見面,但是他們的愛情卻達到了最理想的境界:即使不在一起,但是兩個人的心卻永遠在一起,心里最深處永遠都留有對方一個位置,生生世世。他們遵循了“至善原則”,兩位主人公看似分離,但他們的愛卻升華了,這種愛是什么都打不敗的。結局看似悲劇,但何嘗不是他們愛“永恒”的體現!
在《此情可待》中,由于受到“本我”的刺激,道生依照“快樂原則”不計后果地去尋找三十年前一見鐘情的蘭英。在道生和蘭英從相見到相認的過程中,道生和蘭英的“自我”占據主導地位,他們按照“現實原則”選擇合理的方式去溫存他們的愛情。他們既嘗到了愛情的甜頭,也不至于全然不顧社會倫理道德。故事結尾時,本可以就此在一起的兩位主人公在“超我”的影響下,按“至善原則”做出了最善、最道德化的愛情抉擇。他們的情感一波三折,但最終達到了最理想化的境界,他們的愛變成了永恒。
參考文獻
[1][2]朱立元.當代西方文藝理論[M].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
[3]趙平靜,白樺,趙心怡.從弗洛伊德的人格構造理論透視張賢亮的《綠化樹》[J].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04)
[4](美)C.S.霍爾(著),陳維正(譯). 弗洛伊德心理學入門[M].商務印書館出版,1990
[5][6][7][8][9][11](法)程抱一(著),劉自強(譯).此情可待[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
[10]張小芳.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解讀《妻妾成群》[J].名作欣賞,2019(2)
(作者單位:西安外國語大學歐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