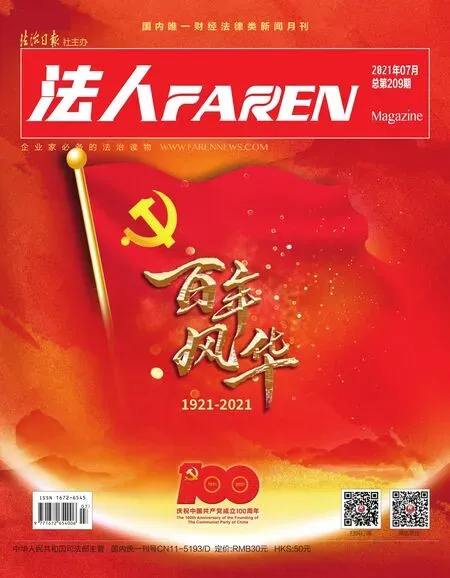寫出性格的吶喊專訪《閃閃的紅星》編劇王愿堅女兒王小瑩
文 《法人》特約撰稿 黃倩
提起中國著名電影編劇、作家王愿堅,相信許多讀者都有深刻印象,他的許多作品被收入小學課本中,比如《黨費》《燈光》《三人行》《七根火柴》《草》等。這些耳熟能詳的作品真實地塑造了那個烽火年代的紅軍形象,影響了幾代人。
靠自學走上寫作之路
王愿堅1929 年出生于山東諸城市相州鎮,1944 年到抗日根據地參加革命工作,1945 年參加八路軍。解放戰爭時,在華東野戰軍第三縱隊的報社任編輯和記者。1952 年,他調到《解放軍文藝》工作。1956 年至1966 年,他參加回憶錄《星火燎原》的編輯工作,1978 年擔任八一電影制片廠編劇、文學部主任,以及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美術系主任。
除了上面提到的幾篇被收入小學課本的文章外,王愿堅的小說代表作還有《糧食的故事》《普通勞動者》《足跡》《路標》《媽媽》《支隊政委》《后代》《趕隊》《珍貴的紀念品》《小游擊隊員》等等。1974 年,他與陸柱國創作了第一個電影文學劇本《閃閃的紅星》,電影中塑造的潘東子形象至今被觀眾津津樂道,他參與創作的《萬水千山》《四渡赤水》等電影也都膾炙人口。他善于刻畫處在歷史大環境背景下,個人信仰的心路歷程以及個人選擇在歷史中的價值,他的許多作品都深刻地反映了這一主題。

王愿堅(1929-1991)
王愿堅并非專業作家,一直利用業余時間寫作。誰也不曾想到,多部作品入選小學課本的王愿堅只有小學文化,全靠自學走上寫作之路。
王愿堅出生于書香門第,其父在京師大學堂讀書,對幾個孩子家教甚嚴,家里文化氛圍很濃。小時候,他的哥哥姐姐上學回來給他講學校的事情,長了很多見識,這種文化熏陶為他的文字功底打下良好基礎。
1945 年,王愿堅小學畢業,當時山東被日本人占領,不得不輟學。王愿堅的小女兒王小瑩對筆者回憶了父親經歷的一件趣事:那時候,學生上學必須給日本國旗敬禮,不敬禮的學生就要挨揍。父親小時候不愿敬禮,幾個孩子把打人的板子扔到茅坑里泡了再曬干,這樣板子一打就斷了。后來家境困難,父親15 歲就不上學了,被送到了根據地。因為小學基礎打得好,每天跟著部隊行軍打仗的同時,他一直堅持寫日記、看書。每打下一個鎮子,他都要去當地逛書店、找資料。有一次在濟南一家書店,他突然找到了一本《辭源》,如獲至寶。老板見他愛不釋手,又見他是軍人就想送給他。不過,父親說,解放軍有紀律,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最后老板只好收了他一塊錢。之后,他就背著這本厚厚的《辭源》繼續行軍打仗。至今,這本《辭源》保存完好。
勤奮執著成就經典作品
據王小瑩講述,進入部隊宣傳隊后,王愿堅自認條件不好,不會演也不會唱,于是開始學習寫話劇。一次,他以在日本俘虜營幫廚經歷寫了一部獨幕話劇,領導看后贊不絕口,這給他增添了極大的創作信心。之后,他又當編劇,又寫快板,還被調去做新聞報道,慢慢走上了寫作之路。
知道自己只有小學文化,王愿堅比別人更加勤奮。因他的哥哥姐姐在蘇聯留學,受到蘇聯文學影響很大。蘇聯文學作品中好人理想、追求公平、勞動人民幸福理念等,都對他日后的創作影響深遠。他一直被稱為“中國革命作家”,蘇聯文學對革命領袖的塑造也影響著他的創作理念。王小瑩說,“父親是個唯美的人,他的作品是理想境界下的文學表達”。

王愿堅小女兒王小瑩(左)與本文作者
1934 年至1937 年,王愿堅從采訪中聽到了許多動人的故事。王小瑩說,父親自認作為一名黨的宣傳員,有責任把這些故事寫出來。對于在優越環境中長大的年輕人來說,太需要讓他們知道老一輩革命者英勇奮斗、不怕犧牲的精神。其中,關于盧春蘭的故事,令王小瑩印象深刻。
山上的游擊隊沒有鹽吃,村里一名叫盧春蘭的婦女組織各家腌咸菜,交給山上來的人帶回去。但是,半路上經常遇到巡邏的敵人,咸菜就會被發現。敵人集合全村村民,以殺戮相威脅,要查出組織者。這時,盧春蘭主動站出來承認。這個故事原型,王愿堅很有興趣,但要將故事變為小說,就需要進行擴充和改編。
對于初次創作小說的王愿堅來說,這著實難住了他。“我幾次把稿紙鋪到面前,卻不得不再收拾起來,我寫不出來。”王愿堅在談寫作經過時回憶道。后來,他想出了一條路:把自己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的經歷融入紅軍故事,以此打通時代內外、融入情感,搭一座橋。他認為,不同的時代肯定有區別,但仍有相通之處。

寫作中的王愿堅
順著盧春蘭的故事,王小瑩繼續對筆者講述,父親剛參加革命的時候,被送到山東老鄉家里當“兒子”做掩護,所在的大娘家里有一個小妹妹。一次敵人掃蕩后,糧食被敵人喂了馬。大家都餓了,大娘找出兩窩頭給王愿堅吃,自己帶著小妹妹往里屋走。等王愿堅快吃完的時候,忽然聽到哭聲。他過去一看,原來是大娘把花生殼咬碎后抹在小妹妹的嘴巴上。看到這一幕,王愿堅心里著實過意不去,這窩頭應該給小妹妹吃。但大娘卻對他說了一句話:“只要有你們在,我們就不怕沒吃的。”這一經歷,便成為《黨費》的其中一個情節——咬碎的花生殼變成小說中孩子想吃的咸菜。
將親眼所見融入進去,王愿堅覺得“故事一下子變得有了生命”。他找到了寫作的竅門:“材料已經不再是聽來的故事,一定要寫下來。”誰也沒想到,這篇處女作日后成為時代經典。
就這樣,王愿堅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創作之路,多部經典小說相繼問世。據他的妻子翁亞尼回憶,王愿堅是個勤奮的人,他深入革命根據地,幾次重走長征路,訪問當地群眾和紅軍老戰士、老赤衛隊員。多年來,他還采訪了100 多位第一次授銜的老將軍和九位元帥。每到一處,凡有革命歷史博物館,他必去參觀,只要看到紅軍題材的歷史資料都會記錄。正是這樣的勤奮與執著,成就了他在文學創作上的成就。
王愿堅和妻子翁亞尼相識于《麓水報》,兩人在最美好的年華一見鐘情,1952 年結為百年之好,攜手走過了30 多年風風雨雨。對于丈夫的創作經歷,翁亞尼說:“自己一覺醒來,常看到丈夫在燈下奮筆疾書。”。

王愿堅、翁亞尼夫婦與大女兒王小京(后中)、次女兒王小冬(后右)、小女兒王小瑩(后左)
敬字為先,敬人敬業
1982 年,王愿堅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一次,他在采訪一位吃過草根樹皮、經歷過九死一生的老領導時,湊巧碰到警衛員進來送參湯。因為老領導說湯涼了,警衛員就順手潑在了外面的地上。看到這一幕,王愿堅心里久久不能忘懷,很不是滋味。他說:“現在條件好了,補的東西就多了,但是人不能只補不瀉(卸),現在是該瀉一瀉了。”這個故事后來被廣泛傳播,成為共產黨人不忘初心的由來。
王愿堅成名后,一直堅持寫作。在他心中始終有一盞不滅的燈,照亮了幾十年的創作道路。調入八一廠后,他從小說創作擴展到劇本創作,其中的經典作品是1983 年的《四渡赤水》。作品塑造了紅軍時代具有雄才大略、平易近人的軍事統帥毛澤東的動人形象,真實地再現了革命領袖挽救紅軍于危難之中的指揮藝術。
創作《四渡赤水》時,因為時間有限,王愿堅只能晚上下班后進行寫作。該劇本由4 位作者參與創作,據翁亞尼回憶,這個劇本一寫就是8 年。最終,該片成為1983 年文化部優秀影片獎,1984年獲第四屆中國電影金雞特別獎。
除劇本之外,王愿堅還從事文學評論。陸柱國評價:“其引人入勝之程度,可以和他的小說媲美,甚至還有所超越。”
王愿堅的創作態度嚴苛,但對身邊的人卻充滿慈愛。他脾氣溫和、待人隨和,常常教育孩子和他的學生說“你要挖井,把水挖出來,如果挖一米深的井挖了10 口,不如挖一口10 米深的井,這樣才能挖出水來”。
王小瑩回憶父親說,他永遠以敬字為先,對外人、家人都很尊敬,人緣非常好。在1980 年發表的《人·人性·人情》一文中,他寫道:“文藝要寫人性人情,這不是奧秘,而是常識。懂得這個常識,我們曾經付出了多么高的代價。”王小瑩表示,父親生在紅色搖籃里,一生勤奮上進、樂于助人,志向高遠、信仰堅定。
王愿堅曾表示,他要寫盡“紅軍英雄志”。但歲月無情,他構思多年的紅軍長征上、中、下三部曲成為生命盡頭的遺憾。1989 年底,王愿堅被查出肺癌,于1991 年1 月25 日去世。他的大女兒王小京是醫生,陪父親走完了生命最后一段歷程。王小京一直記得,在去世前一天,王愿堅還想堅持參加作家周大新的筆會,無奈當天再度發燒,迷糊中他忽然講出一句話:“要寫出性格的吶喊。”第二天,他離開了人世,享年62 歲。
王愿堅曾說過:“為革命而寫作,是我神圣的使命;為革命創作而不斷改善自己、加強自己,也是一項神圣的使命。” 他始終以對黨的初心,融入藝術人生,受到了廣大讀者的熱愛和贊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