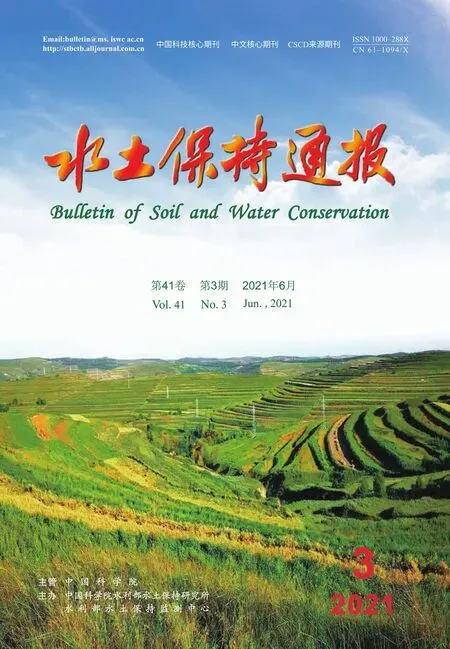青藏高原高寒草原與草甸土壤可蝕性的關鍵因子
魏 寧, 于文竹, 安克儉, 魏 霞, 趙恒策
(1.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理學院, 陜西 楊陵 712100; 2.蘭州大學 資源環境學院, 甘肅 蘭州 730000)
土壤侵蝕是指土壤及其母質在水力、風力、重力和凍融等外營力作用下被破壞、搬離和沉積的過程,它會破壞土壤環境,降低土壤肥力和質量,造成生態環境惡化等一系列危害,如今土壤侵蝕儼然已成為影響生態環境的世界性災害問題。土壤可蝕性是定義土壤是否容易遭受侵蝕影響的關鍵指標[1],也可以直接判斷土壤抵抗侵蝕能力的高低,反映了土壤對外營力剝蝕和搬運的敏感性與易損性[2],是引起土壤流失的關鍵所在,也是定量研究土壤侵蝕的基礎[3]。由于土壤可蝕性不是結構簡單的定向指標而是復雜的綜合性因子[4],因此受到多種影響因素的共同作用,只針對個別指標展開的土壤可蝕性評價往往較為片面[5],因而評估土壤可蝕性的影響因素需涵蓋全面。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們對土壤侵蝕做了大量研究。有研究表明,土壤侵蝕受土壤理化性質的顯著影響[6-8],如土壤容重、機械組成、孔隙度和含水率等變化[9],會引起土壤結構穩定性發生變化,進而影響土壤可蝕性強度[10-13]。還有研究表明土壤有機質是土壤中各種物質的膠結劑[13],可以顯著降低土壤可蝕性[14],并表明相關的生物措施可以有效提高土壤抗沖和抗蝕能力[15-16]。陳佩巖[17]、Levy G J等[18]、Six J等[19]在研究中表明,土壤團聚體的數量、特征可以反映土壤結構的穩定性和可侵蝕能力[18],土壤團聚體的粒徑分布及穩定性也可作為量化土壤可蝕性能力的間接指標,因此土壤團聚體穩定性大小和土壤侵蝕關系密切,可作為侵蝕的有效指示因子[19]。
青藏高原位于中國西南部高寒地帶,是三江源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主體部分,也是生態系統最敏感的地區之一,其任何變化對中國乃至亞洲、全球的氣候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目前,開展土壤可蝕性的研究區域主要分布于黃土高原地區[20]及華中水土流失嚴重的地區,在青藏高原開展的相關研究并不常見,用于評價土壤可蝕性的因子也相對較少,所以導致在青藏高原開展的相關研究存在一定的區域性與局限性。近年來,隨氣候環境變化,青藏高原地區生態環境問題逐漸凸顯,因水土流失導致草地退化的面積逐年增加,高寒草原與高寒草甸作為青藏高原草地的主要植被類型,研究其土壤侵蝕的關鍵因子對青藏高原草地保護具有重要意義[21-22]。因此,本文以青藏高原高寒草原與草甸土壤為研究對象,結合野外調查與室內分析,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從青藏高原高寒土壤可蝕性影響因子中確定土壤侵蝕的主要影響因素,在此基礎上對各主成分進行逐步回歸分析,剔除不顯著與共線性影響因子,篩選通過顯著性檢驗的影響因子,然后經過通徑分析計算來得出各因子與主成分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最終明確影響青藏高原草原與草甸表層土壤可蝕性的關鍵因子[23],此研究將為青藏高原高寒土壤可蝕性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論基礎。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研究區域地處青藏高原中西部腹地,海拔4 200~5 300 m,地勢綿延起伏,四周由唐古拉山、昆侖山、巴顏格拉山和阿尼瑪卿山脈構成新地形框架,被稱為“世界第三極”。屬于典型高寒半干旱氣候,常年氣溫低于0 ℃,空氣稀薄,太陽輻射強且水熱同期。受水熱條件的影響,青藏高原主要植被類型為高寒草原和草甸,其中高寒草原的植被覆蓋度較小、植物多樣性也相對較少,主要為高寒干草原,草原占草地面積約23.22%;高寒草甸面積分布廣,物種豐富度較高,主要的草地亞類有高寒典型草甸草地、高寒沼澤草甸、高寒草原化草甸,草甸占草地面積約76.77%[21]。研究區土壤厚度不大且質地較粗,土粒松散黏度較低,養分貧瘠肥力不高,土地沙化嚴重,是水土流失的重災區。
1.2 樣品采集
于2017年6月和9月進行野外樣品采集,在青藏高原中部沿海拔梯度選取具有植被代表性的采樣點,分別選取典型高寒草原樣點20個、典型高寒草甸樣點11個,共計31個。表1介紹了各樣點的情況。在每個樣地使用環刀采集深度在0—10 cm的原狀表層土壤,每個采樣點設置3組重復,并使用土樣袋收集土壤1 kg左右,用于容重、孔隙度、含水量等土壤孔隙特征的測定及土壤團聚體、土壤粒徑分布等其他土壤理化性質的測定。

表1 采樣點分布概況
1.3 試驗方法
采用環刀法測定土壤容重[24],土壤含水量、土壤孔隙度及土壤飽和導水率的測定方法見趙恒策[23]的研究。采用濕篩法[25]分別測得各粒級團聚體含量,并由此計算得出各團聚體穩定性指標[26-27]。采用激光粒度分析儀(型號為Mastersizer 2000)測定土壤不同等級粒徑含量并將土壤粒徑等級劃分為黏粒(< 2 μm)、粉粒(2~50 μm)和砂粒(50~2 000 μm)。而土壤有機質含量則由濃硫酸—重鉻酸鉀外加熱法測定。
1.4 數據處理
進行相關室內試驗得到數據,分別選取了如下指標:容重(X1)、孔隙度(X2)、含水量(X3)、飽和導水率(X4)、砂粒(X5)、粉粒(X6)、黏粒(X7)、膠粒(X8)、單重維數Dv(X9)、信息維數D1(X10)、WSA百分含量(X11)、平均質量直徑MWD(X12)、幾何平均直徑GMD(X13)、團聚體分形維數D(X14)、結構體破壞率PAD>2(X15)、結構體破壞率PAD>1(X16)、結構體破壞率PAD>0.25(X17)、有機質含量(X18)這18個可蝕性因子,其中X9—X17計算過程見文獻[12,13,25,26,28]。
使用Excel 2016進行數據處理,而主成分分析、逐步回歸分析及通徑分析等統計處理由SPSS 19.0軟件來完成。
2 結果與分析
2.1 高寒草原與草甸表層土壤性質分析
如表2所示,草原和草甸土壤WSA含量,MWD,GMD大小關系依次分別為:草原(86.58%)>草甸(85.6%),草原(1.01 mm)<草甸(1.31 mm),草原(0.72 mm)<草甸(0.89 mm);草原與草甸土壤分形維數D差異不大,其值分別為2.40,2.39。草原土壤PAD>2,PAD>1,PAD>0.25含量為64.13%,51.38%,40.94%,草甸土壤三者含量分別為:61.18%,58.69%,85.6%,草原土壤DV,D1分別為2.46,0.88,草甸土壤DV,D1分別為2.62,0.67,故草甸土壤質地更為緊實,但土壤粒徑均勻性低于草原土壤。草原土壤砂粒、粉粒、黏粒、膠粒含量分別為81.97%,15.02%,3.01%,1.4%,與草原土壤相比,草甸土壤砂粒含量降低了39.5%,粉粒、黏粒、膠粒含量分別提高了65.20%,144.21%,156.41%。

表2 高寒草原與草甸土壤基本性質分析
草原土壤容重為1.53 g/cm3,草甸土壤容重較草原低0.52 g/cm3;草原土壤孔隙度低于草甸土壤;草原與草甸土壤含水量存在較大差異,以草甸大于草原;土壤飽和導水率以草甸大于草原。草甸與草原土壤有機質含量存在較大差異,草甸大于草原。草原與草甸可蝕性影響因子除WSA,D為空間弱變異性、草甸土壤飽和導水率為高度變異性之外,其余因子Cv均處于10%~100%,為中等變異性。
2.2 高寒草原表層土壤可蝕性分析
本文所選取的可蝕性因子存在一定的信息重疊即具有相關性,因此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主要成分進行降維。由表3可知,高寒草原表層土壤經降維后得到4個主成分,其累計貢獻值為86.08%。各主成分主要影響因子見表3加粗顯示部分的數據。根據表3中不同主成分加粗的高信息荷載因子特征,將草原主成分分別命名為:F1土壤顆粒機械組成與孔隙特征因子,F2大團聚體特征因子,F3團聚體結構因子。其中第一主成分的貢獻值最大,為46.54%,因此將土壤粒徑孔隙特征作為草原土壤可蝕性主要影響因素;而第二主成分和第三主成分的貢獻值分別為19.75%,12.19%,且二者均屬于團聚體特征,因此將團聚體特征作為草原土壤可蝕性的次要影響因素;第四主成分無高信息荷載因子且貢獻值及特征值最小,因此后續忽略不計。

表3 草原土壤可蝕性影響因子主成分荷載矩陣
通過主成分分析將可蝕性因子由原來的18維降到4維,對所有可蝕性影響因子進行逐步回歸分析,以完成統計學檢驗,進而分析評價各個因子對主成分的影響。由表4逐步分析結果可知,第一主成分中粉粒(X6)和GMD(X13)通過檢驗,二者均增強了該主成分的影響,粉粒對粒徑孔隙特征影響作用最大;在第二主成分中,膠粒含量(X8),D(X14)和PAD>2(X15)此3個因子通過檢驗,并對該主成分起正向作用,其中PAD>2對大團聚體特征影響作用最大;而在第三主成分中,孔隙度(X2),砂粒(X5),Dv(X9),MWD(X12)和PAD>0.25(X17)通過檢驗,其中MWD和PAD>0.25對該主成分起正向作用,其余指標起負向作用,MWD對團聚體結構影響作用最大;第四主成分中各影響因子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表4 草原土壤可蝕性影響因子主成分逐步回歸矩陣
由主成分分析可得3個主成分,由逐步回歸分析篩選出各主成分通過顯著性檢驗的關鍵因子,通過通徑分析計算這些關鍵因子的相互影響及與主成分的相關作用。分析可知,在第一主成分,即粒徑孔隙特征因子中,粉粒含量和GMD主要起正向直接影響(表5)。其中粉粒含量總決定系數為最大值,且荷載系數最高,因此粉粒可作為粒徑孔隙特征的主要影響因子。在第二主成分大團聚體特征因子中,D,膠粒含量與PAD>2對影響作用較大,且均起正向直接影響,其中D通過PAD>2對該主成分有較大的間接正效應,且破壞率PAD>2總決定系數與荷載系數均為最大值,因此PAD>2可作為大團聚體特征因素的主要影響因子。在第三主成分團聚體結構因子中,通過顯著性檢驗的因子均對該成分影響較大,其中Dv,MWD起正向直接影響,其余為負向,孔隙度、砂粒、Dv和MWD具有雙重效應作用,其中MWD與PAD>0.25總決定系數最大且荷載系數較高,因此可作為團聚體結構因素的主要影響因子。

表5 草原土壤關鍵可蝕性因子通徑分析
2.3 高寒草甸表層土壤可蝕性分析
主成分分析結果可知(表6),高寒草甸表層土壤同樣得到4個主成分因子,累積貢獻值達88.15%,表中各主成分中的荷載較高的主要影響因子以加粗字體格式標識。根據表中各主成分加粗的高信息荷載因子特征將草甸主成分分別命名為:F1粒徑孔隙特征因子、F2土壤穩定因子、F3破壞率因子、F4滲透性能因子。根據各主成分的特征值及貢獻值可以確定,草甸表層土壤可蝕性主要是受到粒徑孔隙特征的影響,其次為土壤結構與團聚體穩定性,最末為滲透性能相關因素。

表6 草甸土壤可蝕性影響因子主成分荷載矩陣
由表7高寒草甸逐步分析可知,在第一主成分粒徑孔隙特征因子中,有容重(X1),粉粒(X6),GMD(X13)和有機質含量(X18)這4個因子通過檢驗,除容重對該主成分起負向作用外,其余均起正向作用,且粉粒這一因子對其影響作用最大;在第二主成分土壤穩定因子中,黏粒含量(X7)與D(X14)通過檢驗,二者均對該主成分起正向作用,且黏粒對土壤穩定特征影響作用最大;在第三主成分破壞率因子中Dv(X9)與PAD>1(X16)通過檢驗, PAD>1起正向作用,Dv起負向作用,PAD>1對破壞率影響作用最大;而在第四主成分滲透性能因子中,分別有飽和導水率(X4),信息維數D1(X10)和有機質含量(X18)此3個因子通過檢驗,且三者均對該主成分起正向作用,這其中,對滲透性能因子影響作用最大的因子為飽和導水率。

表7 草甸土壤可蝕性影響因子主成分逐步回歸矩陣
由高寒草甸關鍵可蝕性因子的通徑分析可得(表8),第一主成分中,容重對該主成分起負向直接影響,粉粒、有機質與GMD則起正向直接影響。其中粉粒直接影響最大、總決定系數最高,且對其余三項均有較大的間接效應,粉粒可作為粒徑孔隙特征因素的主要影響因子。第二主成分中,黏粒和分形維數D直接作用最大,均起正向直接影響,且二者相互作用并無顯著效應,其中黏粒總決定系數及荷載系數最大,因此黏粒因子可作為土壤穩定性特征的主要影響因子。在第三主成分中, PAD>1和單重維數Dv對該主成分具有較大直接影響,其中PAD>1起正向作用,Dv起負向影響。Dv通過PAD>1對該主成分有一定的間接正效應,且PAD>1總決定系數及荷載系數均最大,因此PAD>1因子可作為破壞率特征的主要影響因子。而在第四主成分中,飽和導水率、有機質和信息維數D1對該主成分起較大的正向直接影響。其中D1,有機質均通過導水率對該主成分有較大的間接效應,且飽和導水率總決定系數以及荷載系數均為最大,因此導水率因子可作為滲透性能因子的主要影響因子。

表8 草甸關鍵土壤可蝕性因子通徑分析
3 討 論
由分析可知,在不同植被類型覆蓋下,土壤可蝕性的主要影響因素及主要表征因子存在差異。由主成分分析可知,高寒草原與草甸土壤可蝕性影響因子首要均為粒徑孔隙特征因子,這是由于土壤侵蝕直接反映于土壤顆粒組成的變化,影響土壤質地的粗細程度[11-12]。
本研究表明高寒草原土壤可蝕性主要影響因子分別是:粉粒,PAD>2,MWD和PAD>0.25;高寒草甸土壤可蝕性主要影響因子為粉粒、黏粒、PAD>1和飽和導水率。二者主要影響因子不同,這可能是由于草原、草甸植被狀態不同,導致兩種草地土壤理化性質、土壤結構存在差異[26],在對于抵抗風蝕、水蝕時的抵抗能力也不盡相同。這些基礎土壤指標影響因子可大體代表不同土壤面對外營力及內部作用時的抗沖性及抗蝕性。高寒草甸植被因植被覆蓋較多,植被根系的緩沖、固土作用減少土壤侵蝕,枯枝落葉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相應土壤有機質黏性等均大于高寒草原,因此可知,草甸土壤可蝕性受到有機質的顯著影響,而草原土壤則受其影響較小,這與徐燕等[12]、吳媛媛等[20]、彭新華等[26]在研究中的結論一致,土壤有機質含量多少會不同程度地影響土壤可蝕性大小。劉目興等[29]在研究中表明土壤入滲受到土壤質地、地表植被的深刻影響,草甸土壤根須及腐殖質較多、有機質含量豐富,而草原土壤腐殖質含量較少,因此造成導水效應不同[10,21],其土壤滲透性能對土壤侵蝕的響應作用也存在差異,草甸土壤侵蝕受到滲透性能的輔助影響,而草原土壤侵蝕幾乎不受滲透性能影響;受海拔影響,草原與草甸氣候存在差異。草原平均海拔4 609 m,草甸平均海拔高出草原225 m,高寒草原、草甸地區年均降水量分別為356.46,389.31 mm,年均氣溫分別為-5.11,-6.16 ℃,降水較多,氣溫較低可以使得草甸土壤團聚體的形成與穩定性能強于草原土壤。相關研究表明[27,30],土壤團聚體作為基本結構單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土壤顆粒的數量及分布,而土壤顆粒又是土壤最基本的物理性質之一,因此土壤侵蝕受到土壤顆粒的影響最大、團聚體影響次之,故草原及草甸土壤均受到土壤顆粒及團聚體的影響作用。
4 結 論
本文通過對青藏高原草地的兩種主要下墊面土壤的性質的分析,草原與草甸土壤主要在顆粒機械組成、有機質含量、含水量等方面表現出較大差異,草甸土壤狀態更適合于植被發育。通過對草原、草甸土壤可蝕性因子的主成分分析、逐步回歸分析、通徑分析得出兩種下墊面4種關鍵影響因子。①草原:粉粒、PAD>2,MWD和PAD>0.25; ②草甸:粉粒、黏粒、PAD>1和飽和導水率。青藏高原草地地區可介于此籌劃展開水土保持工作。
致謝:感謝中科院寒旱所何曉波老師和吳曉東老師在野外取樣過程中給予的大力幫助,感謝賀燕同學在室內土壤理化性質分析過程中給予的大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