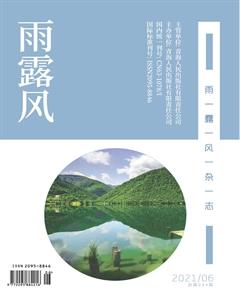母親抗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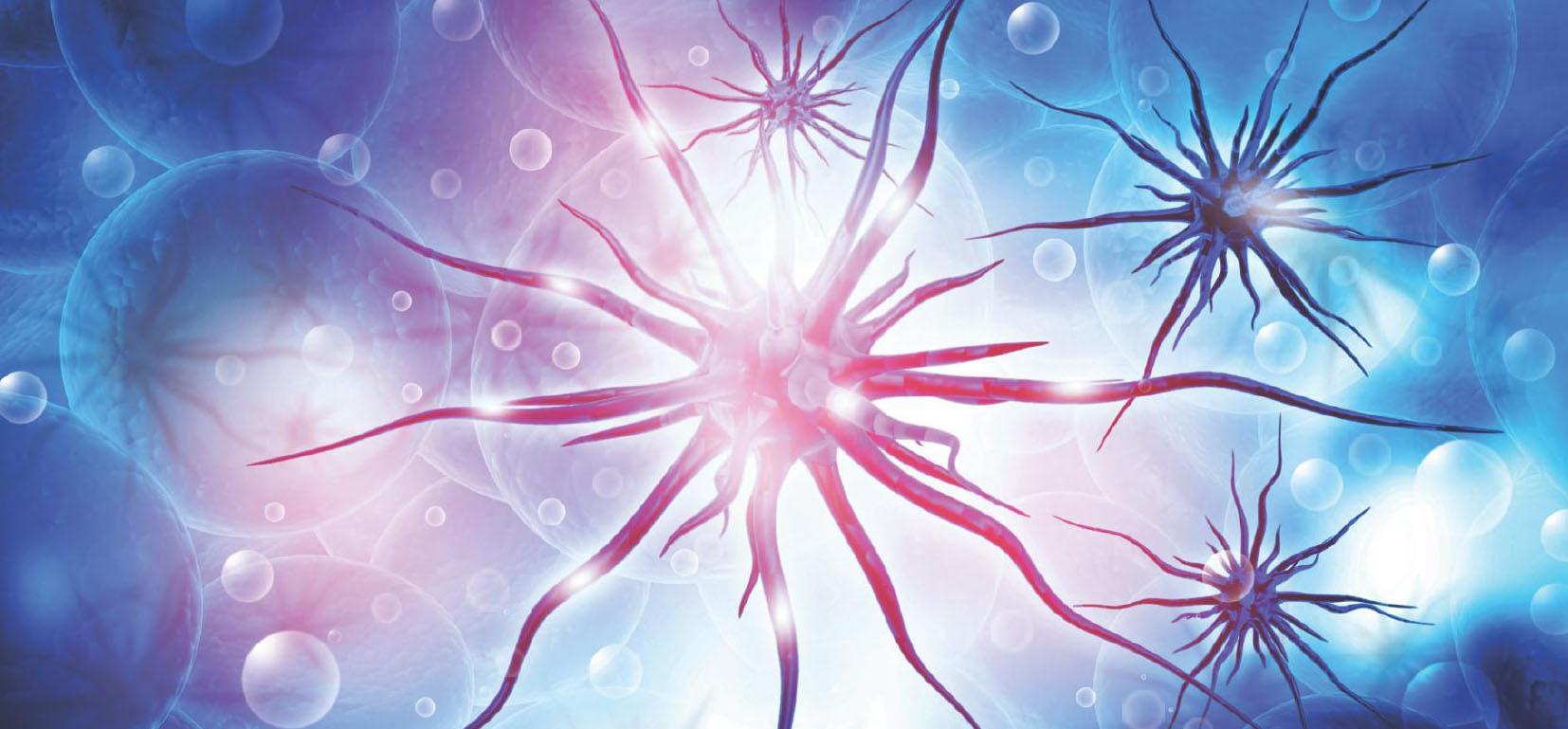


1990年4月,我的第二部醫學專著《實用廠礦衛生保健學》,選題獲江蘇科技出版社通過,開始編寫之初,繁復的主編工作,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偏偏母親這時在體檢中被檢查出了“肺部腫塊”。
母親是個敏感的人,體檢完那天晚上,我下班回家,她問我說:“今天體檢大家都是透視,可是我透視完了,醫生為什么還要求再拍胸片?”我聽了,憑職業警覺,感到不對勁,就糊弄母親說:“大概是透視看不清吧。”當晚我借口外出辦事,去醫院詢問了情況。放射科大夫說:“你母親左肺門部有個1.8厘米×1厘米的陰影,我們懷疑是肺癌,需要復查。”我一下子蒙了。當晚立即找了姐姐和弟弟,然后又連夜去請教資深醫師我的二表哥。他立刻與時任上海第二結核病院院長、肺科專家的妻弟通了電話,共同商定立即去他們醫院,找最有經驗的大夫,給母親做肺組織活檢,先明確病理診斷,再決定治療方案。這樣,我放下手中所有的事,一場搶救母親生命,與死神爭奪時間的戰斗悄然打響。我按照大家的預定計劃,先讓體檢醫院打了假報告,上面寫的診斷是結核球。母親對此深信不疑,因為我祖父和二姑母,還有她的閨蜜,早年都是因肺結核而先后去世的。于是我和姐姐、母親到了上海,借住在四姑母家。
上海第二結核病院,坐落在中山北路虹橋路附近,這兒是一片別墅區,每一幢小巧玲瓏的老別墅,風格迥然不同,或是法蘭西風情,或是英倫風尚,或是西班牙風韻。每幢別墅都擁有一座獨立的花園,池塘里漣漪蕩漾,浮萍朵朵,顯得落寞與靜謐,只有鳥兒們清脆的叫聲,才稍稍添了些許嬉鬧的氣息。如若不是一個個穿著白大褂的醫護人員來回走動,一個個穿著病號服的病人坐在花園凳椅休息,興許我無法相信,在這個喧囂繁華的上海鬧市區,還有著這樣幽雅別致的醫院存在。我雖然喜愛名勝古跡,此時卻全無賞景的心情。
母親入院的目的,就是做肺組織活檢,對可疑的肺部占位性病變,通過穿刺,取出活組織進行病理檢查,明確其性質,從而決定或手術治療,或保守治療。肺穿刺術,當年是在X線定位下,用穿刺針經過皮膚、肌肉、胸膜等組織進入肺部組織,取得組織的一種方法。母親腫塊長在肺門部,這兒血管豐富,如若穿刺不當,會引起致命性大出血。母親是幸運的,穿刺手術由該院頂級的教授操作,術中病理科及時報告,已成功獲取到肺門部的組織,這樣免除了二次受苦。可惜的是,術后并發了氣胸。那個夏天的晚上,母親半臥在床,雖然病房的老式吊扇,在屋頂緩慢轉動,她仍虛汗不止。我用扇子幫母親輕輕扇,不停地用毛巾給她擦汗,直到下半夜,癥狀逐漸減輕,她才小睡了一會。
四姑母家離醫院不遠,我與姐姐都借住在那兒。我們分工,她負責買菜、燒飯、送飯;我是醫生,醫治常規略知一二,所以主要在醫院照顧母親。伯父與四姑母雖然年事已高,但經常來醫院探視。幾位表弟也很給力,有空就來醫院換我休息,所以不感到累。一周后,病理報告出來了,診斷是肺門部低分化鱗癌。對這個結論我是有思想準備的,但真的看到白紙上那幾個刺眼的字,仍心如刀割。我知道,低分化就是惡性程度高,有可能已經轉移了,不及時處理,惡化會很快。來不及傷悲,來不及哭泣,我聽取了上海專家的“回當地醫院手術”的建議,立刻打電話與熟悉的南通醫學院附屬醫院胸外科主任聯系(現南通大學附屬醫院,簡稱通大附院),他讓我立即帶上海醫院的病理報告,安排母親回南通手術。臨行前,我請上海的專家,也給母親開了一份假的病理報告:“結核球”,并讓他們做了母親的心理疏導工作。母親深知結核病的嚴重后果,所以聽從了上海專家的建議,回南通手術。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進行。母親回南通后隨即住進通大附院,主任親自主刀。術中發現,肺門周圍淋巴組織已有轉移,屬中晚期,所以做了根治術。主任對我說:“你母親肺部條件不好,年紀大,長期吸煙,有肺氣腫,再加上這次創面大,馬上還要進行化療,元氣大傷,所以全面恢復會較慢,你們要有長期思想準備。”我迫不及待地請教:“母親能活多久?”主任搖搖頭說:“多則兩三年,少了不好說。”這番對話,我如實向姐姐和弟弟轉告,我們都很難過。母親術后,先在通大附院完成了第一個化療療程,回家休息了一段時間,而后選擇了在南通抗衰老研究中心,完成后續的化療及輔助治療。近半年的系統康復中,母親平安地完成了四次化療,輔以中藥,精氣神恢復不錯。尤其是抗衰老研究中心的血輻射治療技術,當時在全國尚處領先。原理是,癌癥放化療時,血象往往急劇降低,造成治療被迫中斷、影響療效。而同時輔以血輻射治療后,則可以保障放化療的順利進行。此療法操作是,先采集自體血,經低劑量輻射處理,再重新輸入體內,刺激機體造血,迅速恢復血象。母親在醫護人員精心治療下,康復效果很好。母親出院后說:“我這個結核球不是什么大事,驚動了這么多人,過意不去。”她向大家保證,聽醫生話,出院后不再抽煙。煙齡有50年的母親后來真的一支煙都沒抽過。
母親康復回家,我與她共臥一室,她睡大床,我睡鋼絲床。白天我上班,家中請了保姆陪她,還請了一位家庭醫生,負責她的常規治療。我與保姆家庭醫生說定了,在與母親的交流中,一定不能說是肺癌,處方上診斷就寫“結核球術后”。母親在眾人關愛中一天天好轉,口唇不再蒼白,每天在室內來回走動的時間日益增多,呼吸平緩,講話聲音也高了。術后一年,母親可以下樓走走,時而與鄰居打打牌,面色漸紅潤,精氣神好多了。我又恢復了編寫《實用廠礦衛生保健學》,晚上常等母親睡下,關上房門,在飯廳寫作。有幾次后半夜了,母親心疼地起來,催我早點休息。
風和日麗中,可能潛伏著風暴;安詳平靜中,可能暗藏著風險。意想不到的困難、挫折乃至災禍,總會隨時可能發生。母親并不知道,作為子女們,內心始終忐忑不安,就是生怕有一天,善意的謊言會被戳穿。
謊言被戳穿完全出于一個意外,并最終將母親擊垮了。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家庭醫生,按常規每周一下午會來家里巡診一次,搭脈查體,爾后開藥,處方放在家里,我回去拿處方再去醫院繳費取藥,周而復始。那一天下午,家庭醫生將處方開好后,匆忙離開,回醫院開緊急會議。我回家發現母親躺在床上默然無語,背對著我,覺得不對勁。我邊向母親問安,邊拿起處方,見診斷上竟然寫的不是“結核球術后”,而是“肺癌術后”,大驚失色,謊言就這樣被揭穿了。我知道,現在任憑我怎么勸慰,一切都是徒勞。母親的病情被隱瞞了這么久,她配合去上海穿刺活檢,又做了這么大的肺切除根治術,還完成了化療,所有的苦痛都忍受過來,就指望有一天,能走出家門,如往常一樣,自由來往于三個子女家庭,與孫輩們一起歡笑。而處方上的診斷,一下子將她的希望破滅。憑她老人家的聰明和敏感,完全能判斷出不久的將來結果是什么。就從那天開始,母親基本不吃飯菜,就喝些水,中西藥一概不服,偶爾用些麝香保心丸。
看母親一天天在消耗,又沒有能量補進,我實在受不了。一個晚上,關起房門,坐在床邊,握著母親的手說:“一切都是我的錯,我不該隱瞞,不該欺騙您。現在我告訴您實話,癌癥已經切除,化療已經將癌根治了,不會再復發了。只要您多吸收營養,有了抵抗力,您很快就能下樓,就可以去姐姐、弟弟家,也可以去上海去南京親戚家。但是您要吃飯,您要喝藥,這是現在最重要的兩件事,好嗎?求求您了……”我聲淚俱下,盼望母親能聽進幾句,哪怕一句也行。可母親不為所動,面無表情。無奈下,我動員了姐姐、弟弟,姑母等所有親友,大家輪流真誠相勸,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然而效果還是不大。飯菜少吃了一點,但中西藥還是不肯服用。這樣的狀況令我揪心,想了許多辦法,變了好多花樣,見效甚微。她內心到底在想什么?拒絕治療,不進營養,這就是放棄生存的希望,兩年中大家的努力,包括她自己的煎熬,都將付之東流。難道她不明白嗎?
1991年4月,伯父從上海回南通,安葬伯母的骨灰。離通前由四姑母和表弟陪同,來家中專程看望母親,讓母親感動不已。伯父一介書生,學植深厚,與人和善可親,言少而精,語樸無華,繼承了王氏厚德載物的家風。他與我父親情同手足,當年,在父親失業之時,盡全力相助。父親早逝后,他以各種方式對母親予以了關心。1957年大伯被錯劃為“右派”,長達二十余年,自顧不暇,如履薄冰,與族人基本無來往。母親在上海住院時,他來醫院看望過,當時病理報告尚未出結果。而這次他來看望母親,心中是有許多難言之隱。伯父已是74歲高齡,剛剛將伯母入土為安,心存悲切。現又看望身患絕癥的弟媳,夢里歲月,年華長嘆。1943年伯父與父親,兩家人在揚州留有唯一合影。那時他們風華正茂,妯娌亭亭玉立。而今僅留下兩位古稀老人,何況我母親還是危重患者,這也許是倆老人的最后一面了。伯父內心充滿憂傷之感。我準備了薄酒簡宴招待客人。伯父聽說我兒子會拉小提琴,要求拉一曲《梁祝》。琴聲幽幽而起,伯父雙目微閉,兩行老淚流下。多少別緒鳴音,執掌寂寞,千觴不為醉。過往如風,恍若煙波,悵然孑影,今日老人相聚,何日再會,或成別離?場景令我無比動容。
母親的體力越來越差,連下床都較費勁,整天就窩在床上,不言不語,或兩眼看著天花板,或兩眼緊閉。1992年五一勞動節假期,我們一家人團聚,午飯后,她讓姐姐獨自一人進房說話。姐姐出來后兩眼通紅說:“母親讓我去做壽衣。”我們聽后都心如刀絞,淚如雨下。我不知道,母親面對死亡,她究竟是畏懼,還是堅強?從知道了自己是肺癌后,從沒見她流過淚。從理智上說,死亡實質是對晚期癌癥的一個終結,所有人都會如此。從感情上說,我不愿母親過早離去,哪怕多活一天也行。母親的病情急轉直下,又開始咯血了,對癥治療后,咯血控制住,但精神不見好轉。
五月下旬,天越來越熱,母親開始整夜在床上翻來覆去,問她哪兒不舒服,她不言語。見我很晚還在寫作,總關心地催我,你睡吧,明天還要上班。我每天上班前,總用聽診器給她檢查心肺,量血壓,對保姆關照幾句。下班回來第一件事也是聽心肺,量血壓。有天下班后,我問她想吃什么,她脫口而出,想吃“焦麥屑炒蛋”。我一下子蒙了,這怎么做?但還是滿口答應了。焦麥屑,我記得是當年母親在郊區催詩小學上班時,這是她最愛且最方便的夜宵。她在家會用元麥粉,放在鍋里先炒熟,后用瓶子裝好帶到學校去。晚上備課晚了,挖幾勺在碗里,放些紅糖或糖精,用開水一沖,再用蓋子燜一會,然后揭開,頓時香氣四溢,這個夜宵也算是當年的奢侈品了。可眼下農民都不種元麥了,哪來的焦麥屑?再說,焦麥屑也不好炒蛋呀?母親這題目真是無解。我考慮了一下,就先用白面粉在鐵鍋里炒,成了焦黃色后盛在碗里,然后放了紅糖、麻油,用開水沖成了糊狀,再將已炒好的雞蛋搗碎,放到碗里與“焦麥屑”一起攪拌,這樣,母親想吃的“焦麥屑炒蛋”做成了。母親嘗了后,點點頭,給我豎了個大拇指。
1992年7月5日,是周末,全家相聚陪母親。下午姐姐按母親的囑咐,將剛做好的壽衣拿來,讓她過目。母親撐著虛弱身子,仔細看了每一件,摸了又摸,最終滿意地點了點頭,似乎如釋重負。晚餐時,母親罕見地喝了很多的稀粥,還吃了她最愛的肉松。好久不見母親這么開胃,我高興地與弟弟開了一瓶啤酒。吃飯間,母親在房間說要小便,外甥媳婦去攙扶,不一會兒聽她大聲叫喊:“快來人,不好啦!”我趕了進去,只見母親大口喘氣,口角有粉紅色泡沫,身上全是汗水,皮膚發涼,兩眼直往上翻。我馬上用聽診器檢查,聽到雙肺滿是廣泛的濕啰音,心音快而弱,血壓只有80/50毫米汞柱,判斷是急性肺梗塞,十分兇險。我迅速將母親放低頭部,再墊高下肢,以求增加回心血量。我與姐姐、弟弟商量說:“母親很危險,是送醫院搶救,還是在家搶救?送醫院,搬動后可能會就出現意外。在家搶救,我馬上通知醫生。”姐弟都表示不送醫院。母親的頭無力歪躺在我的手臂上,呼吸開始減弱,斷斷續續地說:“我要見你們父親去了,你們不要再辛苦了。”說完頭歪在我的手臂,眼角流下的淚水,滴在我的手臂,還帶著她最后的溫度,時間定格在19點42分。
沒等到醫生上門,母親就安詳地合上了眼。母親在知道病情真相后,不惜用近乎自殘的方式,走完生命最后旅程,是想早點解脫我們,也解脫自己。她在病中沒有掉過淚,而臨終的眼淚告訴我,世上有種堅強是含淚的堅強。在我不惑之年,失去了疼我愛我的母親,悲慟中我也逐漸地理解了她。
母親自小性格活潑開朗,父親過早地去世,成了她一生的拐點。此后她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保護家人;她一生視教育事業為己任,愛學生如同子女。在我五歲時,父親的冤死,使我失去了快樂的童年。從那年起,母親在之后的幾十年中,既為父又為母,對我們子女嚴厲有余,慈愛藏心,用她自己的方式庇護我們,讓我們平安地活了下來。人從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會面臨生與死,而生死由不得我們自己選擇,或是命運早已注定,我們能選擇的是,活著就要如母親一樣,活得有價值。這些感悟,是母親在抗癌的日日夜夜里,用生命告訴給我的。而由我主編的《實用廠礦衛生保健學》,也在母親去世后兩年,正式出版,至今仍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2021年母親忌日定稿)
作者簡介:王其康(1950—),男,江蘇南通人,中專,主治醫師。研究方向:文學,作者系南通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