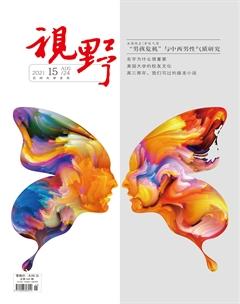數學天才為什么都那么超凡脫俗?
貝小戎

數學是一個很神奇的學科。我兒子上四年級,老師經常強調數學源于生活,要多找機會跟孩子講生活中的數學,不然他們對分米多長之類的沒有概念。《小學高年級趣味數學》中有這么一個數學故事,看上去很生活化:印度有個農民,臨終前對三個兒子說,他留下了19頭牛,老大分總數的二分之一,老二分總數的四分之一,老三分總數的五分之一,這怎么分呢?一個鄰居牽來自己的一頭牛,把自己的加上19,老大分到10頭,老二分到5頭,老三分到4頭,一共19頭,鄰居再把自己的牽了回去。一本書中說,既然加一頭牛后來又牽走了,那么不加一頭也是可以分的:三兄弟分牛的比例是1/2:1/4:1/5=10:5:4。
對文科生來說,小學數學有時候已經很難了。今天小朋友數學作業的最后一題是:一個長方形,如果寬加長4厘米,長增加一倍,面積變成原來的4倍;如果把長減少8厘米,它會變成一個正方形。問它原來的面積是多少?我不知不用未知數怎樣把它講清楚。
畢業于耶魯大學數學系的本·奧爾林在《歡樂數學》中說,偉大的數學家能夠用簡單的思路解決復雜的問題。1920年以前,在所有的數學分支中,代數是最枯燥乏味的。做代數題就像陷進充滿瑣碎細節的沼澤,或是進入充滿細節的荊棘叢。直到1921年,數學家艾米·諾特發表了論文《環域理想理論》。她把“數學”這個概念束之高閣,對她來說,對稱和結構才是最重要的。她教會了同行用簡單、普適的術語進行思考。她愛好徒步,有時會在周六帶學生去遠足。在路上,她常因專注于討論數學而忘了看路,學生們還得保護她。是的,偉大的數學家不太在意人行橫道和車流這種瑣事,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統計學中有一個高斯相關不等式,有些人已經研究它研究了四十年,計算了數百頁。2014年,賓夕法尼亞大學統計學家理查茲收到一封郵件,發件人是德國一位制藥公司退休職員,郵件附件是word文檔,數學家平時用LaTeX程序。這個退休人士證明了高斯相關不等式,而且用的論證和公式非常簡單。
數學應該是對天賦要求最高的研究領域。有一本關于數學定理的書叫《天才引導的歷程》。埃里克·坦普爾·貝爾所著《數學大師》,寫到費馬、拉格朗日、傅里葉等人,標題有“天才與貧困:阿貝爾”,“天才與愚蠢:伽羅瓦”,也有“業余愛好者中的王子費馬”。
在《數學巨匠》一書中,牛津大學教授約安·詹姆斯介紹了60位數學家的生平,歐拉、高斯、黎曼、龐加萊、希爾伯特、康托爾等,其中有三位女性,分別是熱爾曼、柯瓦列夫斯卡婭和諾特。
數學家中有很多看上去有些瘋狂的天才,他們不愿或不會過日常生活。2010年,美國克雷數學研究所為了感謝佩雷爾曼對破解龐加萊猜想的功績,授予他100萬美金的千禧年大獎。可是,這位44歲的數學天才拒絕領獎,他每天甚至緊鎖家門拒不接受媒體采訪。
中國數學會網站2014年有一篇文章,說的是數學界的大神格羅滕迪克去世,享年86歲。他完全改變了現代數學,卻在事業鼎盛期退出數學界,隱居山林。有人說,他聰明得一塌糊涂,也瘋得一塌糊涂。21歲時連續發表6篇論文。盡管被奉為代數幾何的上帝,他的工作狀態就像是數學虔誠的奴仆。格羅滕迪克本人過著一種斯巴達式的孤獨生活,只靠著牛奶和香蕉過日子,每周七天,每天十二小時,將自己完全投入到數學中。他穿過用輪胎做的涼鞋。
1966年,格羅滕迪克獲得菲爾茲獎。但1969年,他突然退出了數學界,因為他發現研究所的一部分資金來源于法國國防部。他創辦了一所名為“生存和生活”的組織,推廣他的反戰和生態保護思想。1991年,移居到比利牛斯山區之前,他燒了很多論文。
Kaja Perina說,格羅滕迪克的思維充分體現了圖靈所說的數學推理,結合了直覺和巧思,他會把問題提升到普遍的高度而加以化解。自畢達哥拉斯以來,人們就在爭辯數學家的瘋狂,牛頓、哥德爾、玻爾茲曼、南丁格爾、納什,在成為著名數學家之前,都曾患有某種精神疾病,如抑郁、妄想癥、精神錯亂帶來的宗教神秘主義。
人的思維有兩個極端,一端是機械認知,關心自然界的法則和物體;另一端是心靈認知,興趣在于破解他人的心靈。自閉癥是機械認知的極端形式。心靈認知的極端形式是精神病,對自我和他人有一些妄想。有的自閉癥患者有很高的智商。有的精神病患者非常有創造力。格羅滕迪克智商特別高,也非常有創造力。“創造性認知和紊亂的思想都缺少過濾無關信息的能力。這種狀態讓更多信息抵達意識,從而把無關的概念聯系起來。”
(何靜楠摘自微信公眾號“貝書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