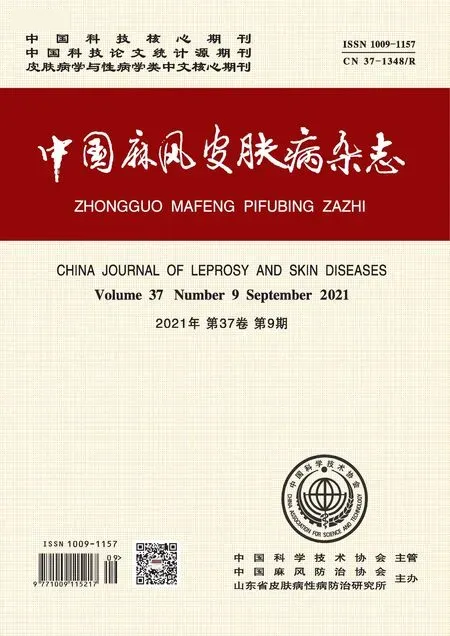分子靶向抗腫瘤藥物皮膚不良反應研究進展
石艾秀 曹雙林
1宿遷市第一人民醫院皮膚科,江蘇宿遷,223800;2南通大學附屬醫院皮膚科,江蘇南通,226001
隨著分子生物學技術日漸成熟以及從細胞受體與增殖調控分子水平對腫瘤發病機制的深入研究發現,幾乎所有惡性腫瘤的發生都與分子水平突變相關,最終導致腫瘤細胞的異常增殖,分子靶向抗腫瘤治療應運而生。靶向治療能為腫瘤患者提供更精確的治療方案,具有特異性抗腫瘤作用,減少對正常組織的損傷, 明顯減少系統不良反應,目前已經成為國內外抗腫瘤治療的熱點,為腫瘤個體化治療帶來希望。但其抗腫瘤作用導致的其他不良反應也接踵而至,其中最常見的是皮膚不良反應。皮膚不良反應的發生會降低腫瘤患者的依從性、影響抗腫瘤療效、增加繼發感染的風險、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甚至增加患者至醫院就診的頻率并加重腫瘤患者的經濟負擔[1]。
雖然患者使用分子靶向抗腫瘤藥物種類不完全相同,出現的皮膚不良反應也多種多樣,但這其中并不是無規律可循。按作用靶點對靶向抗腫瘤藥物進行分類,歸納總結其不良反應類型及嚴重程度,可找出相同靶點分子靶向抗腫瘤藥物致皮膚不良反應的共性及個性,正確認識與管理靶向藥物皮膚不良反應。本文將從細胞膜相關抑制劑、胞內信號通路抑制劑及免疫檢測點抑制劑三個方面綜述靶向藥物的皮膚不良反應(表1)。

表1 靶向藥物不良反應總結
1 細胞膜相關抑制劑及皮膚不良反應
細胞膜相關抑制劑主要抑制相關受體及激酶的活性或與其爭奪配體而發揮作用。其中,表皮生長因子受體抑制劑(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inhibitors,EGFRIs)、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受體抑制劑(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inhibitors,VEGFRIs)、多靶點受體酪氨酸激酶抑制劑(multi-taget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MKIs)等最易產生不良反應,且臨床上各具特點。
1.1 表皮生長因子受體抑制劑(EGFRIs) 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在人類癌癥中經常過度表達或過度激活,可以導致正常角質形成細胞的異常增殖、遷移、分化,其在毛囊基底角質形成細胞和毛囊外根鞘中表達豐富,所以EGFRIs在發揮抗腫瘤效應的同時,常常會給患者帶來各種皮膚不良反應[2],這使得EGFR成為腫瘤治療的關鍵靶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抑制劑(EGFRIs)是目前臨床上應用最早、最廣泛的靶向抗腫瘤藥物之一,包括吉非替尼、厄洛替尼、西妥昔單抗、尼莫珠單抗、帕尼單抗等。常見皮膚不良反應改變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1.1 皮疹 EGFRIs所導致的最常見的皮膚不良反應為丘疹-膿皰樣皮疹(papulopustular rash),又被稱之為痤瘡樣皮疹。超過75%的患者在治療后1~2周出現皮疹,皮疹的發生呈劑量依賴性,這種皮疹主要發生在皮脂溢出部位,如頭面部、耳后、前胸部、后背部等部位。皮疹的形態單一,起初為無菌性毛囊性膿皰、丘疹,可伴有瘙癢或觸痛,繼發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并不少見,與痤瘡皮疹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并不伴有粉刺、結節或囊腫,約8周后可消退,消退可出現持續的炎癥后色素沉著[3]。
1.1.2 瘙癢(itching)以及干燥(dryness) 約三分之一患者在接受治療1~2個月會出現瘙癢及干燥的癥狀,提示與角質層功能異常、皮脂腺功能低下相關[4]。既往有濕疹的老年人及既往接受過細胞毒性藥物治療的患者更容易發生干燥且常伴有瘙癢、脫屑,尤其容易出現在既往發生皮疹的區域,并可在整個治療過程中持續存在,這種干燥瘙癢未加控制可進一步進展為慢性濕疹甚至繼發感染。
1.1.3 甲損害 甲損害的發生率約為12%~16%,其中甲溝炎(paronychia)是非常常見的一種甲損害類型,可伴有甲裂、甲營養不良和甲襞結痂,通常發生在初始治療的4~8周,拇指和拇趾最常受累,表現為痛性甲周肉芽形成或脆性化膿性肉芽腫樣改變[5],甲溝炎可能會繼發感染。
1.1.4 毛發改變(regulatory abnormalities of hair) 治療2~3個月左右,患者會出現發量、發質及毛發生長模式的改變,如頭發生長較慢,質地變細、較脆,面部多毛、眉形的改變、甚至出現非瘢痕性的脫發(這種脫發一般會伴有瘙癢),還有部分患者會出現睫毛的增長扭曲。
參照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對常見不良事件評價標準(CTCAE 5.0)可對皮疹進行分級。1~2級皮疹可不予處理或僅對癥處理,3級及以上應與腫瘤科醫生協商,調整EGFRI劑量甚至停藥,若合并感染應選擇合適抗生素治療,必要時需口服糖皮質激素,伴有干燥瘙癢的患者應外用保濕劑。甲溝炎的處理包括消毒浸泡、局部或系統應用抗生素及糖皮質激素,避免穿不合腳的鞋子等,若出現化膿性肉芽腫,可予手術處理。過長的睫毛可能會導致角膜損傷,及時修剪可以減少對角膜的損傷[6]。此外,表皮生長因子受體抑制劑的使用也可能出現口腔黏膜炎癥、毛細血管擴張、超敏反應、色素沉著等其他不良反應[7]。
1.2 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及其受體(VEGFR)抑制劑 血管生成在腫瘤的生長和擴散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需要信號分子(如VEGF)與正常內皮細胞表面的受體結合。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及其受體抑制劑可導致內皮細胞數量減少,微毛細血管形成減少,從而間接抑制腫瘤生長。按作用靶點不同,可以分為:靶向VEGF及VEGFR的單克隆抗體(貝伐珠單抗、雷莫蘆單抗)及靶向VEGFR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劑(瑞戈非尼、阿帕替尼)。其中按不良反應的種類及特點,靶向VEGFR的TKIs我們放在多靶點酪氨酸激酶抑制劑處進行討論。
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參與3種對組織損傷的生理反應,這3種生理反應是傷口愈合所必需的,包括:血管舒張、增加血管通透性和血管生成。故VEGF抑制劑可導致患者傷口延遲愈合,易于發生創面裂開、創面出血和創面感染等并發癥。目前建議血管生成抑制劑在擇期手術前至少4~6周停用,術后至少4周可恢復使用,并密切觀測傷口愈合情況。
1.3 多靶點受體酪氨酸激酶抑制劑(MKIs) 多靶點酪氨酸激酶是作用于多種信號通路的小分子,多靶點作用可以降低耐藥性的發生。涉及的靶點繁多,根據其產生皮膚不良反應的共性與差異,本節我們分兩部分討論。
1.3.1 靶向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及其受體的多靶點酪氨酸激酶抑制劑 靶向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及其受體的多靶點酪氨酸激酶抑制劑臨床上也極易引起皮膚不良反應。代表藥物包括索拉非尼和舒尼替尼及阿帕替尼等,它們是能夠影響血管生成和增殖的新型多靶點激酶抑制劑。
這組MKIs雖作用靶點不完全相同,但其引起的皮膚相關不良反應存在極大的共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不良反應是手足皮膚不良反應(hand-foot skin reaction,HFSR),可能會影響患者生活質量,并導致劑量調整甚至治療中斷。手足皮膚不良反應見于約9%~62%的患者,一般在治療后1~6周左右出現,表現為對稱性紅斑、水腫、角化過度、皮膚干燥、無水腫的痂樣大皰、脫屑和感覺異常。皮疹常出現在掌趾部,尤其是受壓、摩擦和外傷部位[8]。HFSR是較早出現也是最容易導致治療中斷的不良反應,因此預防顯得尤為重要,可建議患者穿戴手套、厚棉襪保護手腳,避免摩擦及創傷性活動。針對紅斑、角化過度及因皮疹產生的疼痛,可分別予局部外用糖皮質激素、尿素、水楊酸及系統應用非甾體類抗炎藥物和普瑞巴林等對癥治療[9]。
其他的皮膚不良反應包括紅斑丘疹樣、麻疹樣或苔蘚樣皮疹,頭皮感覺遲鈍、甲下裂出血、黏膜炎、顏面部腫脹、脫發、毛發改變、干燥癥、表皮囊腫,皮膚鱗狀細胞癌等不良反應在MKIs的使用中也時有發生[10-11]。
1.3.2 Bcr-abl及c-Kit抑制劑 以伊馬替尼、尼洛替尼為代表的多靶點酪氨酸激酶抑制劑,可抑制Bcr-abl、c-kit、PDGFR等受體活性。目前臨床上主要用于慢性粒細胞性白血病、胃腸道間質瘤及皮膚纖維肉瘤等疾病的治療。Bcr-abl抑制劑最常見皮膚不良反應包括:①皮疹多為麻疹樣發疹或苔蘚樣皮炎,呈劑量依賴性,少數患者皮疹可達3級及以上,可通過減藥、停藥或加用糖皮質激素及抗組胺藥緩解。研究表明,女性及使用伊馬替尼是出現麻疹樣發疹的獨立危險因素[12]。②水腫最常見,一般用藥6周左右出現,主要發生于顏面部,表現為晨起眶周水腫,嚴重者可出現胸腹腔積液及腦水腫,考慮與PDGFR抑制間質液穩態相關。不嚴重的水腫可通過限制鈉鹽的攝入得以緩解,若出現系統性水腫可予利尿劑系統治療。③色素沉著與色素減退c-Kit與黑素生成、黑素細胞穩態和UVB誘導的色素沉著有關,故使用伊馬替尼后可觀察到患者出現皮膚、毛發的色素改變,深膚色的人往往更容易出現色素改變,這種改變一般是可逆的[13]。伊馬替尼相關皮疹一般都為個案報道,既往報道過有使用伊馬替尼后出現剝脫性皮炎、重癥多形紅斑、急性泛發性發疹性膿皰病、玫瑰糠疹、苔蘚樣皮炎、銀屑病、光敏性皮炎等。
2 細胞內分子信號通路抑制劑及皮膚不良反應
RAS-RAF-MEK-ERK(MAPK)通路、PI3K-AKT-mTOR通路及Hedgehog通路是最常見的三條細胞內信號通路,當信號通路中任意一環節異常激活,均會導致許多惡性腫瘤的發生,目前這些通路的抑制劑也已成為分子靶向治療研究的熱門靶點。
2.1 RAS-RAF-MEK-ERK(MAPK)通路抑制劑
2.1.1 絲氨酸-蘇氨酸蛋白激酶抑制劑(RAF抑制劑) 絲氨酸-蘇氨酸蛋白激酶(Raf)基因家族由A-Raf、B-Raf和Raf-1(C-Raf)組成,在人類癌癥中,B-Raf突變最為普遍。1型RAF抑制劑結合并抑制激酶的活性構象,包括威羅非尼和達拉非尼,主要用于治療轉移性黑素瘤;而2型RAF抑制劑索拉非尼能結合激酶的非活性構象 ,也是一種多靶點酪氨酸激酶抑制劑(MKIs),主要應用于不可切除的肝細胞癌和轉移性腎細胞癌。1型RAF抑制劑的不良反應包括良性和惡性病變,如皮膚鱗狀細胞癌(SCC)、疣狀角化病、足底角化過度、Grover’s病(丘疹性棘層松解性皮病)、黑色素細胞痣及黑素瘤以及毛囊改變,脂膜炎,瘙癢及光敏性等。與單用BRAF抑制劑相比,RAF抑制劑和MEK抑制劑聯合使用可延遲耐藥性并顯著降低了皮膚毒性[14,15]。2型RAF抑制劑的皮膚不良反應可參照非選擇性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及其受體抑制劑,此處不做贅述。
2.1.2 MEK抑制劑 上游信號的突變可能會異常激活,導致RAS-RAF-MEK-ERK(MAPK)信號通路異常活化,匯聚于MEK蛋白,導致細胞的異常增殖。MEK抑制劑旨在在下游阻斷這種信號通路的異常活化。常見的MEK抑制劑包括一代的CI-1040及二代的西魯米替尼、曲米替尼,在結直腸癌,胰腺癌等治療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其皮膚不良反應與EGFR抑制劑很相似,而與同為MAPK通路抑制劑的RAF抑制劑截然不同[16]。一般對癥處理即可,可參照EGFR抑制劑所致皮疹的處理方法。
2.2 PI3K-AKT-mTOR通路抑制劑 PI3K-AKT-mTOR信號級聯是多種惡性腫瘤的上調通路,其中mTOR抑制劑已在臨床上得到廣泛應用。常見的mTOR抑制劑包括替西莫司和依佛羅莫斯,已被FDA批準用于晚期或轉移性腎細胞癌的治療。其所致的皮膚不良反應主要包括口腔黏膜炎及皮疹[16]。常見的處理措施包括局部或全身應用鎮痛藥、糖皮質激素可緩解癥狀,若仍無改善可考慮暫時停藥。25%~76%使用mTOR抑制劑的患者可能出現皮疹,呈麻疹樣、濕疹樣或痤瘡樣,最常累及軀干部,其次是四肢、面部及頭頸部,通常在治療后2周內出現,一般并不嚴重,無需調整用藥劑量,處理上可參照EGFR抑制劑所致皮疹的處理。
2.3 Hedgehog信號通路抑制劑 Hedgehog信號在許多惡性腫瘤中異常激活,而最常見的靶向該通路的方法是抑制SMO的活性,幾乎所有的基底細胞癌都顯示出hedgehog基因信號通路(HhSP)的基因改變,Vismodegib成為Hedgehog通路抑制劑中第一個被批準用于治療晚期基底細胞癌的靶向藥物。Hedgehog信號通路抑制劑最常見的不良反應是脫發。2級脫發見于10%~14%的患者,病理改變提示毛囊異常角質化,毛囊中沒有正常的毛干。這種脫發一般是可逆的,但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尤其是女性患者。外用米諾地爾可改善脫發癥狀,但尚無任何藥物可預防因Hedgehog信號通路抑制劑所致的脫發。
3 免疫檢測點抑制劑及皮膚不良反應
腫瘤的免疫治療被認為是近幾年來癌癥領域治療最成功的方法之一。癌細胞能夠通過激活特定的抑制信號通路(即免疫檢查點),逃避宿主免疫系統的識別和破壞。
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CPIs)是一類免疫抑制性分子,作用于細胞毒性T淋巴細胞抗原-4(CTLA-4)和程序性細胞死亡蛋白1(PD-1)或其配體(PD-L1)的抗體,旨在阻斷腫瘤細胞與免疫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從而促進對癌癥的免疫反應。目前已成功應用于黑素瘤、非小細胞肺癌、腎細胞癌、前列腺癌、膀胱癌等惡性腫瘤的一二線治療[17,18]。抗CTLA-4抗體作用于T細胞早期活化,而抗PD-1和抗PD-L1抗體主要作用于T細胞活化的末期。
ICPIs最常見免疫相關不良反應(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s)主要累及皮膚,發生率高達72%,嚴重者可導致患者停藥減藥。其中以斑丘疹、瘙癢及皮膚色素減退(白癜風)最為常見[19]。這種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相關皮疹表現為斑疹或斑丘疹,常發生于光暴露部位以及軀干、四肢等部位,可伴有瘙癢或無任何癥狀,皮疹和瘙癢常出現在治療的第一個周期(即用藥前3周),輕中度的皮疹可局部應用小劑量皮質類固醇激素以及保濕劑,持續瘙癢的患者可口服抗組胺藥。我們觀察到,色素減退的出現一般在治療的第8個周期,臨床可表現為橢圓形脫色斑點或斑塊,一般出現在發生皮疹之后,Wood燈檢查可明確色素減退。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中所有出現色素減退的均為黑素瘤患者,這可能是由于黑素細胞與黑素瘤存在共同的抗原(例如MART-1,gp100,酪氨酸酶)所導致的皮膚不良反應的出現,尤其是黑素瘤患者出現色素減退可能是預后良好的表現[20]。
有文獻報道使用抗PD-1抗體治療后出現Stevens-Johnson綜合征(SJS)、中毒性壞死松解癥(TEN)、藥物超敏反應綜合征(DRESS)、大皰性表皮松解癥等嚴重不良反應,雖然發生率低,但仍應引起足夠重視。其他不良反應包括自身免疫性皮膚病(如銀屑病、大皰性天皰瘡、皮肌炎、斑禿、硬皮病),苔蘚樣皮炎、急性發熱性嗜中性皮病(Sweet綜合征)、結節病、指甲和口腔黏膜改變、神經性皮炎等也有報道[21]。
4 總結
靶向治療的患者出現皮膚不良反應極其常見,這些不良反應極大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質量及用藥的依從性。正確認識各種類型分子靶向抗腫瘤藥物所產生的皮膚不良反應的共性與各性,對患者進行預見性的指導與建議,可以提高腫瘤患者的依從性,進一步提高抗腫瘤治療療效,減少繼發感染發生的風險,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減少患者至醫院就診的頻率并減輕腫瘤患者的經濟負擔,最終受益于廣大腫瘤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