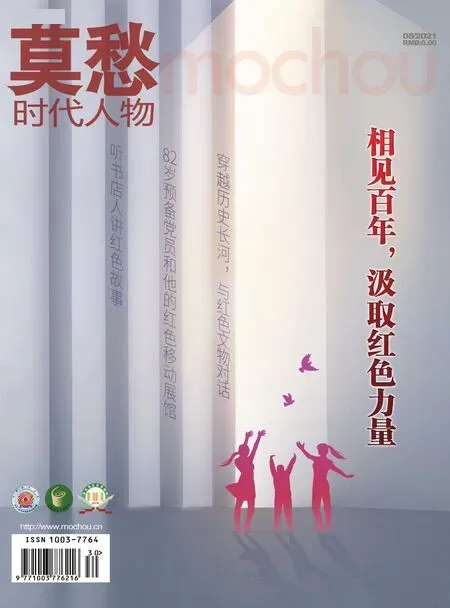徐光華:左手管理學,右手書法藝術
文/王若宇

徐光華
“從經濟走向藝術,是理性的思考。光華的執著不是單一的,他將練字和思考始終聯系在一起,以后會帶來更大的正能量……光華以自己的生命為基準,從邏輯思維到意向思維的過程里,為生命帶來別樣的色彩。”著名書法家言恭達在南京崇正書院舉辦的徐光華書法展上如此說道。
從經濟走向藝術,只是一個籠統的說法。對于一個完整的生命而言,總有交匯點和平行線。南京理工大學教授徐光華說,其實管理學與書法藝術一直并行在他的生命里。
會計專業的書法愛好者
熱衷書法、溫文爾雅的徐光華,讓人不自覺地以為他是藝術系書法專業的教授。但事實上,他卻是在云波詭譎的商界輔導資本上市,給企業提供決策建議的人物。
這樣一位在商戰里百煉出來的教授,談起書法藝術滔滔不絕。在徐光華的記憶里,與書法結緣始于一場知識焦慮。“中學時,我在武進縣前黃中學(現為江蘇省前黃高級中學)就讀。校門的匾額由林散之先生題詞,同學們常常聚集在一起,笑稱這幾個字寫得糟糕。”徐光華在查閱資料時,偶然瞥見了林散之的故事,得知林散之乃書法大家,心中大吃一驚,“為什么‘當代草圣’的字寫成了這樣呢?”后來,他每天上學時都要借著晨光好好審視一番校名,但直到高考,還是沒有琢磨出名堂。“我當時就覺得自己的書法知識不足,立志要在上大學后好好請教、學習傳統文化知識。”
1981年,徐光華考入剛剛成立的南京財經大學,讀會計專業。“同學來自全國各地,還有1977年、1978年考試未果不斷復讀的老同學。”不過正因如此,徐光華的書法才能得到這些老同學的指點。
正是因為書法,讓徐光華遇到了自己的知音與愛人。在鎮江教書時,他遇到一位氣質絕佳的女孩,略一打聽,這位女孩名叫李珣,生于書法世家。為此,徐光華更加努力地研習書法,功夫不負有心人,李珣也被徐光華的才氣吸引,兩人最終走到了一起。
書法和管理學都要創新
有同學推薦徐光華去臨摹《蘭亭集序》。《蘭亭集序》是1600多年前會稽(現為浙江省紹興市)內史王羲之與友人謝安、孫綽等人飲酒時寫下的千古名篇。徐光華認真閱讀了幾遍,心中豁然開朗。“藝術的價值在于創新。”徐光華解釋道,他發現《蘭亭集序》中的二十一個“之”字,字字不同,呈現出一種別致的審美。“獨持偏見,一意孤行。”徐光華借用了徐悲鴻的名言。
頓悟后,徐光華的書法有了突破,筆力遒勁,靈動自如。而在學術上,也因為自我的內省格外精進。“管理學和書法有共通之處,都強調創新。”他開始專注于創新思維的開掘,也讓他在學術上造詣漸深。
“我的管理學理論中,納入了環境、社會責任等多維度的元素。”徐光華介紹道,作為企業,在經營過程中,需要面臨各種博弈,但是環境、社會責任并不能被忽略,“試想一下,國家為企業提供了人才培養、公共社會服務支持。簡單地說,國家培養一個人才花了多少年時間,企業就能夠直接聘用,而且為了維護企業經營環境的平穩,保護社會的安定,國家為國防事業花費了很大代價。如今,很多企業以犧牲社會利益為代價,提高自己的經濟利益,實在讓人不齒。”
保持管理學創新的速度
徐光華常常與企業高管分享自己的新理論。“這些理論都是在卡普蘭的理論上結合中國國情創新出來的。”徐光華說,中國社會發展速度越來越快,企業作為社會的一分子,面臨著各種前所未有的問題。這種情況下,就要求科研工作者能夠在中國速度下保持管理學創新的速度。徐光華說,創新的速度非常快,但幸好每個研究工作者都能夠站在前輩巨人的肩膀上。
徐光華敢于實踐,這是很多管理學研究者不敢去做的事情。作為多家江蘇龍頭企業的獨立董事,徐光華對江蘇企業有著別樣的情懷,這種情懷讓他敢于挑戰。前不久,他成為江蘇華西村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屆獨立董事,而此時的華西村股份面臨著輿論的巨大壓力。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幫助這家具有特殊意義的企業渡過難關。這份初心源自一種責任感。
對于徐光華而言,創新的速度同樣需要用創新的方式傳播出去,為此,徐光華負責籌建了南京理工大學企業家學院,主要給民營企業家提供學習的環境。“我們前不久去了久吾高科公司參觀學習,所有同學和老師一起進行了頭腦風暴,討論出了很好的管理思路。”李步有是企業家學院的學員,他對徐光華的理念深感贊同,也在自己的企業大力進行管理模式的改革。除此之外,徐光華還參與到江蘇省會計領軍人才培養項目中,他希望通過自己的教授,讓不同行業的人才在自己的行業發揮出積極作用。
“如山,如水,如云。自在,自由,自然。”臺灣著名學者江岷欽曾如是評點南京理工大學企業家學院的精神,指其氣勢像鐘山一樣磅礴自在,思路像江水一樣柔軟自由,舉止像云朵一樣優雅自然。而這份精氣神,也多浸潤了徐光華的氣質。

徐光華書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