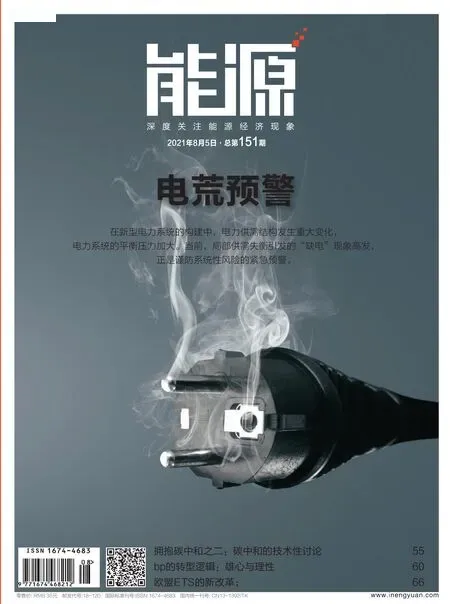煤炭行業低碳轉型發展的工程路徑與技術需求
文 | 彭蘇萍
作者系中國工程院院士
對于以煤為主的中國來說,煤炭的低碳轉型是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關鍵。
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是一場硬仗,也是對我們黨治國理政能力的一場大考;中國言出必行,將堅定不移加以落實。
我國擁有全球最大的能源系統,也是最大的煤炭生產和消費國。“相對富煤、油氣不足”是我國資源稟賦,由此產生了煤、油、氣和非化石能源“一大三小”的能源生產結構。大規模的煤炭開發利用是我國能源行業目前最突出的特點,也是我國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2020年煤炭相關產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76億噸,占我國總排放量的77%左右。
由于之前煤炭在中國工業和國民經濟發展中起到保障性作用,是中國能源安全的基礎,所以我們曾經投入了上百億用于煤炭的基礎設施建設。這些基礎設施不僅規模大、投資大,而且發展周期長,轉型也是相當困難。因此能源革命也意味著煤炭行業要革自己的命。

碳約束將深刻影響和改變現有能源開發利用方式。世界各國能源綠色低碳轉型路徑與方式各有不同,由資源稟賦與技術優勢差異所決定。推動經濟增長模式的綠色低碳轉型不會一蹴而就,我國國情能情的特殊性決定了無可借鑒先例可循。
作為一個以煤為基礎的國家,中國想要實現能源轉型進而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就必須探索自己的路徑。在這種前提下,我們必須堅信煤炭是可以做到清潔高效和低碳利用的,而且可以變成更經濟、更安全的能源。
煤炭的高質量發展是我國能源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正在建設并發展以新能源為主的新型電力系統,但是新能源在清潔性突出的同時,也存在大量的局限性。目前的中國應該是化石能源與可再生能源最好的融合時期,而不是強調由誰來代替誰。
所以不實現煤炭的綠色低碳發展,很難完成我國的碳中和目標。我們必須立足國情,走中國特色的能源轉型道路。
助力碳達峰的煤炭低碳發展措施主要包含了6項:大力發展煤炭開采碳排放控制技術、降低煤炭開發利用的能源消耗強度、提升用煤質量減少煤炭利用碳排放、推動煤炭向原料、燃料并重轉變、推動煤炭與其他能源實現融合發展、研發實用的碳捕集、利用與封存技術。
為了支撐碳中和目標的實現,我們需要發展煤炭綠色智能生產和二氧化碳近零排放的煤氣化燃料電池發電技術。
煤炭行業的低碳轉型面臨著諸多的現實挑戰,其中包括:當前煤炭相關產業碳減排壓力巨大;以煤為基礎的發電和轉化效率還不高,急需開發高效技術將用煤總量降下來;大規模可再生能源近期還很難替代煤炭,油氣供應安全形勢嚴峻,能源轉型還需時間;煤炭開發利用過程中二氧化碳資源化回收及高值化利用技術不足等。
因此,我國煤炭行業要從以下四個方面來進行努力:第一,煤炭的智能綠色開發;第二,煤炭的清潔高效發電;第三,煤炭的清潔高效轉化;第四,煤基能源或者碳基能源的CCS、CCUS技術。
具體來說,不同的研究重點能夠解決不同的問題實現不同的目標。
煤炭的智能綠色開發要在智能開采和綠色開采方面實現關鍵技術突破,進而解決井下環境復雜,智能感知、協同控制可靠性低;能耗高(噸煤能耗7公斤標煤);煤礦主產區嚴重缺水,生態環境脆弱;煤炭開采引起地表沉陷、地面塌陷和裂縫,導致礦區地下水位大范圍和大幅度疏降,生態退化等問題。可以實現降低噸煤能耗、減少煤礦數量和人員成本等問題,還可以使礦區塌陷得到生態修復,加強固碳能力。

我國的煤炭污染物排放已經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在煤電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方面還有差距。《電力發展“十三五”規劃》要求2020年煤電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控制在865g/kWh左右;美國將煤電二氧化碳排放控制在636g/kWh。燃煤發電技術如果不創新,將會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
現有煤電技術(包括超超臨界煤電技術)面臨著提高效率難、近零排放難、減排CO2難的瓶頸,只有整體煤氣化燃料電池發電技術能夠突破這三大瓶頸。
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IGCC)是目前已被驗證的能夠大型化的煤氣化發電技術,可實現高供電效率、污染物與CO2近零排放、靈活調峰。IGFC是將IGCC與高溫燃料電池相結合的發電系統,可在IGCC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煤氣化發電效率,降低CO2捕集成本,同時實現CO2及污染物近零排放,是煤炭發電的根本性變革技術。
IGFC實現了煤基發電由物理發電向化學發電的技術跨越,突破卡諾循環效率限制,發電效率從目前的40~45%提高到50~75%;
該發電系統固體氧化物燃料電池(SOFC)所需燃料來源廣泛(粗氫、現有各種碳氫燃料包括人造煤氣、天然氣、沼氣等),無需建立新的能源供給系統。
從結果上來說,IGFC有利于CO2的富集和污染物的控制,大大降低了C O2的捕集成本,預測C O2排放可控制在500g/kWh以下。相當于標煤180g/kWh,比天然氣發電還低。
盡管國內已掌握主要關鍵技術,但與國外差距仍然很大,尚無長期運行的示范系統,中國SOFC應用研究仍然需要從突破關鍵技術及建設示范工程開始。
煤炭的清潔高效的轉化是為了保障應急狀態下國家油品安全,用直接或間接的方法實現煤制油品、化學品、材料的供給多元化。
這包括煤炭的直接轉化和間接轉化過程中的技術革新,進而實現碳減排、能效提高、高附加值先進材料制造等一系列目標。
碳的捕集利用和封存——尤其是低能耗的規模化技術——是為雙碳目標實現提供的兜底手段。
在“雙碳”目標下,很多人均碳排放比較高的地方政府會出于控制碳排放的目的限制煤炭項目。但這些項目可能無論從經濟發展還是實際需要來說,都有上馬的需要。這個時候就需要對二氧化碳進行捕集和封存。但是目前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的成本較高,因此技術創新的重點就在于降低能耗進而降低成本。
另外,在油氣資源開發等領域,二氧化碳還有一定的使用價值。因此積極開發二氧化碳的利用也十分重要。二氧化碳存在難以活化和規模利用經濟性差的問題。因此我們和其他行業積極合作,構建綠色的碳循環體系,實現煤炭利用的碳中性。
總的來說,煤炭高質量發展是我國能源安全新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科技進步,煤炭可以成為清潔高效和低碳利用且最經濟安全的能源。煤炭綠色低碳化發展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關鍵,不實現煤炭的綠色低碳發展很難完成我國碳中和目標。
其中,整體煤氣化固體氧化物燃料電池發電系統(IGFC)是煤電發展的顛覆性技術。其完善和發展將物理發電向化學發電邁進,能源轉換效率可提高一倍以上,實現發電流程中二氧化碳閉路循環不排放,從而打破目前碳排放的緊箍咒。這對我國以煤為基礎的能源大國具有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