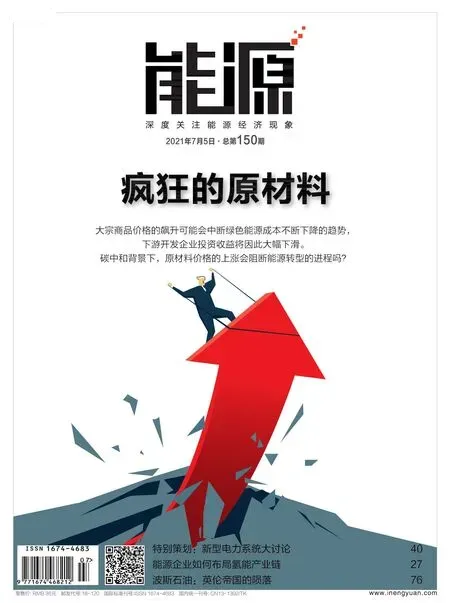波斯石油:英倫帝國的隕落
文 | 陳湘球
作者任職于中油國際管道公司
1950年11月28日,阿美石油公司和沙特家族之間達成的五五分成的協議,這個消息對于英伊石油公司來說是災難性的。在素以強硬作風著稱的英伊石油公司董事長威廉·弗雷澤爵士看來,這是美國國務卿中東事務助理麥吉在他面前引爆的一枚重磅炸彈,這枚炸彈不僅摧毀了自己的強硬與傲慢,更是燃爆了摩薩臺對英國人的怒火,伊朗石油工業國有化已經走上了一條不歸之路。
迅猛的國有化之路
摩薩臺是《時代》雜志1952年的年度人物,被編輯稱為“幾個世紀以來,這個古老民族創造出來的著名人物,是伊朗的喬治·華盛頓”。他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節和強烈的排外情緒,使他成為伊朗民族主義運動無可爭辯的領袖,早在1944年就開始著手將伊朗石油國有化。
當蘇聯向伊朗施壓,要求取得在北部的石油開采權時,作為國會議員的摩薩臺就推動通過了一項法案——在戰爭期間禁止一切石油談判——阻止了蘇聯人借戰爭時期在伊朗駐軍的契機涉足伊朗石油工業。他強硬的作風漸漸使他成為國會中“麥伊斯地區無可爭議的最具聲望和人氣的代表”。1949年,他建立了后來被稱為“國民陣線”的政黨。實現“石油國有化”和“立法以保證公正和自由的選舉”是這個政黨的兩個主要政治目標。
石油國有化的口號在政治精英中很受歡迎,他的同僚阿亞圖拉·卡沙尼,一位什葉派宗教的領袖人物,通過宗教的力量,讓更多的人加入到伊朗石油國有化運動中來。卡沙尼動員人們為這一事業采取行動,他發表了一份聲明,號召人們于1950年12月22日到德黑蘭的大清真寺集會。在這個由穆斯林圣公會組織的盛大集會中,卡沙尼宣布要從伊朗的敵人手中奪回石油,并將石油工業國有化。
1950年12月29日,卡沙尼在巴哈爾斯坦廣場召集人們再次集會,他選擇這個廣場(在議會附近)是為了支持國民陣線的代表,并警告那些反對石油工業國有化的代表。卡沙尼的努力取得了成效。摩薩臺在一封給卡沙尼的電報中寫道:你的支持和勇敢的嘗試是伊朗在這場歷史性運動中取得成功的根本。
1951年3月初,在巴基斯坦出差的麥吉突然接到華盛頓的指示,伊朗總理阿里·拉茲馬拉遇刺身亡,華盛頓要求他立即前往德黑蘭,評估局勢,并強調要特別注意國民陣線正在引導伊朗政府將英伊石油公司國有化。麥吉在德黑蘭的行動立即成為了全球關注的焦點,就在他抵達德黑蘭的當天,《倫敦每日郵報》刊登了一篇標題醒目的文章:《派往波斯的石油特使》,這篇文章說,麥吉將就英國的讓步重啟談判,敦促伊朗接受英波石油公司提出的對半分成的計劃。顯然摩薩臺的行動已經突破了弗雷澤的底線,在拉茲馬拉面前曾經咄咄逼人的弗雷澤已經不再計較分成比例了。現在他面臨的選擇是英伊石油公司在伊朗的生死存亡,而他的去留已經被死死捏在曾經被自己冷漠嘲諷的麥吉手中。他還不清楚,伊朗石油會不會通過美國繼續流入西方市場。
麥吉抵達德黑蘭的第二天,他見到了國王穆罕默德·巴列維,他對國王的印象還停留在華盛頓時的那次會面:驕傲、挺拔,一位充滿自信的年輕人。但是,當他走進昏暗的會客室,出現在他眼前的卻是一個愁苦沮喪、幾近崩潰的人,“國王對暗殺充滿了深深的恐懼”。當麥吉詢問國王是否相信美國的支持可以幫助伊朗避免石油國有化時,國王回答說不能那么做,他甚至懇求麥吉不要讓美國那么做。
拉茲馬拉的遇刺象征著伊朗人反對英伊石油公司和支持國有化的情緒空前高漲,英伊石油公司“成了大英帝國剝削帝國主義的化身,是社會和經濟不公的根源”,在石油問題上,來自不同背景的伊朗人聯合起來抗議舊秩序。
就在拉茲馬拉遇刺的第二天,1951年3月8日,伊朗國會石油委員會響應公眾的要求,一致通過了石油國有化的決議,這項決議要求國會給該委員會兩個月的時間來研究如何最好地將國有化付諸實施。3月9日,為了響應阿亞圖拉·卡沙尼的號召,15000人再次在德黑蘭集會示威,敦促國會支持委員會的決議。
伊朗國有化的進程是如此的迅速,讓美國人始料不及。1951年4月28日,伊朗議會以79比12的投票結果任命摩薩臺為新總理,5月1日,摩薩臺政府宣布將英伊石油公司收歸國有,取消1993年到期的石油特許經營權,并沒收其資產。
摩薩臺一方面安排人設法打進駐在德黑蘭的英伊石油公司總部,竊取到一份由英國董事精心保管的名單。這份名單上開列著英伊石油公司向一些伊朗議員、內閣大臣和政界人物饋贈“禮物”的戶頭,其中甚至還包括巴列維國王身邊的一些人物,通過反腐敗清理政府的門戶,他開始直接動搖巴列維國王的根基;另一方面他暫停了英伊石油公司每天的日報,讓英國政府無從知曉國有化的進展。
每天下午全球的石油商人都在豎起耳朵收聽BBC廣播,捕捉最新的信息,如果廣播中沒有提到阿巴丹或者德黑蘭,大家都似乎覺得錯過了什么。BBC開始加大對摩薩臺的負面宣傳,但是此時伊朗人民不像對待禮薩沙阿·巴列維那樣對待摩薩臺,此時的摩薩臺是拯救國家的民主英雄,當BBC開始對摩薩臺進行詆毀的時候,伊朗當地所有的廣播員突然消失了,沒有伊朗人準備說任何反對摩薩臺的話,沒有伊朗人會對摩薩臺不尊重。BBC別無選擇,只能引進說波斯語的英國人,所有的波斯語廣播都帶有很重的英國口音,英國著名的波斯文化和伊斯蘭研究學者埃爾韋爾·薩頓在后來的著作中寫道,“這種廣播宣傳是令人討厭的”。
麥吉回到美國,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聽眾說,他“有機會與德黑蘭的國王進行長時間的討論……, 沒有跡象表明克里姆林宮策劃了目前的伊朗危機”。如果沒有跡象表明克里姆林宮策劃了這場危機,那么誰會策劃這場危機呢?在已經公布的工黨文件中——英國首相理查德·艾德禮在自己的筆記本里講述了英美關系在伊朗地區失衡的事實,他說,“事實是,美國想以犧牲我們的利益為代價來換取她自己的利益。”
倒向美國
這些筆記本記錄了內閣部長們對一位幾乎不為人知的美國人的討論,這位美國人是這場運動的先鋒,他就是麥吉。麥吉溫文爾雅,面無表情,并不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可怕人物。然而,他在英國中東命運轉折點上發揮的關鍵作用是破壞英國在該地區的信譽,他也是引發蘇伊士運河危機的關鍵人物。
美國國會在5月4日舉行專門會議,聽取麥吉對伊朗局勢的匯報,麥吉說,“自拉茲馬拉死后,國家治理成為了德黑蘭的主要問題。現在的伊朗國王不像他父親那樣強勢。你們很多人都在這里(華盛頓)見過他。他在瑞士接受教育,三十出頭,擁有忠誠的人民,但他不是一個強者,他不具備他父親的那種控制力。更為不幸的是,他的地位使他很難支持一個強有力的首相,他總是擔心自己會像父親的前任那樣,被某個對軍隊或人民忠誠的強人推翻… …”
麥吉所說的“強有力的首相”就是摩薩臺,摩薩臺似乎生來就是伊朗國王的宿敵,他的父親是愷加王朝的財政大臣,母親是愷加王朝的一位公主。在波斯王宮里長大的他,從來就沒有畏懼過王權,“摩薩臺”是當時的伊朗國王給他的外號,意思是“經過考驗,英勇非凡”。他曾公開反對強勢的禮薩·汗攫取王位,當下他顯然沒有把軟弱的穆罕默德·巴列維放在眼里。
所以,麥吉這番言論意味著伊朗已經進入摩薩臺統治時代。麥吉還說,“國有化是摩薩臺民族主義運動的結果,他是國民陣線黨領袖,從1944年以來,就一直是議會的主宰者,現在更是伊朗總理… …,國有化已是既成事實,如果阿巴丹煉廠和油田出現罷工,3500名英國人的安全將受到威脅,伊朗政府無法為他們提供警察保護,我認為英國人肯定會撤離,英國的船只將進入阿巴丹港,為人員撤離做準備… …;(英國人撤離后)如果他們(伊朗)試圖完全通過雇傭外國技術人員來運營管理,可以證明不會成功, 3500名英國人中大多數人都想回家,伊朗不能把所有的專業技術人員組合在一起,除非有一家綜合性的石油公司愿意接手英伊石油公司的運行管理… …”
沒有人知道麥吉是不是在努力趕上摩薩臺的節奏,為美國政府提供伊朗石油國有化危機的解決方案。在美國國會舉行聽證會的十天后,1951年5月14日,他召集了所有在中東有業務往來的美國石油公司討論“英伊石油公司的問題”,新澤西、海灣、阿美、真空、加德士和太平洋西部石油公司的重量級人物悉數到場。麥吉一開始就告訴他們,“美國政府的觀點是,一種最低限度的國有化必須被作為一個既成事實接受。到目前為止,英國還沒有提出我們認為伊朗人有任何機會接受的提議”。在討論到英伊石油公司后續管理的時候,他接著說:“如果美國現在提供運營管理,我們與英國的關系將受到嚴重影響,英國將失去從這場爭議中收拾爛攤子的機會。但是,如果情況惡化(指蘇聯介入),它(美國公司提供運營管理)將變成一個選擇,要么是共產主義技術人員,要么是美國技術人員,毫無疑問,(到那個時候)英國政府會支持并敦促美國公司采取行動”。很明顯,麥吉開始策劃在國會聽證會上提到的“綜合性的石油公司接手英伊石油公司的運行管理”這一方案。麥吉的意圖非常清楚,他想把英伊石油公司偽裝成一個財團來“稀釋”其股權,而控制這個財團的若干公司中,起主導作用的應是美國公司。
5月26日,持有英伊石油公司最大股份的英國政府,向荷蘭海牙國際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法院支持伊朗遵守1933年的協議,并就國有化過程中對公司利潤造成的不利影響提出損害賠償。伊朗立即做出反應,盡管摩薩臺年事已高,健康狀況不斷惡化,但他仍帶領伊朗法律團隊捍衛伊朗議會的決定,同時轉向美國尋求支持和幫助。

在1951年6月11日,摩薩臺給杜魯門總統寫信,描述了伊朗必須將石油工業國有化的原因。他說:“總統先生,多年來,伊朗政府一直對前英伊石油公司的活動感到不滿,他們向這片土地的唯一擁有者伊朗人民分享的利益是如此之少,以致激起了所有公正人士的憤慨… …,在戰爭中,伊朗為爭取權利、正義和世界自由的最終勝利與盟國進行了充分和真誠的合作,她遭受了難以言表的苦難,做出了許多犧牲……,這個國家的勞動階級,曾承受了全體戰爭盟友難以面臨的價格上漲和失業飆升……,如果我們像其他遭受戰爭之苦的國家一樣得到外界的幫助,我們的經濟可能很快就會復蘇,即便是沒有這種幫助,如果我們沒有受到(英伊石油)公司的貪婪和阻礙,我們的努力也能取得成功。可是,公司總是千方百計,限制我們的收入,給我們施加巨大的財政壓力,擾亂我們的組織,迫使我們向公司求助,結果就是,不管公司想強加給我們什么,我們都得屈服… …”
大英帝國最后的傲慢
摩薩臺情深意切的求助立即得到了美國政府的響應,杜魯門明確反對英國政府對伊朗采取軍事行動,并立即派出商務部長艾弗里爾·哈里曼前往德黑蘭,以防止沖突發生。因為此時英國已經將它的傘兵部隊派往塞浦路斯,駐扎在毗鄰伊朗的伊拉克邊境地區,甚至把“毛里求斯”號巡洋艦開到了阿巴丹港的外錨地。
7月5日,英國財政大臣收到海牙國際法院的判決,結果以多數票宣布英國政府的請求已經超出了國際法院受理管轄的范圍,駁回了英國政府要求伊朗遵守1933年特許權協議的訴求。英國駐德黑蘭大使隨即宣布,英國政府將對該判決提出上訴。
海牙國際法院的判決對英國政府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他們開始接受美國商務部長哈里曼從中斡旋的方案。7月23日,摩薩臺宣布,他同意與英國政府啟動談判,條件是英國政府必須接受伊朗石油國有化的事實,他同意英國官員作為英伊石油公司的代表參加談判會議。但是,隨著哈里曼的到來,德黑蘭民間出現了大規模的游行示威,數百人受傷或被殺。這是摩薩臺沒有想到的,他在議會上說,“我們議會里的英國代理人,我們政府里的英國代理人,和摻雜在我們社會上的英國代理人,他們無處不在… …,這是英國特工的所作所為”。他開始調查游行示威事件的來龍去脈,內務部長法茲魯拉·扎貝迪是這次行動的組織者,這是扎貝迪發起的第一次針對摩薩臺的政變,背后是英國人在故伎重演,想把他們不想要的總理趕下臺。
扎貝迪的行動并沒有終止哈里曼的斡旋,摩薩臺迅速為他清理了障礙,但是在他拜會卡沙尼之后,他深切地感覺到最大的障礙其實是卡沙尼,因為后者對他說,“如果摩薩臺屈服,他的血也會像拉茲馬拉一樣流淌”,毫無疑問,卡沙尼是一個不可調和的危險的反對者,這位曾經把摩薩臺推上總理席位的宗教領袖,在取得勝利后,想任命一些部長,卻沒有得到摩薩臺的認可,于是曾經的戰友開始分道揚鑣,這位老謀深算的牧師成了摩薩臺的敵人,摩薩臺與英國政府的任何妥協,都不符合他對石油國有化的構想。
與卡沙尼的會晤,讓哈里曼看到了一絲希望,與卡沙尼相比,摩薩臺對待英國政府的態度,顯然要柔和的多。所以,他建議英國政府派出一個特別的談判代表繼續與摩薩臺談判,一位有著社會主義背景的百萬富翁理查德·斯托克斯無疑是最佳人選。根據丹尼爾·耶金在 《石油風云》中的介紹,陪同斯托克斯一起去德黑蘭的還有唐納德·弗格森,他是有影響的燃料電力部的常務副部長,一貫批評英伊石油公司及其董事長威廉·弗雷澤;認為弗雷澤是一個狹隘、專制和對較大的政治潮流及考慮不敏感的人士,對伊朗走到石油國有化這一步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斯托克斯與摩薩臺的談判取得了很大的進展,雙方約定按照英國實際需要向其銷售石油、充分考慮伊朗政府和英伊石油公司在國有化之前的合法權益、英國石油專家和工程師繼續為國有化后的石油公司工作;斯托克斯還接受了由國家石油公司的董事會全權管理國有化石油公司的管理構架,摩薩臺也同意斯托克斯提出的從中立國聘請一些一流的專家作為董事會新成員的提議。但是,斯托克斯仍然沒有擺脫“英國紳士”固有的優越感和冷酷的殖民心理,在討論到石油公司總經理人選的時候,斯托克斯聲稱,英國專家不會也不愿意在非英國血統的人領導下工作,他們寧愿讓一個英國人坐在這個職位上。即便是在離開德黑蘭后,也依然沒有忘記致信摩薩臺,“如果伊朗政府不接受這一條件,將立即停止一切討論和談判” 。
也許英國人壓根就沒有想到過要離開阿巴丹,首相艾德禮曾對他的內閣成員講,“如果英國職工在阿巴丹被趕出,對我們這個國家是一種恥辱”。但是,談判破裂,艾德禮最不愿意看到的結果出現了,英國工人和技術專家被驅逐出石油地區。摩薩臺給駐扎在伊朗的英國人發出了最后通牒,從1951年9 月25日算起,留在阿巴丹的英國雇員們必須在一周內撤離。
10月4日,停泊在阿巴丹港外錨地的“毛里求斯”號巡洋艦不僅未采取任何軍事行動,反而成為了撤離留在阿巴丹的英國石油人的交通工具,這是英倫帝國的恥辱。西方人在中東石油開發進程中獲得的第一份開采權就這樣被“毛里求斯”號巡洋艦帶回了英國,“英國紳士”固有的優越感和冷酷的殖民心理已經成為了留在阿巴丹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