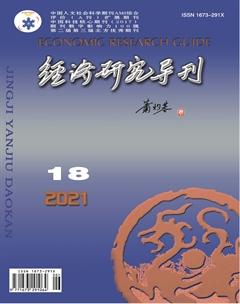財產的兩權演化
摘 要:梳理財產的漫長演變過程,對洞悉當今世界的一些現象有著積極意義。原始財產階段,交換權和分配權是統一的。物質財產階段,交換權獲得獨立。貨幣財產階段,交換權演化為分配權。在這種進步之中也蘊含著消極后果,易引起社會的金錢化、泡沫化、空心化。因此,應創設振興實體經濟的社會治理機制,即用政治手段迅速解決表層的貨幣分配權虛擬化問題,用法律手段跟進解決中層的貨幣分配權的泛濫化問題,用經濟手段最終解決深層的貨幣分配權的極端化問題。
關鍵詞:財產哲學;演化;實體經濟;社會治理
中圖分類號:F014? ?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1673-291X(2021)18-0142-07
財產問題是人類一個永恒的話題。賈誼說:“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1]這是我國傳統典籍中少有的一次對財產的直接論述,道出了其對財產的憂慮。當前社會問題背后依然是難以擺脫的財產窠臼。我們有必要繼續探討財產的本質及其演化,并因之提出適應現在問題的對策。
從財產哲學[2]出發考量財產的演化,其基本觀點如下:最初的財產主要是人本身,分工協作、分享所獲是同一件事情。分工是內部交換,分享是內部分配,交換權和分配權是統一的,是一回事。財富產生后,物質作為財產成為可能。物質財產的直接作用是消費,但同時也是交換自己所沒有的使用價值的前提。所以,財富的基本作用是作為使用價值存在的交換權。貨幣實現對兩個自然限制第二次突破后,成為了財富的直接形式。貨幣在作為貨幣時不再具有使用價值,它代表的是可以分得多少勞動價值的分配權。財富由交換權轉化為分配權。這一方面是人類的進步,另一方面又會有很多不良后果。對財富的貪婪追求使人們放棄了去創造財富,而把更多的時間花費在了對作為財富的分配權的貨幣的追求上,導致了社會的金錢化、泡沫化、空心化,我們必須為此創設振興實體經濟的社會治理機制以應對。
一、交換權和分配權的原始統一
約400萬年前,人類的祖先—原人—在非洲東部和南部的熱帶草原上出現,但在約5000年前人類才學會了書寫。我們所說的第一個時期就是起自400萬年前,終于1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這個時期,人類的直接要務是與自然的對抗,以求得生存,這就是以人的互相依賴為基礎的社會存在狀態。這是一個人的互相依賴時期,人和物不分是當時的現實,由此,交換權就是分配權,二者是原始統一的,這才是人類絕大部分時期的事實。
(一)人的互相依賴
斯密的“狩獵時代”、摩爾根的“蒙昧階段”以及斯塔夫里阿諾斯的“食物采集者時期”都指舊石器時代。據可靠估計,最初的原人數量為12.5千人,舊石器時代末期則有約532萬人[3]。其部落規模一般為20—50人,組成部落的是更小的單位——家庭。家庭成員中,男負責狩獵保衛,女職司采摘生育,男女關系平等。部落建立在親密的血緣關系之上,部落成員在抵抗外敵、獵采食物、躲避風雨中共同協作。部落是部落成員通過生產關系聯系在一起的一個群體的“人”,這個“人”從我們今天研究的角度看是一個實際的“人”,其由個體成員、多個家庭、各種獵采工具和領地等組成一個整體。脫離了這個整體的“人”的“個人”的生活無非是一種“自殺式”的叢林冒險。漢娜·阿倫特指出:外來者“如同村莊中來犯的野獸,可以隨時被射殺。”[4]當然,那個時候是談不到“個人”的,“個人”只是我們現代人的觀念。這些“個人”之間是緊密不可分的,這就是最初的人的互相依賴的社會存在狀態。按照我們現代人的觀念,如果說當時存在“我的”“你的”“他的”,那也只能是作為整體的“人”的“我的”“你的”“他的”,而不是“個人”的“我的”“你的”“他的”。“個人”只是作為“人”的財產存在的。因此,最初的財產是人本身。爭奪財產首先就是對人口的爭奪,所以,奴隸社會的出現并不值得大驚小怪。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看出,人是最大的財產。
(二)人和物不分的現實
原始人處于自然的完全包圍之中,連自我意識都不可能存在,或者說沒有存在的基礎。原始人是自然界的天然組成部分,有物而無自我,不同部落之間的對抗本質上只是自然界中“物與物”的對抗,原始人個體是部落這個群體物的組成部分。其存在狀態與周圍萬物一樣,無論生老病死還是戮力求生均屬自然而然,宛如周邊的各種生物。老弱病殘都會被狠心地拋棄掉而無愧疚。部落就是在自然界神力下形成的“由死者、生者和來者所組成的無始無終的隊伍。”[3]不管今天、明天還是后天都是這樣,個人存在的目的是群體的存在,即延續這支隊伍的生命。為了對抗神力無窮而又難以預測的自然界,并不太大的部落竟然會令人驚訝地產生巫師。北極探險家努特·拉斯穆森曾聽一位愛斯基摩人說:“我們相信我們的巫醫、我們的魔法師。我們之所以相信他們是因為我們希望自己能夠活得長久些,是因為我們不愿受到饑餓的威脅,還因為我們希望生活安全、食物有保障。如果我們不相信魔法師,我們要狩獵的動物就會全無影蹤。如果我們不聽從他們的勸告,我們就會生病、死亡。”[5]這個時期的原始人個體已經在實踐中掌握了包括說話、制作工具和用火等多種技能,從生理和各種條件來看,他們已經進化成“人”,不過還沒有“人”的意識,或者說還不敢有“人”的意識。每個人就像洪荒中的一棵樹、一株草、一只獸,自然界的奴隸是他們的第一身份。直至今天,謙虛的人們還往往自稱“一介草民”。人和物不分的現實告訴我們,那時的人們只是自然界的財產。但他們已經通過自己的想象給自己制造了神,巫醫、魔法師就是他們與神對話的途徑。這是非常重要的,這意味著人與自然的分化開始,意味著他們知道他們自己的“獨立”存在,意味著他們知道在他們之外還存在無所不能的“神”,他們只能按照“神”的指示(規律)行事。
(三)交換權就是分配權
在這樣一個“個人”歸屬于“人”的時期,在這樣一個人作為“物”歸屬于一元自然的時期,一切都是同一的。同樣,交換權與分配權是統一的。也就是說,權利的劃分只是現代人的法律觀念,在那時是不存在的。原始財產是作為分配權和交換權的統一而存在的。
從“個人”歸屬于“人”的角度來說。“個人”的“我的”“你的”“他的”是不存在的。“個人”只是作為“人”的財產存在的。男女家庭分工、部落生產協作、各取所需都是“神”的旨意,是自然而然的結果。就像一顆種子落地、生根、發芽、立桿、分枝、開花、結果一樣。養料在這株成長的樹里自然分配,使這棵樹茁壯成長。但一個事實是,樹葉帶來了陽光,根系帶來了水分,樹皮作為導管,木質支撐了葉、根、皮,作用各不相同。沒有分工就沒有這棵樹,就沒有養料的分配。若說截留某部分的養料給其他部分,那無疑是要毀掉整棵樹。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分配權和交換權是統一的。
從人作為“物”歸屬于一元自然的角度來說。古人的存在是粗陋的原始共產主義的存在,他們完全置身于自然界的“幸福”牢籠中,這就是所謂的“大道”彰顯的時代。他們被自然界的神力擠壓在一起成為一支隊伍,只有無縫團結才能維持這支“無始無終的隊伍”的存在。這個時候,人與“獸”、人與“物”處于完全競爭狀態,人“獸”不分,人“物”不分,這支“無始無終的隊伍”地位不高,在“猛獸群體”面前往往只能望風逃竄,他們也只會被另一個陌生的部落當作一個“猛獸群體”。人的地位不但不高于獸或植物,可能還處于劣勢,山、木、草、水等都可能成為人崇拜的“圖騰”和“神靈”。自然界就是前面所說的那一棵樹,這棵樹的組成部分就包括人,人按照自然秩序在其中扮演分工角色并分得生存資料。就像蜜蜂一樣獲得了花蜜,但它同時也傳播了花粉,使花兒得以繁殖生長,維持著這個生態群落的存在。分配權和交換權是統一的。
二、交換權的獨立
第二個時期就是被稱為“游牧時代”、或者“農耕時代”、抑或“食物生產者時代”的新石器時代。由于世界各地古人類進入時間很不相同,我們只能為這個時期確定為一個時間范圍,大致在距今1萬年前到2000年前。這個時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財富的產生,“人”因財富而分裂為一個個據有財富而獨立的“個人”。“個人”獲得了最初的自由,打破了人的互相依賴為基礎的社會存在狀態。這是一個人對物的依賴為基礎的社會存在狀態,人和物實現了分離,交換權凸顯出來。這個時期離我們并不遙遠。
(一)人和人的分離
古羅馬執政官西塞羅曾重點提到過羅慕洛斯時期的兩種主要財產:土地(loci)所有權和家畜(pecus)。“從這兩種財產,我們得出‘財富(pecuniosus)與‘富有(locuples)的詞語。”[6]財富的概念就此產生,與之相伴的是財產概念的出現,但從邏輯意義上來說,財產遠早于財富。根據摩爾根的描述,家畜是當時的超級財產,其價值超過人們以前所知道所有財產的總和,其具有充當食物、交換商品、贖回俘虜、支付罰金和用作宗教儀式上的犧牲等多種功能。另外,又因為家畜能夠無限繁殖,對它們的占有就意味著擁有無窮無盡的物資,于是人類頭腦中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財富的概念。其后是農業的進步,人類開始對土地進行有組織耕作,據此家族和土地緊密地結成一體,成為財產組織。當時,希臘、拉丁和希伯來父權制部落(包括仆從與奴隸家族)中都有這種情形出現,父親和子女的勞動日益與家畜繁殖、土地耕種和商品制造成為整體。這就使當時已是專偶形態的家族個體化,還因子女的勞動在家族財產創造過程中的貢獻而催生了繼承特權。毫無疑問,此時的畜群、土地等按照自然法仍是歸胞族、氏族和部落所有的。但人不僅在社會條件上、生理上,并且在意識上,已經事實上作為獨立于部落這個無縫團結的“人”——或者叫“物”——的人的角色出現了,尤其是各個家長們。“土地的耕種證明整個地球表面均可產生歸個人所有的財產,家長已成為財產累積的自然中心。到了這時,人類財產就開始了新的歷程。這種情況在低級野蠻社會之末就已充分完成了。”[7]現代意義上的“個人”出現了,個人的出現是因為個人擁有的財富足以保證其不依賴于那個整體的“人”而生存。但同時也就意味著個人要依賴于作為物的財富才可以“獨立”生存。這就是人和人的分離。
(二)人和物的分離
人和物的分離最起碼是指三個方面:人與自然的分離、人與“人”的分離、人與“財富”的分離。
1.人從作為“物”歸屬于一元自然的狀態發展為人作為意識到自己是人的“個人”獨立于作為物的自然界的狀態。這在財富產生之前是無法想象或者是沒有基礎想象的。在此之前,人除了把自己團結為一個“人”的情況下是無法看到自己的力量的。相比來說,臣服于自然界的力量才是最佳的選擇,這就是巫師產生的直接原因。
2.個人作為其組成部分與作為其存在的前提的作為自然物存在的整體的“人”的分離。而這個“人”正是一個由人、生產工具、不算太多的勞動價值構成的一個“物”。的確,在自然界眼中,甚至在早期人類眼中,也只能是“物”。這個分離就意味著,“個人”首先作為有意識而區別于“物”的人產生了。同時意味著,“個人”和群體、生產工具、勞動產物分離了,這在財富產生之前也是不可能的。因為生產工具、勞動產物等只能是在“人”對抗自然的前提下作為“人”的有機組成部分才能夠發揮作用,一旦分離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
3.“個人”與作為其存在基礎的以物的形態存在的“財富”的分離。這種分離意味著“個人”作為有意識的“人”,作為財富的主宰者的地位的確立。這就是私有財產的產生。一方面,我的財富是我的財產,我是高于作為物的物質財富的,我是主人。另一方面,相較于其他“個人”來說,我是一個獨立的人,誰若膽敢染指我的財產,我必還擊。作為把人、生產工具、勞動產物等作為“人”的財產的自然法在財富產生后已經是名存實亡了。
(三)交換權的凸顯
物質財產的出現摧毀了原始財產的存在形態。使自然一元的世界裂變為人與自然對立的世界。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認為,但實際上,人類與浩渺的宇宙相比那簡直連塵埃都算不上。不過,最起碼在地球這個“自然界”、這個生態系統中我們可以這樣說:這是一個人與自然相對立的二元世界。而這個世界的精彩部分卻在于人類社會。這個社會中人與人分離,人與物分離,人與社會分離。在這些分離的現實中,原始財產作為分配權和交換權的統一體同時分崩離析了。交換權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凸顯出來。
1.人與人的分離意味著交換權的產生。首先是同一部落內產生了差異。首領、家長等離財富近的人能夠先占、多占,占據地理位置好的人當然有對財富占有的優先權,壯碩的也可能多分強占。伯克說:“有可能你周圍的許多資產是憑借武力取得的,那是幾乎與迷信一樣惡劣的事情,而且不乏無知。然而,那是很古老的暴力,在開始時可能是錯誤的事情,卻會被時間神圣化,成為合法的事情。”[8]此類理由太多了,除了這些法學家們經常說的現實占有情形外,還有占領、時效、添附和繼承等方式。而且,他們的占有物往往是各不相同的。其次是不同部落之間也產生了差異。狩獵民族有毛皮產品,農耕民族有糧食產品,游牧民族有畜牧產品。他們的貧富程度各不相同。再次是財富刺激了人們的需要。一方面,相同財富的數量不均導致的人們之間的饑飽溫寒之差異刺激人們追求財富的量;另一方面,不同財富的稀缺性導致的人們之間生活方式之差異刺激人們追求財富的質。而交換就是滿足人們這種受到強烈刺激的需要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手段。你發現別人比你的黃金多嗎?那好,你可以去冒險,從美洲土著手中廉價換來大量黃金,這樣你就擁有比別人更多的黃金了。你發現狩獵民族的皮草能夠保護你的老寒腿嗎?那好,你可以用你的精細糧食與他們進行交換,他們求之不得。
2.人與物的分離意味著交換權的外化。原始財產作為分配權和交換權的統一體,它的交換表現為內部的分工,它的分配表現為生活資料的共同分享。物質財產的產生把這種分工外化了,而作為滿足消費的分配來說交換是一種重要的補充。分工外化表現為耕者、牧者、獵者、漁者等的清晰分立。也有同種分工之差異,比如耕者,其所種莊稼、所獲收成、從事工種、使用工具等也很不相同。物質產品的交換由最初的部族邊緣的偶然行為變成了經常性的行為。人們交換的是物而不是像原先一樣通過內部分工來交換自身的勞動。這樣隨著交換權的載體即物質財產的出現,交換權越來越外化于人了。這種外化,一方面使人進一步獲得尊嚴,另一方面又使人進一步依賴于物。
3.人與社會的分離意味著交換權重要性的進一步提高。原始財產的解體標志著原始安全機制的逐漸喪失,那種同仇敵愾,那一支共抗風險的“無始無終的隊伍”消失了。財富盡管使人脫離了餓死的危險,但并不能使人脫離在睡覺時被野獸吃掉的危險。這就需要巡邏保衛的專職士兵,而如果他們成為專職的士兵他們就不能照顧自己的牛羊莊稼,大家如果不能補償他們的損失,他們是不會去干這件危險工作的。通過這樣的交換,士兵、警察、法官、司禮等職能就產生了。人們通過交換的方式免去了縫補、餐煮、打獵、種田、織布、作戰等多職能的負累[9]。通過工作職能的分化,使社會成為了另一件似乎與“個人”無關但能夠保障其“自由”的外物。這些都要拜交換之功,而分配就隱藏在交換的后面。
三、交換權轉化為分配權
交換權的凸顯伴隨的是人們對交換力的追求,因為這直接決定著人們財富的量和質。東方需要西方的洋酒、名表、雪茄、咖啡,西方需要東方的香料、絲綢、瓷器、茶葉。除了車船舟楫的轉運能力外,物物交換本身的障礙才是交換力不高的更重要原因。貨幣的產生大大提高了交換力,人由對物的依賴轉變為對貨幣的依賴。貨幣實現了人和物的統一。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不再考慮交換的問題,因為人們只需要考慮分配問題了。
(一)貨幣主導人間
貨幣從它起源的那一刻就具備神奇的魔力。
1.貨幣公信力。人類最初貨幣的公信力來源于其超級財產地位,最典型的就是牲畜這種貨幣,最早貨幣的代表是牛,牛羊豬等沒有人可以拒絕。荷馬談到過把牛當貨幣的情景,他說:一套迪奧米德鎧甲價值等于九頭牛,一套格羅卡斯鎧甲價值更是高達一百頭牛。牲畜被實踐所證明的神奇保值增值功能使之得到了古人的普遍認可,牲畜等同于無盡的財富,獲得更多牲畜是那時人們的夢想,牲畜作為一般等價物的地位就是由這種公信力確立的。
2.貨幣便利性。當人們不再質疑貨幣公信力的時候,就開始追求貨幣的便利性,即從最初分散于世界各地不同形制的貨幣中選擇最宜于使用的種類。早期的貨幣包括:牲畜、貝殼、鹽、砂糖、干魚丁、獸皮或鞣皮、煙草、鐵釘等,但它們只能在較小的時空內履行貨幣職能,隨著歷史的發展和交換地域的擴大,金銀逐漸成為貨幣的一般形態。金銀兼具早期千差萬別貨幣的共同特性,并混一了這些初級貨幣,因其良好的稀缺性、易分割、易度量、易保存、易攜帶等優點成為超級財產中的超級財產,用它作為中介物(也可稱中介商品)交換商品再好不過了。在過去的歷史上,人們找不出勝過金銀的一般等價物。它具有資源的稀缺性,不會象牲畜一樣在交易中無法分割,質地均勻(切出相同的大小塊重量總是一致)適宜度量,不會像食物一樣易腐爛,高密度使之具有小件物品易于攜帶的特性。總而言之,世界人民最終都選擇金銀作為一般等價物。所以說:“金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10]這是對交換成本的極大降低。
3.貨幣簡化交換。從經濟的角度來看,貨幣產生以后的世界是一個二次元世界,無論何時何地人們只需要兩次交換就能夠實現自己的目標。人們出售自己的勞動力換得貨幣,這是第一次,再用貨幣換得自己所需的各種產品,這是第二次。但在貨幣產生之前,人們實行的是物物交換,看似直接,實際上卻要通過冗長復雜且耗時巨大的不確定交換鏈條才能夠實現交換目的,而貨幣將之縮短到了兩次交換的最低極限。進一步來說,人們只要手中握有大量貨幣就可以擺脫生產領域,不用再付出勞動,這就是人們所稱的財富自由。在這種情形下交換只剩下一次,即用貨幣換得自己所需的各種產品,當然主要是奢侈品和消費品,也就是生活領域的交換。人們只要有足夠多的貨幣,就有了一切。而當這一次交換也在實踐中不需要了的時候,那就是按需分配。
久而久之,貨幣主導了一切。人們眼中的財富只剩下了貨幣財富,人們眼中的財產也只剩下了貨幣財產,假使還有別的財富存在,那也只是為了保證貨幣的保值增值罷了。貨幣的存在意味著交換權的普遍存在,我們不必再顧慮手中的物換不來東西,也不必再顧慮耗時耗力的長長的物物交換鏈條。
(二)貨幣對人和物的統一
有了貨幣后,我們的眼里看不到物,看不到人,看到的只有貨幣。馬克思正確地指出貨幣的本質是宗教,他指出,貨幣主義的本質是類天主教的,而信用主義的本質上是類基督教的。蘇格蘭人很不喜歡金子,而紙幣只是一種信仰,商品以紙幣信仰為媒介進行流通的存在只是因為社會的需要。這種信仰是對商品內在精神(貨幣價值)的信仰,是對生產方式與其所要求的既定秩序的信仰,也就是對能夠自行實現增殖的資本人格的信仰,即對資本生產者個人的信仰。不過,基督教并沒能從天主教基礎上解放出來。同樣,信用主義也沒能從貨幣主義基礎上解放出來[11]。所以,金銀仍然是最后的決定者。
事實也是這樣,人們的關注點轉向了貨幣,擁有更多物和人的重要性下降,因為擁有貨幣是更現實的選擇。大量貨幣的擁有就意味著按需分配生活的實現,以及各盡所能義務的拋棄。商業場所能夠滿足人們日常吃穿住用行的需要,專業場所有特供產品以及忠誠敬業的保姆和秘書服務。國外的奢華同樣觸手可及,厭惡擁擠的班機?沒關系,豪華的私人飛機和游艇隨時恭候。只要你有大錢。因此,當代社會中財富的通常概念已經從最初的牲畜轉化為金錢。的確,貨幣金錢就是一種超級財富。它具有財富的兩個典型特征,突破了人的消費能力界限和物的保質期界限兩個自然限制。毋庸置疑,金錢的財富特性遠優于禽畜等原初貨幣。它不但能使人們擺脫可惡的勞動,而且保質期無限;不僅可以服務于人們今生,還可以傳承于后代。加之,它是對千差萬別的個性化的物的統一,也是對特定的不同的人的勞動的統一。從而它就統一了一切。我們可以毫不避諱地說,似乎這個世界就是一個金錢的世界。黃金的確是一種奇妙的東西,誰擁有了它,誰就能瞬間成為他所想要的所有東西的主人。有了黃金,甚至可以使人們的靈魂升入天堂(哥倫布1503年寄自牙買加的信)[12]。于是,頌揚金的圣杯成為人們最根本生活原則的光輝體現。然而我們必須批判:“人間再沒有像金錢這樣壞的東西到處流通,這東西可以使城邦毀滅,使人們被趕出家鄉,把善良的人教壞,使他們走上邪路,作些可恥的事,甚至叫人為非作歹,干出種種罪行(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12]貨幣似乎成為了人間的現實的上帝。有它在,人就是物,物就是人。有它在,貴人可以輕賤,賤物可以騰貴。它模糊了界限,它顛倒了黑白。
幸好還有法律的存在,貨幣難以橫行。法律捆住貨幣的手腳,限制它的極端性,同時確定財富的正確歸屬。
(三)只剩下分配權
貨幣是作為交換權和分配權的統一體的貨幣商品存在著的,但是我們似乎只能看到分配權,遺忘了交換權。
1.貨幣交換權的鞏固。這種商品因著它的交換特性為人們所普遍接受。而當它一旦具有這樣的不可撼動的地位時,人們就把它這種使用價值神圣化了,沒有人再去質疑,或者說沒有人可以質疑它的這種地位。這種地位意味著它的索取的不可拒絕性,而這種索取本來就是它所具備的分配權,也即它的勞動價值。而這種勞動價值因為勞動者的個體差異導致的個體勞動價值的差異性而成為一般社會勞動的標準。個體勞動只能與這種勞動價值比對出價,而不可能反過來出價。換句話說,貨幣要取得多少勞動,社會就必須給它多少勞動。當貨幣這樣“統治”了社會以后,傻瓜都知道要向貨幣這唯一的標準看齊。人們不再考慮能不能交換的問題,因為,有貨幣在就必然能夠實現交換。
2.貨幣分配權的凸顯。人們轉而要考慮手中的貨幣能夠分得多少人的勞動價值,多少勞動產品,什么勞動產品的問題。假使國內的馬桶人們覺得不值,那一定是要跑到日本或者別的什么國家去購買的。從而貨幣的量成為人們考慮的重點,越多的貨幣量意味著能夠分得越多的勞動產物。由此,交換權和分配權的關系發生了質的變化。曾經的分配權因交換權的存在才能夠存在,曾經的勞動價值因使用價值的存在才能夠存在,現在反轉過來了。曾經凸顯的交換權讓位于曾經隱匿的分配權,曾經被重視的使用價值讓位于交換價值,由此,交換權讓位于了分配權。
3.貨幣交換權演化為貨幣分配權。我們可以看到,經過這么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人類由對最低限度生存的追求階段進入了對財富追求的階段,進而又發生了對物質財富的追求階段轉變為對貨幣財富追求的階段,對貨幣財富的追求最后轉變為對分配權的追求。完成了財產由交換權到分配權的演變過程。
四、演化的后果
財產由交換權到分配權的演變是人類進步的結果,其積極意義不言而喻。我們需要關注的是其消極后果,應當注意進行應對。其消極后果主要有三,一是社會的金錢化,二是財富的泡沫化,三是經濟的空心化。
第一,社會金錢化的本質是貨幣分配權的極端化。人們在爭奪貨幣時,早已不關心它的使用價值,它代表的是可以分得多少勞動價值的分配權。物質財產轉變為貨幣財產,財富由交換權轉化為分配權,只剩下了分配權。金錢化的社會已經不是原始意義上的經濟社會,而是貨殖社會,或曰GDP社會。亞里士多德對此早有論述,他區分了經濟和貨殖。他認為,經濟僅僅是謀生術之一種,它的限度是對家庭或國家有用的生活必需品,這些是真正的財富,其本質是使用價值,用于滿足優裕生活的需要且數量并非無限。而另一種謀生術就是貨殖,它模糊了財富和財產的界限。商品交易(■καπηλικη,按字面意義是零售貿易,亞里士多德采用這個形式,是因為在這個形式中起決定作用的是使用價值)的性質并不是貨殖,人們交易的目的是為了換取他們自己(買者和賣者)互相需要的物品。但當貨幣發明并大行其道的時候,物物交換發展為商品交易,并拋棄了它的最初的宗旨,化為貨殖,變成了賺錢術。經濟是有界限的,而貨殖是無窮的,前者的目的是使用價值而不是貨幣本身,后者的目的就是不斷增加貨幣。世人錯把兩種謀生形式混為一談,誤認為無限地存錢和賺錢就是經濟的根本目的(散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貝克爾編,第1篇第8、9章)[12]。從而,金錢統治一切。
第二,財富泡沫化的本質是貨幣分配權的泛濫化。金錢社會直接導致了社會的泡沫化。人們更關心的是能夠獲得更多的貨幣量,這就是我們市儈化所說的賺大錢。生產者不管產品是否有用,賣出去就行;勞動者不管你生產什么,能多給我開點工資就行;債權人不管把錢借給好人壞人,能按時拿到利錢就行。貨幣分配權與價值相分離,甚或導致壞的使用價值(財富)荼毒社會。另外,由于貨幣的進化,金銀作為儲備退居二線,各國紛紛發行具有主權性質的法定紙幣。紙幣是適用于一國范圍的等價職能,是對金銀貨幣商品職能的剝離,是貨幣的進一步提純與抽象。紙幣已經不是商品,是沒有類似于金銀使用價值的等價物,它現在只是分配權。我們在銀行的不同存款已經不是黃金白銀,而是一個個不等的數字,這些數字的大小表示社會對我們的債務額度,我們據此可以從總的社會勞動產品中分配到我們應得的數量。工商界和金融界首先創造了金銀信用基礎上的匯票,隨后又發明了種類各異的有價證券,包括:銀行券、股票、國債、債券、期貨、虛擬貨幣、電子貨幣、數字貨幣等。但無論如何變化,它們都是貨幣的分身與化身,其與它們的本體貨幣一樣擁有著同樣的效能。這時,一個鍋底那么多的水在貨幣的泛濫下淤出鍋來,看起來一片繁榮。
第三,經濟空心化的本質是貨幣分配權的虛擬化。社會金錢化的結果是財富泡沫化,財富泡沫化的結果是經濟空心化。整個社會都陷于瘋狂的賭博游戲中,比如當年的荷蘭郁金香事件。人們無心于財富的創造,只熱心于財富的攫取,而這種可能就是貨幣分配權提供的。當潮水退去的時候,我們看到了裸泳者們。這是最糟糕的結果。由于實體經濟的覆滅。或者如上面所舉的例子,連一個鍋底那么少的水都蒸發干了。人們能夠得到的也就只有貨幣,也就只有分配權,然而可分配的財富卻不存在了。歷史上每每出現這樣的悲喜劇,端著金飯碗餓死。
五、可能的對策
應對貨幣分配權的極端化、泛濫化和虛擬化一直是各界研究的熱點。我們在此適當探討一下財產演化后果的相關對策。
斯密以后,主要的西方經濟學家如李嘉圖、凱恩斯等都是研究分配權的。“爭論卻從洛克的自然法則和神的理性的豐裕狀態轉變到了休謨的稀缺狀態中的短缺和便利。”[13]休謨提出了“沒有財產,就沒有非義”[14]這個命題。
馬克思《資本論》論述了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馬歇爾搞出了一個折衷主義。隨后,凱恩斯針對“看不見的手”提出了宏觀調控。然而,2008年以來的經濟危機至今沒有減弱,大火燃燒到了幾乎所有國家。所以,這些曾經的靈丹妙藥在當今面臨捉襟見肘的尷尬處境。而新冠病毒的肆虐使這種狀況雪上加霜,某種程度上終結了凱恩斯主義等主流經濟理論。也就是說,從分配權本身出發來解決當今問題已經陷于絕境。我們必須回到其原身才能夠找到新的辦法,那就是振興實體經濟。
振興實體經濟有三條途徑:一是政治手段,迅速解決表層的貨幣分配權的虛擬化問題。通過包括宣傳、勸解、交流乃至強制等各種綜合的行政手段打擊投機行為,抑制泡沫乃至消滅泡沫。其目的是讓人們認識到事實的真相與所處的境地。二是法律手段,跟進解決中層的貨幣分配權的泛濫化問題。通過新立法、新判決、新執行等各種法律手段對舊的財產形態進行規范,使之回復到本來的價值基礎。其目的是讓人們把時間和精力轉向財富的創造。三是經濟手段,最終解決深層的貨幣分配權的極端化問題。通過財政、稅收、產業政策、銀行等各種經濟手段限制貨幣的任意創設,控制其流向和使用范圍。其目的是讓人們在當前和未來需要的領域中財產得到保障和獎勵。綜合以上,我們就可以創設出一個適宜于財富增長和財產增值的社會治理機制。
正像威廉·配第所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15]有了這樣良好的環境,我們還擔心“天下財產,何得不蹷”?
參考文獻:
[1]? 司馬光.文白對照全譯資治通鑒[M].馮國超,等,譯.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326.
[2]? 常青.財產哲學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黨校,2017.
[3]? [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M].董書慧,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4]? 陳偉.財產與財富之辨——漢娜·阿倫特的財產觀論析[J].國外理論動態,2015,(11):89-94.
[5]? K.Rasmussen.The People of the Polar North(Lippincott)[M].Andesite Press,2015.
[6]? [古羅馬]西塞羅.國家篇 法律篇[M].沈叔平,蘇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64.
[7]? [美]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古代社會[M].楊東莼,馬雍,馬巨,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396.
[8]? Edmund Burke.Speech on Reform of Representation of the Commons in Parliament,1782[C]//L.I.Bredvold and R.G..Ross,eds..The Philosophy of Edmund Burke.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0.
[9]? [英]亞當·斯密.國富論:下[M].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241-353.
[10]?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45.
[11]? 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70.
[12]?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 [美]康芒斯.制度經濟學[M].趙睿,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7:155.
[14]? [英]休謨.人類理解研究[M].關文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144.
[15]? [英]威廉·配第.賦稅論[M].邱霞,原磊,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13:97.
Evolution of Dual Rights of Property
CHANG Qing
(School of Marxism,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4,China)
Abstract:In the original stage of property,the right to exchange and distribution is the same thing.In the material property stage,due to the generation of wealth,the right of exchange gains independence.In the money property stage,due to the widespread use of money,the alienation of exchange right is the right of distribution.Which caused the money society,foam society,and hollow society.One way to change all of this is to create a new social governance mechanism.
Key words:property philosophy;evolution;real economy;social governance
[責任編輯 百 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