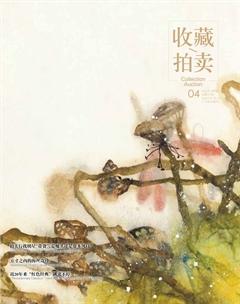“偷拍”作品攤上事,別拿藝術糖衣唬大眾
朱真真

前段時間,OCAT 上海館展出的作品《校花》引發熱議。該作品是作者宋拓通過偷拍一所學校里近5000 名女大學生,并按個人審美喜好將女生們進行顏值排序而產生的。作品一經展出,就引發網上眾多的批評和討論。面對質疑,宋拓的回應是:物化女性,是我對她們的尊重。
其實,藝術家在藝術作品中使用大眾影像并不少見,在徐冰的作品《蜻蜓之眼》中,也基本是對監控中大眾影像的借用,但與宋拓《校花》不同的是,徐冰盡可能地征求了視頻提供者、出現者的授權。在這一過程中,徐冰并非利用監控來操作、評價影像中的人,相反他在這之中為大眾提供了一種藝術的參與手段,發現了一種“參與式文化”。我們在《蜻蜓之眼》中看到的是藝術家對現代人精神癥狀的描述,對圖像本身的思考和對監控這一權力視覺的警示。
但在《校花》創作中,宋拓顯然在把藝術當做一種特權。在這種“權力”的加持下,他建立一個所謂“真實的個人標準”,一個以“好玩”(引自對其個人的采訪)為目的的排名體系。在這里他成為審美評價王國的自封之王,將一個個陌生女性變為其彰顯自己權力的數字。當他被問及排名的客觀性時,他提到:“半年以后品味都變了,我當時很喜歡某一種類型的女孩子,就把這種類型的通通放在前面了,后來我就覺得這類型的有點沒勁了。”宋拓作為作者很享受這種在作品中的支配權,并且在對其作品的介紹中肆意地評價、戲謔,以他自以為“幽默”的話語對項目中的女性進行二次傷害。
“物化女性沒有關系……我掏心掏肺地物化你,這也是一種尊重……最后一名,我把她們放在對的位置上,這就是尊重她們,特別特別尊重。”而這種“玩世不恭”的犬儒主義態度反而被包裝成“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英雄主義,被一些人稱贊其具有反抗精神。藝術在《校花》中就仿佛皇帝的新衣,被庸俗化的學術詞匯包裹著對《校花》的闡釋護衛著藝術的“高貴”,仿佛只有能夠理解、認同這一項目的人才是“真實的”,才真正懂得藝術。
此次點燃《校花》爆點的并非是觀展者的個人聲音或是受害者的維權,而是展館OCAT 上海館微信公眾號的推文。在6 月17 日的展館推文中介紹了宋拓及其作品《校花》(現已刪除),時隔一天,又在官方微博上發表了“重新審視”決定撤展的聲明。但網友對美術館的這一聲明似乎并不買賬。
盡管美術館的權威在中國藝術領域中已經不同于往日,但這并不意味著美術館在對展品的選擇上沒有發言權或可以全權交給策展人。引用知乎大神莊澤曦對《校花》這件作品的評價:“這個作品從不同視角看,其價值是不同的。從市場角度看,這也是一件好作品,因為它可以被闡釋為對目前女團現象的一種諷刺,并在可預見的未來還能再次利用(請給策展人打錢;給闡釋者揚名;作品不是藝術家一個人的,絕不能獨占),還能引申出另一個問題,即在數字/ 網絡藝術技術普及的今天,藝術家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是否能以策展人(更專精于理論生產、影像批評、藏家人脈和宣發推廣的人)為中心呢?”
在美術館為歌頌藝術自由而放寬展覽門檻的同時,館內的展品依舊是被選擇的,這就無法避免地代表著一種權力和態度。因此,美術館與博物館在新的藝術環境中,并不能以藝術自由為名義簡單地放棄所有標準。放棄所有標準也意味著自我消解,因此美術館只是在注意力經濟的操縱下以挑戰法律和道德為其“自由”的符號,相反,建立一個更加多元、包容同時更具態度的標準才是其迫切需要思考的。
如今,盲目推崇藝術的時代已經過去,當藝術的光環褪去,所有假借藝術為名,泥沙俱下的展覽顯然已經無法簡單地靠“藝術”兩字的魔力“唬”住大眾,被資本包裝為“藝術”的罪行已無處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