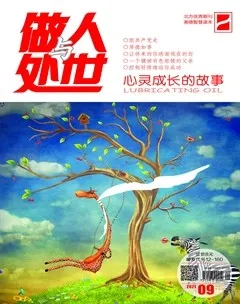瑕疵讓美有光
朱成玉

只要放對位置,任何事物都有意義
有一次,上林竹庵請茶道宗師千利休參加茶會。千利休答應了,還帶著眾弟子前往。上林竹庵非常歡喜,在千利休和弟子們進入茶室后,開始親自為大家點茶。但是,由于他過于緊張,點茶的手有些發抖,致使茶盒上的茶勺跌落、茶筅倒下、茶筅中的水溢出,顯得十分不雅。千利休的弟子們都暗暗地在心里發笑。可是,茶會一結束,作為主客的千利休就贊嘆說:“今天茶會主人的點茶是天下第一。”弟子們都覺得千利休的話不可思議,便在回府的路上問千利休:“那樣不恰當的點茶,為什么是天下第一?”千利休說:“那是因為上林竹庵為了讓我們喝到最好的茶,一心一意去做的緣故。所以,沒有留意是否會出現那樣的瑕疵,只管一心做茶。那種心意是最重要的。”
那樣小小的瑕疵,反而讓千利休覺得完美。在千利休看來,真正的完美里必須有瑕疵的成分。他以瑕疵來襯托美,甚至特地找老手工藝人制作粗糙的茶碗。
千利休的兒子在打掃茶室的庭徑,完畢之后報告父親。千利休認為不夠干凈,吩咐他再掃一次。過了一個多小時之后兒子再次稟告,說地上干凈得哪怕一根小樹枝一片落葉都沒法找到。千利休走入庭中,抓住一棵樹干搖將起來,院內頓時灑滿紅黃落葉,片片皆是秋之錦緞!“這才打掃好了!”千利休說。瑕疵便如那人生的落葉,永遠無法打掃干凈,何不順其自然,讓它成為你生命里美麗的點綴?
所有人都認為千利休有著鬼神般的茶道創作力,他的一舉一動都能使普通的事物帶有特殊的美感。然而這一切看似圓滿的核心卻是帶有瑕疵的,就好像一顆沙子在蚌殼里變成美麗的珍珠一樣。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人生真是匆匆,剛談得投機就又要分手”等,都讓人無可奈何。張愛玲在《紅樓夢魘》里有個話頭:“有人說過‘三大恨事是‘一恨鰣魚多刺,二恨海棠無香,三恨紅樓夢未完。小時候看紅樓夢看到八十回后,一個個人物都語言無味,面目可憎起來,我只抱怨‘怎么后來不好看了?……很久以后才聽見說后四十回是有一個高鶚續的。怪不得……”且不論后四十回到底是不是高鶚續寫的,但我想,就算是曹雪芹本人,也不敢保證后四十回就完美無瑕吧。正是因為有遺憾,才讓人無比懷想期待中的完美。接納它們,它們就是一種美。
散文家張曉風很喜歡曾國藩“闕”的境界,她說:“曾國藩把自己的住所題作‘求闕齋,求闕?為什么?為什么不求完美?那齋名也使我著迷。”“求闕齋”,有闕為美,是中國哲學極其深邃的一種心靈向度和人生智慧。曾國藩憑自己的器識和人生閱歷,一眼就看透人性弱點,認為“其一損一益者,皆自然現象,物生而有嗜欲,好盈而忘闕”。明白人性有缺的本質,才是個明白人,就懂得宇宙萬物的此消彼長,如同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其執黑守白、皆符合造化之理,他深諳其客觀規律,“求闕齋”的齋名,泄露了他洞穿人生的高妙目光。
念這悠悠世間,多少未完成的事,不必為此太過遺憾。爬不過去的山,仍然橫亙在那里,那么不妨就把它畫到畫板上來,順便把白云也移過來,身體過不去,心總飛得過去吧。靠自己雙手培育的幸福,雖有殘缺,也是令人滿足的,余味繞梁。
(責任編輯/劉大偉 張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