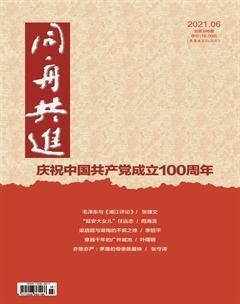大明穿戴那些事兒
袁燦興
【民間穿戴,率性而為】
服裝是身體的延展,愛美是人的本能,人們習慣用衣裳營造出賞心悅目的效果。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曾總結元代滅亡的經驗,認為元代風氣過于奢靡,僭越禮法,一般民眾衣食起居與公卿無異,奴仆“往往肆侈于鄉曲”,導致“貴賤無等,僭禮敗度”。
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朱元璋下詔“復衣冠如唐制”,詳細規定了皇帝、太子、大臣的服裝,此后不斷頒布涉及服飾的各項規定。不但官員們的朝服、常服有著繁瑣規定,就是引車賣漿的平民們的服飾,朱元璋也親自過問,參與設計,再三修改。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令,庶民不論男女,其衣服不得用金繡、錦繡之類,鞋子不得裁制花樣,不準用金線裝飾,佩戴的首飾只準用銀,不許用金玉、朱翠等。洪武六年(1373年),又下令庶民巾環不準用金玉、瑪瑙、琥珀之類。平民的帽子不準用頂,帽珠只許用水晶、香木,甚至規定庶民不準穿靴子。可北方冬季寒冷,總不能讓平民穿著單薄的鞋子外出,迫不得已之下,朝廷只好做出變通,徐州以北的地區可以穿靴,以御寒冬。
但嚴苛的服飾規則,遇上復雜的社會生態,和眾生追求新、奇、美的心理,終究是要冰雪消融的。
早在洪武三年,民間就罔顧禁令,衣服采用黃色,在服飾上繡上古代帝王、圣賢人物及各類龍鳳、麒麟圖像。教坊司的婦女已被打入樂籍,身屬賤民,更無忌憚,穿綢緞衣服,佩金銀首飾,街市往來,坐轎乘馬,屢禁不止。衛道士們痛心疾首地斥責:“輕薄子弟,厭常斗奇,巾襲晉唐,衣雜紅、紫,競相慕好,汰奢無己,實為服妖。”
外來的稀奇服飾,更是受到舉國上下的追捧,引起了不少風波。最先發起沖擊的,是來自朝鮮的馬尾裙。
成化年間,朝鮮國使臣來到中國,他們穿著馬尾裙出沒街市,立刻被京師中人效法,之后風靡一時。馬尾裙以馬尾制成,系在襯衣之內。穿上馬尾裙的好處是,它使人整體看上去更加豐滿,衣著如同撐開的傘,行走之間,姿態萬千。
最初穿馬尾裙的人主要是商人、富家公子與歌伎,后來朝內武臣效法,京師之中多有織賣者。馬尾裙之風行,以至于不論貴賤高下,都穿上這種裙子。個別內閣大學士,一年四季,不論寒暑,都是馬尾裙不離腰。作為禮部尚書的周洪謨,本該遵循禮法,可他喜歡也就罷了,卻還要穿上兩層馬尾裙,讓衣服更加膨脹。年輕的公侯伯爵、駙馬,還覺得馬尾裙張開的弧度不夠,在裙內繃上弓弦,增強效果。
馬尾裙的流行,也帶來了一個棘手的問題。要制作馬尾裙,就需要大量的馬尾,民間的馬尾被采光之后,馬尾缺乏,市價日貴。軍營內的馬匹被人給盯上,不時發生偷拔軍馬馬尾的事件。軍馬被硬生生拔去尾巴,痛楚難當,不思飲食,日益清瘦。有官員利用此次契機,主動出擊,稱偷盜馬尾,有誤軍國大事,請求嚴禁馬尾裙。最終,在朝廷的強力干涉之下,馬尾裙暫時消失,軍馬們再次留起了漂亮的馬尾。
走了馬尾裙,其他的各類服飾次第而起。蒙古的曳撒,便是“后起之秀”。
曳撒受蒙古的生活影響,在下擺豎向“密密打作細折”,在腰間橫向打細折。這本是蒙古人騎馬需要,縮緊腰圍。可在明人眼中,此種服裝鮮艷好看,外形華麗。明人所穿的曳撒,主要在下擺打褶,中間則無褶,比較平坦。曳撒與馬尾裙本是最佳組合,二者搭配,更顯出裙子蓬松如傘的效果。
曳撒不但為士人所喜,也為皇帝所鐘愛。成化皇帝游玩時,身著大紅織金龍紗曳撒,弘治皇帝退朝之后,一身曳撒。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德帝朱厚照從宣府回京,命京師百官戴蒙古人的大帽,穿蒙古人的曳撒迎接——這完全背離了祖先之制。不過也有人敢與皇帝較真,監察御史虞守隨就勸告皇帝:“蓋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以有禮義之風,衣冠文物之美。”正德對此嗤之以鼻,毫不理會。
明初曾建立起一套復雜的官員服裝規定,但這套規定,后來被逐漸打破。自成化、弘治以后,官員以穿蟒服為榮。蟒無角無足,龍有角有足,官員們卻不在乎,穿上“有角有足”的蟒服出入公堂。最甚時,宮中的太監也一身蟒服,無人來管。
這種“僭越禮制”的現象,在《金瓶梅》中有較多反映,西門慶每日騎大白馬,頭帶烏紗,身穿五彩灑線揉透獅子補子圓領,“獅子補子”只有一二品武官才能使用,西門慶是五品武官,按規定只能用“熊羆補子”。麒麟服本是公侯、駙馬、伯爵的服制,此時也被庶民隨意穿著,如《金瓶梅》中的吳月娘、春梅。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李嬌兒一人做了一件“錦雞緞子袍兒”,依照禮制,只有二品文官才可在補子上使用錦雞紋樣。
明初厘定禮法,妓女在著裝上受到嚴格限制。“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不許錦繡衣服”“不許戴冠”等。但到明代中晚期時,妓女們已突破了昔日的繁瑣禁制,以服裝展示自己身體之美。衣著面料以紗羅錦緞為主,色彩上朱碧紅紫,工藝上織金繡彩,款式上異色花樣,首飾上金玉寶石。“去船盡是良家女,來船雜坐娼家婦。來船心里愿從良,去船心已隨娼去。”這寫的是妓女們服飾華美,甚至讓良家女子心生羨慕。
明代以赤色為尊,原因在于朱元璋“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大紅服裝一般只有朝廷命官才能穿,庶民,特別是女性,不能隨意穿大紅色衣服。到了萬歷年間,妓女之中流行大紅縐紗夾衣,灑線繡,這也很快在民間流行開來,甚至連販夫走卒、一般傭夫也穿紅襖。名妓陳雪箏色藝雙絕,“都中時態新妝,多出其手,合度中節,仕女皆效之”。

《金瓶梅》第五十三回中,妓女李桂姐穿的“五色線掏羊皮金挑的油鵝黃銀條紗裙子”,潘金蓮說是“里邊買的”,也就是“宮裝”。這宮裝不但用了“羊皮”,還是黃色。
正德年間,服飾風格發生了巨大變化。此時的民間穿戴,率性而為,追隨潮流,“寬袖低腰,時改新樣”。松江地方上的男子服飾款式多變,時而變胡服,時而又變為陽明衣、十八學士衣、二十四節氣衣之類。艷麗色調被保守士人深惡痛絕,可紫紅色服飾在讀書人中日益流行。范濂提到,松江儒童之中流行穿絳紅道袍。范濂貧窮,崇尚儉樸,可也開始穿大紅大紫色衣服。
在一些“癲狂士人”中,還流行“男著女裝”。唐伯虎一身女裝,與和尚逍遙下棋。蘇州人卜孟碩,夏季挽高髻,著大紅苧皮袍,赤腳在街市上且歌且行。《續見聞雜紀》中記載,李樂隱居鄉間,某日進城,看到城內讀書人都是艷麗打扮,紅絲束發,唇涂紅膏,面抹香粉,著紫紅衣服。遂作打油詩云:“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襟。遍身女衣者,盡是讀書人。”
至明末社會動亂,遼東戰事經年不息,便有人指責服飾是禍害。顧炎武就認為“萬歷間遼東興冶服,五彩絢爛,不三十年而遭屠戮”,李漁則認為“風俗好尚之遷移,常有關于氣數”。
【“蘇樣”的魅力】
明代中后期,時尚潮流的中心是蘇州,蘇州流行的吃穿住行、娛樂方式及各類精致器物,統稱為“蘇樣”,也叫“蘇意”。
吳中素來人才輩出,物產豐饒,宮中各類御用物品尤其是紡織品,多取自蘇州。據文徵明記載,蘇州織染局有房屋二百四十五間,織造工匠不下千余人。司禮監專設有蘇杭織造太監,在蘇州督造。蘇州城中,家家戶戶都有從事絲織業者。蘇州紡織業的發達,帶動了服裝業的繁盛。而蘇州周邊的松江、杭州、嘉興、湖州等地,商賈云集,店鋪密布,也成為蘇樣服飾的強力消費軍。
“蘇樣”衣服初期顏色鮮艷,絢麗無比,后改為清雅的風格。熱衷于時尚的男士們,也從著紅紫之服,轉而變為崇尚清淡色調的服裝。晚明“蘇樣”服裝中流行白色,時有俗語云“要待俏,三分孝”,《金瓶梅》中,西門慶眾妻妾多穿著“錦繡衣裳,白綾襖兒,藍裙子”,便是受此風的影響。“蘇樣”衣服在款式上也呈現出多變的態勢,如上衣時而長過膝蓋,時而僅僅及腰。袖子時而寬松及地,時而短窄收縮。紋飾也漸變為素雅淡泊,女裙只在裙角繡上一圈花紋而已。
當日的蘇州,無疑是時尚之都。風和日麗,抑或鮮花盛開之時,男男女女們,換上流行的服裝出游,成為亮麗的城市風景。當時流行的時裝,男性服裝以高冠、道袍為代表,女性服裝則以月華裙、水田衣為代表。如同今日的皮靴、西服、領帶一般,高冠、道袍、淺履,堪為“蘇樣”男式服裝的經典搭配。
道袍寬松,衣袖寬大,衣長過膝,風起時衣帶飄飄,使穿者看上去仙風道骨。道袍的這般出塵效果,使得它流行于士人及富人之中。道袍之妙,在于寬大的衣袖,出塵氣息的營造全靠它。為了追求飄逸效果,“蘇樣”道袍袖子越做越大,最后“有大至二尺七寸者”,有看不慣者諷刺道:“兩只衣袖像布袋。”
“蘇樣”道袍用料講究,手工精湛,價格不菲,不是一般人家可以負擔的。《警世通言》中,宋敦將身上穿的潔白湖綢道袍脫下道:“這一件衣服,價在一兩之外。”
“蘇樣”風行,善于舞文弄墨的蘇州人馮夢龍自然不會放過。他在《古今譚概》中講了系列有關奇裝異服的故事。蘇州進士曹奎,穿大袖袍,大概因為袖子的尺寸過于夸張,讓人不解。楊衍就問他:“袖何須如此之大?”曹奎昂然道:“要盛天下蒼生。”楊衍笑道:“盛得下一個蒼生就已經不錯了。”
僧人所穿的鞋子,以布帛為面,大口,薄底,鞋幫較低,穿著輕便舒適,也受世俗男子喜歡。“蘇樣”淺面僧鞋,采用上等絲綢制成,上繡有各類花紋,顏色艷麗。
杭州一名官員,笞打了一名腳著“蘇樣”淺面僧鞋的家伙,并將他枷號示眾。在書寫封條時,官員靈機一動,寫下“蘇意犯人”四字,警告杭州市民,不得受“蘇樣”的影響。可“蘇樣”魅力還是無法抵擋,蘇州興起的百柱鬃帽,浮浪少年無不戴著招搖過市。就連清修的和尚道士也生了俗心,私下購置一頂,以備扮裝俗人,出去玩耍,挑逗一番美嬌娘。
在追求新鮮、引領時尚方面,蘇州婦女更不輸男子。所流行的“月華裙”精致華美,巧奪天工,價格十倍于一般裙子。“月華裙”一開始是用六幅布帛,至明末開始用八幅布帛,穿著的人行動起來,觀之如水之波紋。后來又出現有十幅之裙,每一幅用一種顏色,十種顏色各不相同,“風動色如月華,飄揚絢爛”。
“水田衣”則是以零碎的衣料拼結縫制而成,衣料色彩多樣,交錯若水田,由是得名。水田衣早在唐代就已出現,有“裁衣學水田”之說。到了明代,水田衣的制作,不再講究衣料拼結時的均勻,而是雜亂隨意,猶如渾然天成。水田衣從一般民婦的穿著,成為大家閨秀之愛,并一度成為時尚。

揚州繁華不亞于蘇州,但在服裝上卻受到蘇州影響。
“杏放嬌紅柳放黃,誰家女子學吳妝?”“吳妝”,正是指“蘇樣”。揚州府治下的通州,深深受到“蘇樣”的浸染。風氣所至,當地人如果穿著無顏色、無花紋的樸素衣服去赴宴,連鄉下人也要對其加以恥笑。
張岱認為,浙江人沒有主見,凡是蘇州所流行的款式,都要極力模仿。可在時尚的追逐上,浙江總是落后蘇州一拍,是故蘇州人取笑浙江人為“趕不著”。雖然趕不著蘇州的時尚腳步,可在膽子上,浙江人卻高過蘇州人。在浙江余姚,一般庶民穿著士人的方巾常服,為了吸引眼球,甚至“飾以王服”,可謂“膽大包天”了。
崇禎帝的周皇后是蘇州人,最喜在夏季穿純素白紗衣,被崇禎帝稱贊為“白衣大士”。田貴妃入宮前在揚州居住,受“蘇樣”影響,入宮之后,一切穿著仍是南方式樣。田貴妃的母親每年都要根據“蘇樣”制作最時髦的衣服送給女兒,以讓她在后宮的競爭中保持不敗。
其實,“蘇樣”只是明代蘇州諸多時尚中的一種,其他如蘇戲、蘇繡、蘇酒、蘇妝等,無一不為時人追捧。古董收藏、書畫鑒賞,被士人稱為“姑蘇人事”。南京秦淮河上的青樓女子常自稱是蘇州籍,以求嫁個好人家,改變命運,外人戲稱這些青樓女子為“小蘇州”。很多徽商娶了“小蘇州”后,卻發現她們是與自己口音一般的安徽同鄉。
潮流終究是無法阻擋,流行時尚,自有它的市場。對于新鮮事物,人們需要一個心理轉變的過程。明代以后,“蘇樣”雖然不再主導時尚潮流,可一個個新的潮流卻在不斷涌現,一直延及今日。
【“山人”與頭巾天地】
在明代,小小的一方頭巾,用途卻很大,它成為區分身份的工具,被賦予了諸多意義。朱元璋甚至以行政命令推行頭巾,其中最有名者,莫過于“網巾”及“四方平定巾”。
明代男性用來束發的網,類似魚網,網巾口以布制成,有金屬圈可穿身,用以收緊頭發。網巾的由來,也有段故事。一日朱元璋微服私游,至神樂觀,看有道士在燈下結網巾,就問這是何物。道士云:“網巾,用以裹頭,則萬發俱齊。”
萬發俱齊,在朱元璋看來有“萬法俱齊”之意,遂決意將網巾推行天下,不分貴賤,一律使用。次日,朱元璋召見道士,命為道官,取網巾頒布于天下。
在明代的服飾等級制度中,網巾是唯一沒有身份之別、人人可以使用的服飾。后人將“網巾、不用團扇用折扇、濱海之地不運糧”,視為前代所未有,明代之獨創。明清鼎革之后,網巾更被視為最能代表明王朝的衣飾,抗清人士紛紛裹著網巾,投身于反清復明大業之中。
網巾使用馬鬃、絲線或絹制成,至于窮人,則使用頭發編成的網巾。《醒世姻緣傳》中,一個窮秀才的母親就靠織賣頭發網巾為生。網巾的廣泛使用,使它成為成人的象征。男子成人儀式中,首先要束發加網巾。
明代還有著名的“四方平定巾”,此巾平頂四角,以黑色紗羅織成。四方平定巾的巾式不時發生變遷,或高或低,或方或扁,或仿晉唐,或從時制。明初曾規定,士人、庶民皆可戴方巾,但實際上只有身負功名的讀書人才能戴。方巾青衫,乃是儒生的標準形象。若是平民違規戴了方巾,被儒生們看到,又要生出是非了。
唐巾是以烏紗制成的一種頭巾,下垂的兩腳襯向兩旁分開,成八字之形。在保存下來的唐人畫像中,帝王都戴唐巾,明人從中汲取靈感,復興唐巾。不過唐巾復興后,地位一落千丈,成為喪事中的常用物。《金瓶梅》中西門慶為李瓶兒辦喪事,“外邊小廝伴當,每人都是白唐巾、一件白直裰”,卻是將唐巾作孝帽了。西門慶去世之后,孟玉樓與潘金蓮、孫雪娥等人七手八腳替西門慶戴唐巾,穿壽衣。
明代最受士人歡迎的應屬“東坡巾”。東坡巾與方巾同是平頂四角。不同的是,東坡巾外又加重墻。方巾戴時平面在正前,東坡巾則角綾位于兩眉之間。東坡巾佩戴較廣,西門慶去妓院與愛月兒相會時,頭上戴東坡巾,身穿補子直身,腳穿粉底皂靴。
洪武三年規定,樂工、伶人、娼妓等地位低下之人,只能穿綠色衣裙,戴綠頭巾,以與士人庶民區別開來。“綠頭巾”更演變為一種帶有侮辱性質的頭飾。
正德中期,京內只要一有新款頭巾出現,各行各業中人便會群起仿效。顧起元在《客座贅語》中記載了南京戴巾的潮流變化:“士大夫所戴,其名甚伙,有漢巾、晉巾、唐巾、諸葛巾、純陽巾、東坡巾、陽明巾、九華巾、玉臺巾、逍遙巾、紗帽巾、華陽巾、四開巾、勇巾。”《泉州府志》中,也記載了明代后期頭巾佩戴的現象,“下至牛醫馬傭之卑賤,唐巾、晉巾、紗帽巾,淺紅深紫之服,炫然搖曳于都市”。
頭巾在明代是與身份聯系在一起的。一些參加科舉考試多年的讀書人,在多年科考失敗之后,最終放棄了入仕希望,稱其為“棄巾”“裂巾”“裂冠”。萬歷年有李姓士人,屢試不第,于是“棄置衣冠”,穿布袍,每日唱歌飲酒,為一閑適散人。崇禎年福建侯官人陳遁,讀書經年,屢不得志,一日興起,將所有的科舉文章及士人衣巾全數焚燒后,入山隱居。
在“棄巾風潮”中,最為有名者為松江名士陳繼儒。陳繼儒與董其昌同為松江俊杰,名聞四海。不想萬歷十四年(1586年),29歲的陳繼儒決意“棄巾”,不再參加科舉考試。松江地方士紳官吏得悉后,再三勸告,亦不能挽回他的心意。
棄巾時,陳繼儒發表《告衣巾呈》:“長笑雞群,永拋蝸角。讀書談道,愿附古人。復命歸根,請從今日。”陳繼儒雖然棄巾,但他好標新立異,每事好制新樣,人輒效法,他創“用兩飄帶束頂”,被時人稱為“眉公巾”。
陳繼儒才華橫溢,精通書畫,不再為科舉考試費神后,反倒逍遙自得,生活得以改善。陳繼儒原本赤貧,靠坐館教書補貼家用,后聲名漸隆,編撰的書熱賣,請他寫作的人絡繹不絕,家境開始殷實起來。又有好友贈送山田,得以構亭筑園。或吟詩作畫,或教子弟讀書,或吟嘯忘返,陳繼儒過起了愜意的隱居生活。
屠隆在青浦當縣令時,對陳繼儒青睞有加,稱他為“神仙中人”,陳繼儒也以弟子禮待屠隆。之后,屠隆在官場遭遇挫折,后半生未再出仕,進入山人行列。屠隆曾以“一衲道人”之名作《別頭巾文》,回顧自己一生為了仕途而艱辛奔波,引來無數苦愁的歷程,決意與“頭巾”告別,從此解脫。不想這《別頭巾文》在《金瓶梅》第56回中被全文引用,引發后世無數猜測,探究這屠隆到底是不是“蘭陵笑笑生”。
晚明出現的這個亦俠亦儒、亦禪亦狂的群體,被稱為“山人”,好游是其顯著特征。山人本意是隱士,但在明代,山人的意思卻有了很大的變化。這些山人,多以詩文而出名,號為山人,卻挾詩卷,攜竿牘,四處游歷,或與權貴交往,或與文人唱和。
“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外之人”。原本只有高士才能稱之為山人,可到了明末,山人開始泛濫,什么人都可以稱山人。甚至“粗知韻事”的女子,只要與一二名士交往后,也敢自稱山人,甚至出現了“女山人”群體。
陳繼儒生平最恨別人稱他為山人,曾云“恥作山人游客態”。山人交結權貴,其角色類似于門客幫閑,名聲不佳。陳繼儒的同時代人多尊稱他為“征君”“征士”,意為被朝廷征聘而不肯受職的隱士。不想到了清代,他竟然被視為山人之首,又被攻擊為“隱奸”。
陳繼儒所交往的,都是當時高官,如首輔徐階、禮部尚書陸樹聲、刑部尚書王世貞等人。對于明末黨爭,他自有看法:“自來國家全副財力悉用于遼東,士大夫全副精神又悉用于門戶。”在他看來,這些黨爭不過是清談誤國而已。對于陷入政治斗爭中的人物,他刻意保持距離,他自言:“不求得福,亦宜遠禍。”陳繼儒云:“要做天下第一奇男子,須要事理圓融。”與李贄、徐渭等明末狂人相比,他多了幾分圓通之氣。
陳繼儒知命樂天,與世無爭,凡事不走極端,只求平穩。他所好的,不過是恬淡山水。陳繼儒對人生有自己的理解,他認為個體“可以經世,可以出世,可以警世,可以垂世,可以玩世。”他選擇了退隱于江湖,當他具備聲望,又有能力之后,他積極入世經世。他參與了松江地方上諸多公益互動,維持地方秩序,就地方弊政向官方提出建議。
崇禎十二年(1639年),陳繼儒已是82歲高齡,他雖無大病,但“自覺軀重膚癢,起臥不時,且精神也不若以往”。雖如此,陳繼儒仍筆耕不輟。到了九月,陳繼儒覺得將告別人世,請人來念誦佛經。不久后,他在家中安詳逝世。陳繼儒去世之后,正是明清鼎革之際,四郊多壘,滿目干戈。所以,有人認為他“來亦得時,去亦得時,第一有福矣”。
(作者系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