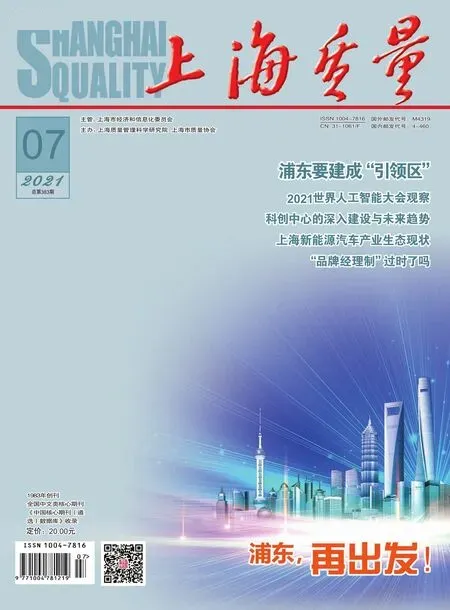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出路在哪
◆ 任聲策 / 文
(作者系上海市產(chǎn)業(yè)創(chuàng)新生態(tài)系統(tǒng)研究中心研究員、同濟(jì)大學(xué)上海國際知識產(chǎn)權(quán)學(xué)院教授,本文已獲愛科創(chuàng)平臺授權(quán))
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是新時期我國堅持創(chuàng)新驅(qū)動發(fā)展、全面塑造發(fā)展新優(yōu)勢的重要路徑之一。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要求,堅持創(chuàng)新在我國現(xiàn)代化建設(shè)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qiáng)作為國家發(fā)展的戰(zhàn)略支撐,強(qiáng)調(diào)要完善科技創(chuàng)新體制機(jī)制,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轉(zhuǎn)移轉(zhuǎn)化成效。
一、當(dāng)前科技成果轉(zhuǎn)化中存在的兩個基本問題
從中央到地方,以及各類創(chuàng)新主體均高度重視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工作。在各省市“十四五”規(guī)劃和2035年遠(yuǎn)景目標(biāo)建議中均進(jìn)一步提出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目標(biāo),如北京市提出“加強(qiáng)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應(yīng)用,打通基礎(chǔ)研究到產(chǎn)業(yè)化綠色通道”;上海市提出“加快構(gòu)建順暢高效的技術(shù)創(chuàng)新和轉(zhuǎn)移轉(zhuǎn)化體系;加速科技成果向現(xiàn)實生產(chǎn)力轉(zhuǎn)化,提高創(chuàng)新鏈整體效能”;廣東省提出“大幅提高科技成果轉(zhuǎn)移轉(zhuǎn)化成效、建設(shè)珠三角國家科技成果轉(zhuǎn)移轉(zhuǎn)化示范區(qū)”;江蘇省提出“完善科技成果高效轉(zhuǎn)移轉(zhuǎn)化機(jī)制,建立省級中試孵化母基金,完善中試保障和運(yùn)行機(jī)制”;浙江省提出“大幅提升科技成果轉(zhuǎn)移轉(zhuǎn)化效率,建設(shè)全球技術(shù)轉(zhuǎn)移樞紐”;等等。

雖然各界對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關(guān)注熱度居高不下,且近年來我國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成效顯著提升,但其中存在兩個頂層問題值得警惕。
一是重“術(shù)”遠(yuǎn)超于重“道”。當(dāng)前在體制機(jī)制改革中針對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討論很多,圍繞權(quán)益、評價、分配、交易渠道等取得了顯著進(jìn)步,但對于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全局性問題討論偏少,過于集中對 “專利”化成果這一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局部問題的討論,導(dǎo)致對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本質(zhì)認(rèn)識仍有很大不足。
二是重“顯示度”遠(yuǎn)超于重“實效度”,重“表”輕“里”,存在過熱與急功近利傾向。雖然重視度持續(xù)高漲有利于加快改革步伐,但是持續(xù)“過熱”也容易產(chǎn)生用力過猛、投入過度、重復(fù)低效、虛假繁榮等問題;急功近利則會導(dǎo)致片面追求顯示度高的成效,而忽視低顯示度、有長遠(yuǎn)效益的工作。例如,過度關(guān)注專利轉(zhuǎn)讓數(shù)量和收入、而對未產(chǎn)生直接收益的知識溢出成效重視不足等。
二、兩個典型的成功案例
第一個成功案例是Cohen-Boyer專利轉(zhuǎn)化案例。Feldman等(2007)介紹了Cohen-Boyer專利“Process for producing biologically functional molecular chimeras”(US4237224,斯坦福大學(xué)1974年申請,1980年授權(quán))技術(shù)轉(zhuǎn)移的成功案例。該專利技術(shù)(rDNA)許可給468個企業(yè),成功轉(zhuǎn)移,快速推進(jìn)了相應(yīng)技術(shù)發(fā)展和運(yùn)用。該專利技術(shù)轉(zhuǎn)移起始于發(fā)明人給企業(yè)提供技術(shù)咨詢服務(wù),斯坦福大學(xué)在Cohen-Boyer技術(shù)許可中的四個目標(biāo)發(fā)揮了重要作用:1)技術(shù)轉(zhuǎn)移要與大學(xué)的公共服務(wù)理念一致;2)促進(jìn)基因工程技術(shù)為滿足公共利益而及時充分的商業(yè)化,并提供適當(dāng)激勵;3)為最小化潛在的生物危害而管理技術(shù);4)為教育和研究提供收入。
第二個成功案例是一個MEMS技術(shù)相關(guān)專利轉(zhuǎn)化案例。Azagra-Caro等(2017)探究了該專利技術(shù)轉(zhuǎn)移典型案例。該微電機(jī)系統(tǒng)專利(MEMS)技術(shù)由美國一大學(xué)于1989年申請,被引用430次。該專利技術(shù)來源于發(fā)明人A的博士論文,發(fā)明人B是其導(dǎo)師,于1986~1990年在高研院開展其研究,受NSF資助。該專利技術(shù)一改之前各代MEMS技術(shù)只能圓形運(yùn)動的情況,使之可以線性運(yùn)動,因而有很多應(yīng)用。技術(shù)誕生時,MEMS相關(guān)產(chǎn)業(yè)處于初步發(fā)展階段。
(1)正式轉(zhuǎn)移渠道:一是該技術(shù)只被正式許可給一家非本地公司MEMS Solution,該公司后續(xù)專利多次引用該專利,但未與該校開展其他合作,對技術(shù)擴(kuò)散的影響較為有限。二是該技術(shù)通過發(fā)明人的咨詢服務(wù)方式為另一家非本地公司Sensor Technologies廣泛所用,該公司是高研院合作伙伴,未收專利許可費(fèi),但該公司后續(xù)與該校合作密切,幫助學(xué)校建立Microlab實驗室、將MEMS制備能力轉(zhuǎn)移到該大學(xué),對該技術(shù)的擴(kuò)散影響很大。三是本地創(chuàng)業(yè)者通過給Microlab實驗室交會員費(fèi)獲得知識轉(zhuǎn)移。1997年該大學(xué)建立Microlab項目,交會員費(fèi)的創(chuàng)業(yè)企業(yè)可以在此開展MEMS相關(guān)制備實驗和試驗研究。很多創(chuàng)業(yè)企業(yè)是該大學(xué)畢業(yè)生創(chuàng)建的,最終本地MEMS產(chǎn)業(yè)因此得以發(fā)展。
(2)非正式轉(zhuǎn)移渠道。一是該研究所畢業(yè)生畢業(yè)后的知識轉(zhuǎn)移,如發(fā)明人A和發(fā)明人D畢業(yè)后到非本地機(jī)構(gòu)從事相關(guān)工作,并進(jìn)一步轉(zhuǎn)移給合作者。二是該大學(xué)的實驗室成為相關(guān)知識交流平臺,為高研院和本地相關(guān)企業(yè)的研發(fā)人員提供交流渠道,促進(jìn)知識轉(zhuǎn)移。
該專利技術(shù)的主要轉(zhuǎn)移渠道和擴(kuò)散路徑非常具有典型性。
三、兩方面重要啟示
以上兩個專利技術(shù)轉(zhuǎn)移轉(zhuǎn)化成功案例給我國高校和科研機(jī)構(gòu)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工作帶來兩個方面的重要啟示。
首先,在理念和思路上,高校與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工作需要開拓理念和視野、秉持長期導(dǎo)向、不忘初心。一是要形成知識轉(zhuǎn)移的綜合觀念。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技術(shù)成果轉(zhuǎn)化理念需要拓寬、拔高,應(yīng)該從知識轉(zhuǎn)移的理念高度統(tǒng)籌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工作,不應(yīng)局限于專利技術(shù)轉(zhuǎn)讓和“四技”服務(wù)。以“環(huán)同濟(jì)”知識經(jīng)濟(jì)圈為例,其發(fā)展更多的是同濟(jì)大學(xué)知識轉(zhuǎn)移的綜合結(jié)果,而不僅僅是專利技術(shù)轉(zhuǎn)讓和“四技”服務(wù)的貢獻(xiàn)。二是要注重長期導(dǎo)向。在科技成果轉(zhuǎn)化中應(yīng)更注重長期導(dǎo)向,樹立“久久為功”思想,關(guān)注知識轉(zhuǎn)移的長期綜合效果,不過度被一朝一夕的所謂“有顯示度”指標(biāo)所牽絆。三是不忘初心。高校、科研院所在科技成果轉(zhuǎn)化中需要以高校、科研院所的核心使命為根本,人才培養(yǎng)、知識創(chuàng)造、社會服務(wù)等均為推動社會進(jìn)步的“公益”事業(yè),因而不應(yīng)過度追求“創(chuàng)收”。如上述兩個成功案例所示,在斯坦福Cohen-Boyer關(guān)于rDNA專利技術(shù)轉(zhuǎn)讓中,如果短期內(nèi)過度追求收益,很可能限制該技術(shù)擴(kuò)散范圍和速度,影響技術(shù)的社會價值發(fā)揮和(或)產(chǎn)生技術(shù)危害。在MEMS專利技術(shù)轉(zhuǎn)讓中,如果過度強(qiáng)調(diào)收益,可能導(dǎo)致與Sensor Technologies公司的合作受沖擊,從而影響該公司對高校的知識反向溢出,可能導(dǎo)致該大學(xué)本地MEMS相關(guān)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及產(chǎn)業(yè)集群興起出現(xiàn)生存危機(jī)。
其次,在路徑上,科技成果轉(zhuǎn)化要堅持正式和非正式渠道并重,促進(jìn)綜合效果趨向最佳。一是從正式轉(zhuǎn)移渠道看,專利許可只是科技成果轉(zhuǎn)化中最顯性的部分,容易被過度重視,但其總體貢獻(xiàn)并非想象的那么大,而技術(shù)開發(fā)、咨詢等服務(wù)活動在科技成果轉(zhuǎn)化中扮演的角色更需要高度重視。在上述兩個成功案例中技術(shù)咨詢活動均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二是從非正式渠道看,知識溢出才是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核心驅(qū)動力。校企合作實驗室是重要的知識溢出平臺,其知識溢出是雙向的,不僅高校向企業(yè)以正式或非正式途徑產(chǎn)生知識溢出,企業(yè)也可以向?qū)嶒炇乙绯鲋R,促進(jìn)實驗室能力提升。在校企合作實驗室的知識溢出中,產(chǎn)品化能力和開放性是校企合作實驗室促進(jìn)知識溢出的兩個關(guān)鍵。擁有產(chǎn)品化能力的實驗室,擁有產(chǎn)品試制平臺,能實現(xiàn)創(chuàng)新鏈和產(chǎn)業(yè)鏈的無縫銜接,有助于基于創(chuàng)新技術(shù)的創(chuàng)意得到快速驗證;開放性則拓寬了實驗室知識溢出的范圍。
因此,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工作是一項綜合性的知識轉(zhuǎn)移工作,需要以知識轉(zhuǎn)移理念為指導(dǎo),其成效不僅體現(xiàn)在專利成果許可轉(zhuǎn)讓,也體現(xiàn)在技術(shù)開發(fā)和咨詢服務(wù)之中,更體現(xiàn)在廣泛存在的知識溢出之中。當(dāng)前,需要重塑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綜合評價體系,不宜以偏概全僅用專利成果轉(zhuǎn)讓數(shù)量和(或)金額來評判;研究機(jī)構(gòu)也應(yīng)樹立“久久為功”的長期導(dǎo)向,既要抓專利轉(zhuǎn)讓和技術(shù)咨詢,也要抓知識轉(zhuǎn)移和溢出。
當(dāng)前,提升我國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成效,既要重“道”又要重“術(shù)”,關(guān)鍵是構(gòu)建高質(zhì)量知識供給和高質(zhì)量知識需求的有效匹配體系。本文所述兩個典型成功案例,均是基礎(chǔ)性和突破性技術(shù)創(chuàng)新,雖然其成功經(jīng)驗產(chǎn)生于特定技術(shù)領(lǐng)域、技術(shù)生命周期和制度背景等,但對我國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工作仍具有相當(dāng)大的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