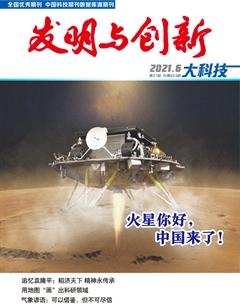新型職業傷害誰來管
本刊綜合
許多人知道塵肺是職業病,那心理疾病是不是?肌肉骨骼疾病是不是?因為工作壓力帶來的亞健康是不是?
4月25日至5月1日是我國第19個《職業病防治法》宣傳周,新職業、新業態下不斷“刷新”的新型職業傷害引發人們的關注。這些長期的、慢性的、隱蔽的傷害如何納入法律法規?新業態下如何創造更良好的工作環境?專家呼吁,應盡早劃出紅線,嚴格執法,維護好員工權益,同時政府、企業和個人都要增強認知,對新型職業病早發現、早認識、早防范。
“90后”張瑞(化名)曾在某互聯網頭部公司擔任內容審核員,盡管薪水可觀,但2020年他還是選擇了離職。
“太累了。早上8 點多出門,晚上10點多到家,一整天的工作都是盯電腦屏幕,干眼癥、頸椎病、腰椎痛、腱鞘炎都找上了門。”張瑞說,遇到加班多的時候,整個生物鐘都亂套了,即使下班回家也睡不著,失眠久了還會陷入抑郁狀態。
在互聯網等行業,像張瑞這樣的情況并不鮮見。在某職場社交平臺頻道,每天更新的大量動態中不乏互聯網“大廠”員工。“25歲,工作一年,某大廠每天加班4小時,體檢后有:過敏性鼻炎、前列腺鈣化、甲狀腺良性腫瘤。”這條動態下的熱評回復是:“你這個在互聯網行業里算健康身體。”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行業不斷發展,各種新業態、新職業不斷涌現,新的職業和勞動方式帶來的新型職業傷害日益受到關注。多位受訪者談到,互聯網等行業從業人員長期從事高強度工作,不僅頸椎病、腰椎病、視力下降、內分泌疾病等新型職業病非常普遍,失眠、焦慮、抑郁等心理疾病也日益增多。
《2019年互聯網產業人才發展報告》顯示,在對自身健康狀況的評判上,互聯網人的樂觀程度低于其他行業。在對疾病的擔憂上,71.7%的互聯網人擔憂頸椎、腰椎問題,53.33%的互聯網人擔心內分泌疾病,40.44%的互聯網人擔心脫發。
與傳統職業病直接、明顯、劇烈的特點相比,新型職業病給勞動者帶來的困擾往往是長期的、慢性的、隱蔽的。
“隨著我國經濟轉型升級,新技術、新材料、新工藝廣泛應用,新的職業、工種和勞動方式不斷產生,職業病危害因素更為多樣、復雜,傳統的職業病危害尚未得到根本控制,社會心理因素和不良工效學因素所致精神疾患和肌肉骨骼損傷等工作相關疾病問題日益突出,職業健康工作面臨多重壓力。”國家衛生健康委職業健康司司長吳宗之說。
我國《職業病防治法》明確,對職業病的認定必須具備4個條件:患病主體必須是企業、事業單位或個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必須是在從事職業活動的過程中產生的;必須是因接觸粉塵、放射性物質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質等職業病危害因素引起的;必須是國家公布的《職業病分類和目錄》所列的職業病。
但職業病侵犯的人群和行業,早已不再是過去普遍認為的工業人群和工業產業,職業病也不只跟那些接觸粉塵、放射性物質以及有毒物質的人有關,而是向科技行業、現代服務業等領域蔓延。
一位來自四川的工會工作人員表示,對于不斷出現的新職業病,大家總是有一個逐步認識的過程。“就好比以前普遍認為塵肺主要在煤礦等行業出現,后來整理工會接到的塵肺維權投訴案例,卻發現不少來自裝修、瓷磚切割等行業,但起初很多職工根本沒意識到這一點。”
“近年來職業病病種出現新變化,尤其是以往未曾出現的職業性皮膚病、職業性腫瘤、職業性傳染病等已有診斷病例出現。”安徽省第二人民醫院副院長陳葆春表示。
據了解,近五年來,安徽省出現了苯所致白血病,石棉所致肺癌、間皮瘤等診斷病例。早年間,江蘇的醫生們也曾發現有的工人出現不明原因的肝損傷或肺部病癥,后來確診是“銦中毒”,當時醫學界對這一情況還知之甚少,社會各界也并不了解職業與這些病癥的關聯。
一方面,工業化進程的加快,一些新材料、新工藝的應用,使得新型有機溶劑、稀有元素使用增多,導致新型職業病的出現;另一方面隨著科技高速發展,新職業不斷出現,職工安全與健康情況比以往更加復雜。
一面是新型職業傷害日益凸顯,一面是相關傷害及相應保障尚未納入現有法規。
原國家衛計委等部門曾頒布《職業病分類和目錄》,其中羅列了10類132種職業病,包括塵肺、職業性化學中毒、職業性腫瘤等,同樣是以傳統制造業的職業健康風險為主,當下互聯網等行業出現的新型職業傷害相關疾病并未被列入其中。
有專家認為,新型職業傷害的特點也讓法律和政策難以應對。比如過去可以制定《工傷保險條例》《職業病防治法》來尋求解決,但現在很難找到制度性的解決方式,因為很難明確定義“工作”,也很難確定傷害是不是工作帶來的。
在法規、制度不夠完善的同時,互聯網企業過度追求績效無疑是新型職業傷害叢生的重要原因。一位互聯網從業者說,大廠習慣把項目時間壓縮得非常緊。此外,與國外互聯網公司以半年甚至一年為周期考核不同,國內企業會將考核周期縮短至一兩個月,這往往讓員工的工作量超出日常工作可承受的范圍。
此外,與過去企業監管職工需要耗費較大成本不同,互聯網經濟下,通過平臺軟件、攝像頭、傳感器等技術手段,企業可便捷了解職工是不是在工作、工作狀態如何,這也容易給人帶來過去無法想象的心理壓力和焦慮。
雖然許多勞動者受到新型職業傷害的困擾,但因這類疾病不屬于法定職業病范疇,勞動者維權無門,企業及用人單位對這類新型職業病選擇性漠視,更談不上防護及賠償。
全國政協委員李國華表示,從2019年到2021年,“996”的問題不僅沒有得到緩解,反而愈演愈烈。“當前我國‘996問題處于企業失控、監管失序、工會失靈的狀態,鮮少見到‘996企業得到處罰,勞動監察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勞動者維權困難。”
從現有《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看,企業違法延長勞動者工作時間的,僅會被“給予警告”“責令限期改正”,并可以按受侵害的勞動者每人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標準處以罰款。
山西大學法學院教授、山西省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會長彭云業建議,應及時修訂職業病防治法等勞動保護方面的相關法律法規,將新出現的職業傷害及相關保障納入其中。同時,相關勞動法規中關于勞動部門履責的規定應當進一步明確,尤其是對不作為的責任人要加大問責力度。
企業工會也應成為員工維權的重要保障。專家表示,工會組織推動集體協商機制,確保企業員工與企業之間有定期圍繞包括加班在內的對等博弈,是“996”等損害勞動者權益現象的解決之道,也是不少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值得借鑒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