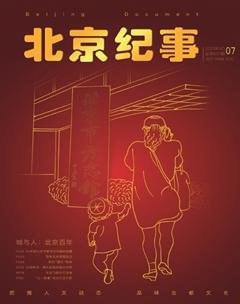翟玉良:做好一盞燈
張知依

“月色燈山滿帝都,香車寶蓋隘通衢。身閑不睹中興盛,羞逐鄉人賽紫姑。”這是唐代詩人李商隱的《觀燈樂行》。月光如水,花燈如山,裝飾華麗的香艷的馬車堵塞了寬敞大道。
詩人記錄的盛景里,燈是主角。
而今天要講的燈,曾是古代的奢侈品——宮燈。在宮燈的序列里,北京宮燈樣式紛繁:掛燈、落地燈、壁燈、戳燈,樣樣好看;造型各異的北京宮燈各具特色,盆兒形,六方形、雙柱形,細說得有幾百種。
精致的設計、獨具匠心的工藝、幾代人的傳承,凝聚著傳統文化燦爛的美。
北京宮燈的傳承故事中,有歷史的重量與匠人的品格。
今天,就請聽文盛齋的第四代手藝人翟玉良為我們細細說。
一見鐘情
1971年,翟玉良中學畢業,由學校分配進入北京市美術紅燈廠,開啟了他的職業生涯。“那會兒,大家的想法很簡單,分配什么就干什么,任勞任怨。”老翟說,和宮燈打交道,一干就是一輩子。
北京市美術紅燈廠的前身,是前門外廊房頭條的文盛齋。歷史上,北京有兩個文盛齋,一個是原址在前門外廊房頭條的文盛齋,大約開業于清朝嘉慶年間,以經營各類彩燈而著名,后來遷到東琉璃廠。另一個是文盛齋琴行,清朝咸豐年間開業的樂器琴行,位于廠甸小沙土園北口西側,后來遷到安定門大街。
今天咱們說的是做宮燈的文盛齋。宮燈曾是宮廷專屬的器具,逢年節也賞賜給王公大臣。清朝時,宮燈由內務府造辦處管理,需要時召工匠入宮。文盛齋的創始人韓子興先生就曾經配了腰牌進宮為慈禧太后做宮燈。而工匠們并不專屬宮廷,于是宮燈就在民間流傳開。“聽我師傅說,當年廊房頭條的燈籠鋪里,文盛齋是做得最好的。”
經過發展,文盛齋改建為宮燈壁畫廠,北京解放后,經過公私合營,宮燈壁畫廠改成北京市美術紅燈廠。
“我們廠那會兒有幾個產品,木制宮燈、大紅燈籠,還有一種就是各種造型的燈彩;廠里的塑料車間和國畫車間也很厲害。當時很多美院畢業的學生到我們廠來,因為他們在美院學得很扎實,所以組成了一個車間,這個車間最多的時候有將近上百人,專門作畫。”
回憶起最初的進廠學習,翟玉良說,自己被分配為宮燈制作學徒,他幾乎是“一見鐘情”地喜歡上了宮燈。以硬木為框架的六方或四方宮燈,可拆卸和折疊,在燈的每個角上都綴有絲穗,燈框架之間嵌以玻璃或紗絹,玻璃內畫有彩色漆畫。如此精美的作品,讓翟玉良格外喜歡。“我最喜歡的還是六方宮燈。因為六方宮燈是傳統的宮燈,非常耐看,什么場合都適合,包括故宮等莊重的場合都掛這種燈。”
學藝
“別看過去的手藝人可能表達得沒那么好,但手上的活特別精。”
回想初進廠時,翟玉良見到的大制作場面,至今難忘。“有300多號工人,做宮燈也像現在的流水線作業似的,機器組負責下料開料,成活組負責做成產品,壁畫組負責畫片,流蘇組做燈穗,噴漆組負責刷漆,大家各自負責其中的一部分。”
翟玉良還記得,師傅們個個有絕技。“宮燈上有五花八門各種工藝,每個師傅都至少擅長一樣,比如說有的師傅特別擅長鎪活,有的擅長掛料,有的擅長拉料,可以說師傅們各個有絕技。”精通技藝需要時間,憶往昔,翟玉良是在日復一日中,才掌握了一整套工序。“單是木工活我就學了三年。”翟玉良說。
翟玉良進廠的年代,正是恢復生產的年代,他和師兄弟們跟隨郭漢、徐文起、孫守亮、劉洪福、袁振經、李春等身懷絕技的老師傅們如饑似渴地學習宮燈技藝,師傅們也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手藝傾力相傳。“所有技藝都在老藝人的腦子里。生產恢復起來特別快。”
別看過去的手藝人可能表達得沒那么好,但手上的活特別精。
世界上沒有一門手藝可以逃過枯燥的練習。“進來以后就直接跟著師傅學,從基本功開始,然后就練去、干去。”宮燈制作的基本功之一是“鎪”—— 在木料上,用鎪弓子鎪出窟窿。制作出精美的圖案,也都倚仗這門技術。“鎪活挺枯燥,也挺累。幾個月,就光干這個。”在這樣勤學苦練中,翟玉良體會到是什么成就了宮燈的美。
“那會兒我們一個組有20多人,一個車間好幾個組。我們鎪起活兒來,站一排,吱吱啦啦就跟奏樂似的,特別震撼。”翟玉良說,技藝練習之中也有趣事,“那時候大家都年輕好勝,要比著看誰的技藝好。我們4個師兄弟較上勁了,把手表往桌子上一放,4個人一起鎪牙子,看誰鎪得最快。一小時的時間內,我和師兄都鎪了上百個窟窿。”
宮燈之美
“宮燈不用一根釘,全部是榫卯結構,跟咱們中華傳統建筑文化是完全吻合的。”
宮燈是在方寸之間創造出的美。從木材變成可以組裝的零部件,需要經歷鎪、雕、刻、鏤、燙等工序,從木工備料、開料,到雕刻、拼接、粘合,都需要師傅們的良工巧做。而后還要拋光、打蠟、上漆,再貼絹或上玻璃,最后插上龍頭、掛上流蘇。工序一道道,都有大門道。

老翟拿起身旁的宮燈:“就拿這盞最普通的六方宮燈來說,這是由一塊一塊做好的木頭拼接到一起的。你猜,這一盞燈要多少塊木頭?”
小巧的宮燈,不能被小瞧。“這一盞燈要120多塊木頭組在一起。”老翟揭曉答案時,在場的人心里著實吃了一驚。“每一個部件、每一根料都需要精心制作。往小了說,一個部件用一道工序就是100多道工序,而且每一根料它要很多道工序。”
懂得中國傳統營造之道的人都明白,宮燈與傳統建筑文化緊密相連。“不管是家里的屋子,還是故宮的房子,只要蓋房子都得有梁、得有柱子、有窗戶,咱這宮燈也是一樣。”翟玉良指著燈扇:“你看,上面這橫扇叫梁,架子上這塊我們叫柱子,彩畫的地方是窗戶。所以宮燈跟咱們中國傳統的建筑、傳統家具都是融為一體的。”
六方宮燈由六片燈扇巧妙拼接而成,傳統手藝不運用額外的粘合劑或者鐵釘這樣的外物,而是用榫卯連接,在木材本身上做文章。老翟利索地從上面取下一扇。
宮燈不用一根釘,全部是榫卯結構,跟咱們中華傳統建筑文化是完全吻合的。
翟玉良講到,“像是故宮里頭那些建筑上的斗拱、百姓家里的紅木家具,都是榫卯互相咬著,有多少級的地震晃悠都不會散架”。平和樸素的榫卯結構,暗含智慧,成就了中國含蓄內斂的審美觀。而在宮燈上完成榫卯的制作,對雕刻尺寸有精準要求。
框架完成后,還有裝飾性的雕花。按照慣例是鏤空雕刻,凸出燈體的部分稱為“花牙”。花牙樣式,基礎的有十來種,臨時變化無窮數,雕刻分布的位置也很靈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鎪弓子、手工刨是木作師傅必備的工具。翟玉良有幾件陪伴了他幾十年的趁手工具,都是自己制作的,“鎪弓子就是現在叫曲線鋸,關鍵是一根鋼絲鋸條。我們那會兒做鎪弓子都是自己做,不是外頭去買現成的。”
親手制作工具,是工藝智慧的應用:經年累月的工作習慣后,工匠知道自己的工具怎么和手里的活完美匹配,工具的制作也是就地取材。“我們車間有做大紅紗燈的嘛!就用做大紅燈籠的竹板子,找最厚最好的竹板一點一點地窩成弓形,用鋼絲給它纏上,繃上勁。”木匠有“百藝之首”的美譽。這份就地取材與恰到好處,是木作最核心的分寸。
中國名片
“當時時間緊任務重,幾位藝人整整三天三夜沒離開城樓,離開國大典只差一天的時間,大紅燈籠終于做好了。”
談起在工廠時的經歷,最讓翟玉良印象深刻的作品,不得不提開國大典由前輩匠人制作的天安門城樓上的大紅燈籠。
“(扎燈老藝人)之前沒做過那么大的燈籠,挺犯難的,但這是任務,大家伙兒就想盡一切辦法要把燈籠做好。”翟玉良說,當時時間緊任務重,幾位藝人整整三天三夜沒離開城樓,離開國大典只差一天的時間,大紅燈籠終于做好了。每個燈籠高3米、直徑5米、重80公斤,3個戰士手拉手才能環抱,堪稱有史以來最大的燈籠。由毛竹、不褪色的紅士林布和松木制作的燈籠,上下部貼有金黃色的云朵,底部配有黃色流蘇,十分莊重、大方、美觀,也成為共和國的集體記憶。
前輩講述過去的故事,激勵后輩做出屬于自己的作品。積累大量經驗后,老翟的宮燈作品出現在重要的外賓接待場所。講起給北京飯店貴賓樓設計宮燈的故事,翟玉良歷歷在目,“當時對方把用意跟設計師一塊兒探討,我設計出了一個大概其的樣子,對方看完以后非常滿意,就照著樣子去做。”翟玉良說,當時給十層的總統套房每間房里配了一盞,還給大廳配了一盞垂花子母燈。
子母燈是按照吊燈樣式制作的宮燈,有不同的樣式,經過適應性的改良,兼具傳統氣質與現代氣息。工匠們給子母燈設計了好聽的名字:一圈小的圍著大的,叫做“云盒”;母燈中央逐層下沉的,叫“垂花”;嵌了金絲的叫做“金龍合璽”,別有雅韻。
“后來我又做銷售,接觸了好多國外的客戶。”翟玉良說,把北京宮燈訂單遠銷海外,成為他很驕傲的時刻:“咱們中國人在國外開餐館的,會照著咱們中國的風俗習慣味道去裝飾店面。我接觸有幾個華人客戶,他們每年回到北京以后,都到我這兒買一批宮燈,邊做裝飾邊出售。宮燈成為了一塊招牌。這些客戶把宮燈放到中國餐館門口,外國人一看就是中國餐館。有的外國人見店主的燈漂亮就買走了。”
近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提高,加之傳統文化受重視,也有越來越多的內地訂單。不止一個客戶找到翟玉良,讓他制作獨一無二的宮燈。“經常有客戶說,想要做一盞別人沒有的,我從沒做過的宮燈。現在大家講個性,要獨樹一幟的特色。”
得益于傳統宮燈手藝的智慧,以及勤學苦練出的本事,在翟玉良手上,個性化的宮燈不難實現。“只要你掌握了宮燈這門手藝,你可以隨心所欲地去設計、去制作。很可能我猛然看見一個東西,馬上來靈感,就可以制作出來。”在老翟看來,定制化需求也是傳統技藝提高的過程:“我也特別喜歡這么做。在整體的設計素材里,別離開工作的本色就行。”
老翟設計了很多的異形燈,荷包燈、縮口燈、亭子燈……各種造型的都有。“燈可以是千變萬化的,只要這些工藝你掌握了,隨便去變化。根據這個房間的大小,根據個人的喜好,根據房間整個的裝飾環境去設計。”這份自在的背后,大概是遵從了“從心所欲不逾矩”。
盡管已經退休,翟玉良也閑不住。近年來,北京聯合大學“北京瀕危手工藝傳承人才培養”項目請翟玉良傳授宮燈制作技藝。學員是從社會上通過考試選定、有一定基礎的愛好者,通過3個月的系統學習,畢業時每個人做了一盞宮燈,還集體制作了一個直徑80厘米的走馬燈。翟玉良對學員的水平挺滿意,“達到了入門水平,時間長了積累多了,他們的手藝會越來越好”。
也有一些中小學把老翟請去給小朋友們講課。面對小朋友,翟玉良設計了難度適合的課程:給孩子們講講宮燈的歷史、制作工藝,最后做一些比較簡單的燈飾,讓大家體驗一下。課程最開心的時刻,是學生們一人拿著一盞做完的燈飾回家。“孩子和家長都特別高興,因為學生在學校體驗到咱們的傳統工藝和非遺文化。”說起這些,翟玉良也開心極了。
他用一輩子的職業生涯做好一盞燈,也用傳統手藝點亮了孩子心中傳統文化的那盞燈。“咱們讓孩子體驗制作燈飾,不見得非讓人家以后傳承這個。讓孩子們接觸接觸中國的傳統文化,知道有這么回事,等他走向社會的時候,能從傳統文化里吸取力量,再發揮自己的創造力,這是多好的事兒啊。”
匠心小傳
70年代進入北京市美術紅燈廠學習宮燈制作,翟玉良一干就是一輩子。和師傅們學習技藝,在方寸之間展現精美木作。一盞宮燈,一百二十塊木頭,一千多道工序。翟玉良以匠心和技藝制作,用榫卯咬合住木制宮燈的聯結處,也讓我們與歷史上燦爛的燈彩文化相連。他用一輩子的職業生涯做好一盞燈,也用傳統手藝點亮了孩子心中傳統文化的那盞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