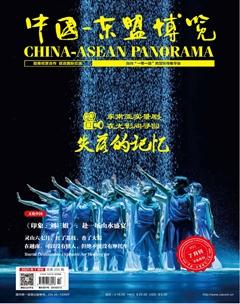千年坭興,淬火的非遺
梁舒欣



在欽州,隨意的拐角,便能偶遇一家典雅別致的坭興陶小店,步入其間,店面不大,陶器整齊擺放,琳瑯滿目,在微黃的燈光下熠熠生輝。小店深處,竟有一隔間,半成品泥坯堆積如山,約摸十八九歲模樣的少年在臺燈微弱的燈光下,以刀代筆,一筆一劃,一勾一勒,細細雕刻手中的陶坯。飛鳥、白蓮、水波栩栩如生,似乎要在指尖一躍而出,沉寂多時的陶坯被賦予靈動的生命,仿佛在一分一秒雕琢的時間里蘇醒。
從泥路走來的
千年坭興陶
在陶花島坭興陶館,我們見到了國家級非遺傳承人李人帡先生。在滿是坭興陶的茶室里,他邊晃著手上的藍白色醫院腕帶,邊向我們致歉,因身體緣故不得已來遲,途中還接了幾個國際長途電話。75歲高齡,滿身榮譽,本可以功成身退,安享晚年,卻依舊為坭興陶產業的傳承和發展奔波,鞠躬盡瘁。
“1920年的時候,在我們欽州本地,發現了一塊碑,寧道務陶碑,大約高四尺,旁邊還附紅陶壺一個,碑上刻有唐開元二十年字樣,在唐初便能制作出如此精良的陶器,可推測出坭興陶在欽州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甚至更久。”以柴火燒制的坭興陶茶盞,清茶被一杯一杯地續上,氤氳茶香里,李人帡為我們講述千年坭興陶的前世今生。
在欽州,有一條煙斗巷,年久失修,老舊破敗。我們詢問了夾雜著欽州白話、號稱精通欽州大街小巷的出租車司機,卻也未能詳知煙斗巷的確切位置。而這條被人遺忘的老街巷卻承載了一段輝煌厚重的過往,在欽州千余年坭興陶的發展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清朝咸豐年間,近代坭興陶奠基人胡老六無意間發現欽江東西岸的泥土相結合,制造的煙斗質感細膩,光潔如玉,精良程度堪比江蘇宜興紫砂陶,同行紛紛效仿,聚居于欽州城南魚寮橫街,建置坭興陶生產作坊,開設銷售商店,自此形成了坭興陶一條街,這便是久負盛名的煙斗巷。如今,于煙斗巷匆匆走過的行人或許不知道,腳下揚起的塵,或許是百年前制作坭興陶時留下的泥。
“那時候苦啊!兩個擔子滿滿當當的陶器,小心翼翼用肩膀挑,生怕磕著碰著,磕壞了,那可是數十日的心血啊。要走十幾公里的泥路,也不敢怠慢,到當時唯一能燒制坭興陶的古龍窯進行柴燒。”在泥路間蹚出一條坭興路,放在李人帡身上一點都不為過。20世紀90年代末,由于國家政策的變化,坭興陶產業由國營變為民營,欽州坭興陶廠一度瀕臨破產,發不出工資來,工人紛紛落廣打工。彼時的李人帡已是坭興陶大師級別,滿身榮譽,本可以高薪跳槽,他卻選擇了堅守復興坭興陶的陣地,7個月里,沒有一分一毫的收入,他白日在廠里拉坯、雕刻、創作,傍晚耕地種菜貼補家用,日復一日。
談及那段艱辛的過往,李人帡說:“我身上是有責任的,如果當時我離開了,坭興陶真的可能就后繼無人了,既然站在那個高度就應該擔起更大的責任。” 2008年6月,欽州坭興陶燒制技藝獲國務院公布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如今,坭興陶產業更是已納入欽州的國民經濟體系,坭興陶產業蓬勃發展,坭興陶從業者也從數十人上升到數萬人,大大小小坭興陶工廠、工作室林立。談及坭興陶傳承和發展問題,李人帡認為,傳承不僅僅是幾個手藝人窩在室內拉坯創作,而是將坭興陶產業做大做強,融入國民經濟體系,增加就業崗位、拉動經濟,坭興陶才真正得以在民間傳承,生生不息。
一筆一劃, 一勾一勒
皆是壯鄉情
“坭興陶有六法,摟、揮、轆、挑、窯、光,這‘挑說的就是坭興陶的雕刻技藝。你看,這茶具上的銅鼓紋采用的是平刻,凸起的飛禽則是淺浮雕法。” 李人帡拿起茶具給我們介紹坭興陶刻之法,只見壺身刻有三只鷺鳥,環繞著繡球飛翔,壺底繞著一圈壯錦幾何圖紋,墨綠色的壺身,朱紅色的雕刻圖紋點綴其間,別有一番古樸典雅的韻味。
坭興陶的設計結合現代化的審美,同時也融入了廣西少數民族文化元素的表達,以陶為媒,以刀為筆,立足本土,展現廣西獨有的歷史文化底蘊和民族風情。在裝飾設計上,多以陶器造型和陶器雕刻等方式展現。《高鼓花樽》外型似鼓,在造型上便是以廣西古代銅鼓、長鼓的高鼓花桶為原型,花樽上則雕刻壯民競舟、野鹿飛奔的場景以及花山巖畫中的人像圖騰,壯族先民的風姿與古老的銅鼓文化躍然陶器之上。
刀尖上的壯鄉情,坭興陶創作者大多是土生土長的廣西人,他們植根于廣西民族文化的土壤,將繡球、銅鼓、蘆笙、風雨橋這些民族元素融入到陶器整體造型設計中,展列于柜臺之上的白海豚茶寵、荔枝茶具、銅鼓花瓶以及器皿上經過精細雕琢的壯族圖案、花山巖畫圖案、青蛙圖騰等無不展示創作者微妙細膩的故土情思。
淬火涅槃,
窯變千彩
到達缸瓦村坭興陶古龍窯時已是晌午,7月的欽州,烈日炎炎,燒陶的工人打著赤膊奮力地搬運堆積如山的瓦缸,放置在窯前窯后的空地上,靜靜等待著蛻變。
窯內,夏日的暑氣加上烈火的高溫,即使大汗淋漓,熱氣難耐,燒制工人仍小心謹慎,視如珍寶,將數千件坯品裝入龍窯,再以磚泥封閉窯眼、窯洞,留窯頭火口用以添薪燒制。數千件坯品整齊劃一,擺放在古龍窯內,于熊熊烈火、千度高溫之下,淬火涅槃,渾然成器,靜靜等待著一場精彩絕倫的窯變。
“這是天斑,最上層的深色是墨綠,墨綠下面為古銅,最底層的是紫紅,紫紅是欽州紫紅泥的原色,只有欽州坭興陶才有如此神奇的窯變。”燒窯工搬出一樽色彩斑斕的坭興陶瓶對我們說道。墨綠、鐵青、古銅、紫紅各色錯落交織,呈漸變色澤,星星點點的天斑點綴其間,瓶身略有細紋,手撫有粗糙顆粒感,乃經古龍窯柴火燒制而成。
《景德鎮陶錄》曾記載過陶器窯變現象:“窯變之器有三:二為天工,一為人巧。其由天工者,火性幻化,天然而成,其由人巧者,則工故以釉作幻色物態,直名之曰窯變,殊數見不鮮耳。”欽州坭興陶無彩無釉,卻能于烈火燒制間形成獨特的窯變,堪稱“中國一絕”。
絕無僅有、獨此一家的窯變著實要歸功于欽江兩岸神奇的陶土。欽江以東,有白泥,質軟,綿密細膩,欽江以西,有紫紅泥,為硬質黏土,遂有“東泥軟為肉,西泥硬為骨”之說。窯變,火性幻化,天然而成,其色澤變化,得之偶然,不循章法,也無定格,同批燒制,顏色也不盡相同,全憑天意,因此便衍生了一句欽州本地俗語,“火中求寶,難得一件,一件在手,絕無類同。”雖說窯變幾乎靠天意,但是窯火把控的恰當與否也會影響窯變的色澤,古老的柴窯燒窯法極難把控溫度的變化,成品率低,坯體易落灰,燒制的陶器表面略顯粗糙。如今的燒窯人逐漸摒棄柴窯,多以電窯、煤窯代替,其燒制成的坭興陶色彩渾然天成,細膩如玉,喜愛者甚廣。
夜幕將至,夕陽將落,我們踏上返程的火車,滿目皆陶的千年陶都于身后漸行漸遠,熾烈如火的天際像極了古龍窯內升起的柴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