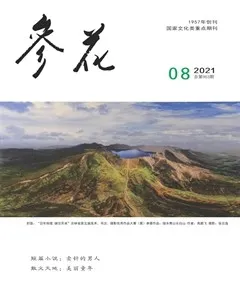先秦喪服禮儀文化淺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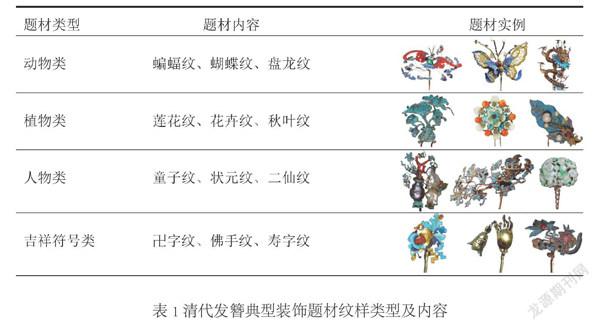
摘要:喪服制度起于先秦時期,喪服作為禮儀服飾中比較特殊且至關重要的存在,是研究中國古代服飾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喪服制度是我國特有的一種文化現象,本文將從喪服這一特殊服飾展開中華服飾體系與禮儀文化的探索。
關鍵詞:喪服制度 禮儀服飾 禮法
服飾文化貫穿歷朝歷代,其不僅作為文化載體,更是體現社會制度和社會文化的符號標志。先秦是文化禮制的初始時期,禮儀服飾依據禮儀活動相應而生。古人認為因疏忽而錯穿禮儀服飾可能會得罪天地神明繼而給國家帶來災害,他們認為天地之理不可變,也就是說時空的規律不能被破壞。由此可見,古人的天命觀和哲學觀也在服飾禮儀中相應體現。服飾制度是服飾禮儀文化最清晰的映現,例如,祭祀時所著的祭服,婚嫁時所著的吉服,從戎時著軍服,服喪時著兇服等等,這些相應產生并伴隨著禮儀所匹配的服飾也是禮儀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禮儀規格不同,則參與者所著的服飾大相徑庭,但無論何種規格都需要遵循禮儀的綱常法紀,正是因為禮法規范著著裝行為。
服飾是禮儀的體現方式之一,服飾制度與禮儀規格相互對應,可以看出服飾作為符號形態映現了禮儀的規格與制度。喪服制度始于先秦時期并貫穿整個中國古代社會,它產生于儒家“六禮”之一的“喪禮”,是“喪禮”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儒家傳統文化的重要標志。《儀禮·喪服》篇是最早記載關于喪服制度的典籍,它將繁縟復雜的喪服制度高度概括并加以整合,從內容可見當時社會中的喪禮服飾與逝者血緣親疏關系遠近、尊卑地位高低各有明晰的所著喪服形制規定。
一、由喪服可見綱常倫理中的禮法有序
“喪”是棄忘之意,人死稱之為喪。一般喪服形制可分為五種,通常稱之為“五服”,由上至下的排序包括斬衰、齊衰、大功、小功和緦麻。這種五服制度在宗親關系里可以按照“同心圓”結構分析,同心圓中心為核心以水波紋形狀散開,離圓心越近者所著喪服等級越高,遠之等級越低,斬衰為最重,緦麻為最輕。
喪服制度中的倫理關系是存在于社會秩序之中的。從喪服制度所見的倫理關系是與儒家思想所提及的“愛有差等”觀念相吻合,其在喪服制度中的“親親”關系中有明確體現,“親親”原則是倡導宗法中提出的“血親至上”與“孝悌”思想,這也出于儒家思想對于血緣親情的重視,后成為中國法律傳統中的原則之一。在宗族社會的親疏關系中,用以喪服形制繁簡輕重來劃分關系遠近,如上文中提及的“同心圓水波紋”親屬結構關系,在這個親屬結構關系網絡中最為親近的關系是父子關系,以父為首,即三綱五常中的“父為子綱”,是喪服制度中“親親”關系的最高等級。孔子曾說:“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孩子在父母懷抱中成長三年,所以父母去世,孩子也為他們服三年之喪,也是普天下之通行的喪禮,這種最為隆重的禮儀歷代帝王也需遵循。斬衰三年體現了喪服制度中的以“禮”報恩,三年之喪其目的是報答父母恩情,這是充斥著人情的禮儀文化。
可見,喪服中最重要的禮儀規格就是斬衰裳,遵循著上衣下裳的傳統服飾形制配以麻做的首绖與腰绖,粗糙的喪仗和用粗麻糾合而成的絞帶,喪冠用麻繩做纓帶,鞋用菅草織成。斬是讓衣服兩側的斷口露著不縫齊,這種服飾可直觀感受到服喪者對于逝者的哀痛之情,為父母服斬衰是家族情感中最上層情感關系的體現。以喪服服飾文化觀華夏服飾文化,不單是從服飾形制方面表現,也有中國傳統特有的取字文化蘊含其中,以“斬”字命名,取斬斷之意,表明哀痛之最。
“斬衰”必須選用最為粗糙的生麻布,裁剪不用剪刀只能用刀斬,所以謂之“斬”。用最不加修飾的粗糙生麻體現情感最真摯的哀痛與悲戚。《儀禮·喪服》中道:“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為受,受冠八升。重申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斬衰以下等級的喪服在材質上都選用熟麻布,下擺縫邊,等級最低的緦麻最精細。升表示布料粗細程度,一升為八十根經線,斬衰到小功的服飾布料材質精密度在逐步遞增,而悲痛逐步遞減,可見喪服禮儀在服飾上嚴格規定并執行。
喪服服飾禮儀文化體現宗族秩序,以禮規范情感與行為之理,這種服飾禮儀文化也是理法的外在表現,內在核心是“理”,理在古代哲學之中是天地之理,在宗族血緣之中是人情道理。有“理”的情感才有禮法秩序的存在,節制人們的生活方式又充斥情理關懷。
雖然喪服制度大多存在于家族中對親友之死時所用,但這種劃分人際關系的服飾禮儀本質是社會秩序的規范行為,家族情感關系在內,社會團體關系在外,內部秩序影響整個外在社會團體。正因綱常倫理中可展露社會人情結構,所以,以情感為基礎的“禮”制約與規范人們的行為,可見喪服展現的禮法有序。
二、由喪服可見古代時空觀與哲學觀
荀子在《禮記》中提道:“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親疏遠近以喪服制式來區分這點是不可隨意更改的,要遵循相應的禮儀制度穿著對應的服飾。在五服形制上主要體現在布料的粗細程度和制作的繁復程度,喪服中布料越粗糙代表關系越親近,布料越精細關系越疏遠,可謂“哀有深淺,布有精粗”。關系越親近哀痛程度越深,服喪時間越長,是由于越親近者哀傷越深,撫平哀痛所需時間更長。
《禮記·三年間》中提到的:“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是一年喪期制定的由來。一年之中,天地更替四季循環,世間萬物都已更新,所以,以一年來制定的喪期蘊含了古人哲學觀念之中對于宇宙、時空的理解。中國古代禮儀文化中蘊含中國古人特有的時空觀,這也是中國早期哲學觀的體現。服喪三年則是在以一年喪期基礎上延長一倍再加一個月,也就是二十五個月,讓服喪之禮更為隆重。
三、喪服制度在社會結構中體現的禮法道德
《儀禮·喪服》中提道:“為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諸侯為天子,天子至尊也。君,君至尊也。” 君臣之間本無血緣關系,只是等級尊卑的從屬關系。按照喪服制度中的“尊尊”原則,對君主服喪的服飾禮儀要同對父親一樣服斬衰。在喪服制度中的“尊尊”是宗族關系之外的政治等級關系,它很好地詮釋了社會政治中的禮法道德。“尊尊”與“親親”相輔相成,如果說“親親”是個人或家族情感體系的禮制,那么“尊尊”就是尊卑等級秩序的禮制所現。對君王服以最重的斬衰,這種“尊尊”關系更是家國一體的政治禮法體現,父為“親親”關系中的至親,君王為“尊尊”關系中的至尊,為君主服斬衰可見“尊尊”是以“親親”為核心,但“親親”要服從于“尊尊”,把喪服制度服飾禮儀延伸為個人親情與集體秩序、與國家等級的關系,即個人要服從于集體,集體要服從于國家。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喪服制度的服飾禮儀又作為政治工具規范并約束人們的社會禮法道德。從服飾的文化性來看,在這樣一個服飾重紋樣、重裝飾的時期,斬衰裳卻毫無修飾可言,它是人情禮儀與政治文化的結合。
在中國古代沒有社會一詞,但卻存在社會群體關系,其中“倫”是早期社會構造中最重要的標志。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有釋:“倫,輩也。從人,侖聲,一曰道也。”人是組成社會的必要條件,倫所用的人字部,即人與人之間的輩分關系,宗親血緣體現的也是倫,更深層次便是道德層面。荀子在《荀子·富國》中說:“人之生不能無群。”其所表述的是人的生存離不開社會群體,小到宗族倫理的長幼尊卑,大到國家階級的禮法秩序都是“倫”。以“倫”貫穿整個中國古代社會,而喪服制度就是“倫”最直觀的展現。
喪服的服飾禮儀由宗族倫理影射社會道德禮儀規范,這種小到個人、家族,大到國家體制的道德禮儀規范都可由喪服禮儀所約束。不僅如此,喪服中的五服制度還是中國傳統法律的一部分,即“準五服以制罪”。這種“禮律并重”是在禮法之上制約人行為的法律準則,融入儒家思想在法治道德方面約束管理和維護社會的秩序,這是喪服制度在禮儀文化之上存在的法律道德功能,也是喪服制度服飾文化所具有的獨特的屬性。
四、結語
服飾作為一種文化載體,是華夏人民創造的燦爛歷史文明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服飾文化隨著歷史文明的進程不斷演變。喪服是我國傳統服飾中比較獨特的存在,卻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由此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華服飾體系。其獨特的功能性、禮儀性以及文化性都為我們研究中國傳統服飾文化提供了獨特視角和幫助。臺灣學者王關仕在其編撰的《儀禮服飾考辨》序言中提道:“服飾之事雖微,然而屬歷代禮儀典制之所系。”從服飾禮儀文化探究服飾本源,不僅是學習和傳承,更是對歷史的尊重,對文化的探索。
參考文獻:
[1]丁鼎.《儀禮·喪服》考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2]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3]費孝通.鄉土中國[M].上海:三聯書店,1985.
[4]吳飛.從喪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對一個經典概念的再反思[J].開放時代,2011(1):112-122.
(作者簡介:石玥,女,碩士研究生在讀,沈陽師范大學美術與設計學院2019級,研究方向:中國傳統服飾)
(責任編輯 劉月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