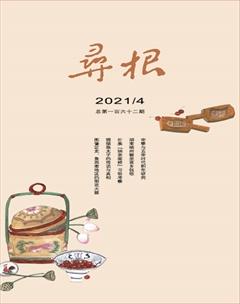論花間詞與流行歌詞的傳承關系
李司同
花間詞派是中國古代一個重要的詩詞流派,誕生于晚唐,繁榮于后蜀,得名于后蜀趙崇祚所編纂的《花間集》。此集收錄了溫庭筠、皇甫松、韋莊、孫光憲等18位詞作者的作品,共計500多首,被譽為“近代依聲填詞之祖”,其中尤以溫庭筠、韋莊的詞作最為著稱。花間詞的創作是晚唐五代時期盛行的流行歌詞的真實再現,對后世同類歌詞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
花間詞盛行之前的流行歌詞
人類社會自有歷史記載以來,生活中就一直伴隨著歌唱活動。晚唐五代時期的詩歌創作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可以入樂,像詞一樣配樂歌舞;一種不入樂,僅供誦讀之用。第一種可以入樂入舞的詩歌,即學界所稱的“歌詩”。據吳相洲先生考證,“歌詩”一名,最早見于《左傳·襄公十六年》,文稱“歌詩必類”,就是指詩歌演唱的意思。《墨子·公孟篇》中也有相關記載:“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漢書·藝文志》中將“詩賦”分為五種類型,其中最后一類就是“歌詩”,在漢代逐漸演變為對歌詞的通稱。唐五代時期,歌詩在坊間里巷傳唱非常普遍。白居易《與元九書》中“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柳宗元《樂府雜曲·鼓吹鐃歌·東蠻》中“歌詩鐃鼓間,以壯我元戎”,陸龜蒙《丁隱君歌序》中“好古文,樂聞歌詩”等相關記述,即為明證。
詞的誕生和音樂旋律有著非常緊密的關系。清代蔣湘南在《醒花軒詞序》論述詞樂關系時說:“詩未入樂,以詩為主。詩既入樂,以聲為主……以唐之樂譜為詞譜,雖填詞者不必盡為樂設,而有一定之譜,則樂工無煩增損,其名為琵琶譜者,樂以琵琶為主也。猶漢樂府以篳篥為主,而以鼓節之,故名為鼓吹曲也。”從中可見樂器在詞樂關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對歌詞產生的影射性作用。合樂而歌是唐五代時期詩歌創作的一大特征,很多詩歌就是為了配合當時盛行于宮廷的燕樂而產生的。
作為唐朝新興的一種俗樂,燕樂不同于雅樂和清樂的平和中正,是融合了外來的胡夷音樂和里巷俗樂等音樂元素而出現的,生動地體現了大唐兼容并蓄、海納百川的胸懷與氣象。《舊唐書·禮樂志》記載:“貞觀元年,(太宗)宴群臣,始奏《秦王破陣》之曲。太宗謂侍臣曰:‘朕昔在藩,屢有征討,世間遂有此樂,豈意今日登于雅樂。”《秦王破陣樂》起初本為軍歌,經過唐太宗李世民重制、朝臣進行作曲之后,先后用于宴會和祭祀,從中可見從燕樂到雅樂的逐漸變化。在唐太宗、唐高宗、武則天等人的不斷推動下,燕樂舞曲逐漸增多,至唐玄宗時期達到極盛。這種經過不同音樂元素融合碰撞后所產生的新興俗樂,有著非凡的沖擊力和感染力。
明人胡應麟《詩藪·內篇》卷六記載:“唐妓女多習歌一時名士詩,如《集異記》載高適、二王酒樓事,又一女子能歌白《長恨》,遂索值百萬是也。”《集異記》所載“高適、二王酒樓事”,就是文學史上膾炙人口的“旗亭畫壁”的故事。此事最早見于唐人薛用弱所撰的傳奇《集異記》,主要講述開元年間詩人高適、王昌齡、王之渙齊名,有一次三人在旗亭共飲,聽梨園伶官唱三人歌詞的故事。唐人靳能為王之渙撰有《唐故文安郡文安縣太原王府君墓志銘并序》,盛贊其詩作“傳乎樂章,布在人口”。元人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三“王之渙”條下亦有記載,稱其“為詩情致雅暢,得齊梁之風”。文曰:
(王之渙)每有作,樂工輒取以被聲律。與王昌齡、高適暢當忘形爾。汝嘗共詣旗亭,有梨園名部繼至,昌齡等曰:“我輩擅詩名,未定甲乙,可觀諸伶謳詩,以多者為優。”一伶唱昌齡二絕句,一唱適一絕句。之渙曰:“樂人所唱皆下里之詞。”須臾,一佳妓唱曰:“黃沙遠上白云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復唱二絕,皆之渙詞。三子大笑。之渙曰:“田舍奴,吾豈妄哉!”諸伶竟不諭其故,拜曰:“肉眼不識神仙。”三子從之,酣醉終日,其狂放如此云。
據傅璇琮先生考證,明人胡應麟在其《少室山房筆叢》卷四一《莊岳委談》中曾經對上述故事加以考辨,認為具體事情可能不實,但“唐人之絕句用之于歌唱者乃當時風習,且之渙與昌齡、高適交往亦有可征,故此事未可遽加否定”。
“安史之亂”后,唐諸帝王雖然也對宮廷宴樂較為重視,但憲宗朝“不禁公私樂”之傾向事實上為私人宴飲大開方便之門,宮廷禁曲大量流入民間。《舊唐書·元稹傳》載:“穆宗皇帝在東宮,有妃嬪左右,嘗誦元稹歌詩以為樂曲者。”王建《溫泉宮行》云:“梨園弟子偷新譜,頭白人間教歌舞。”就反映了文人歌詩在上層宮廷和民間社會廣泛傳播的真實情況。“女子能歌白《長恨》”,就是中唐時期與白居易有關的又一文壇佳話。其事載白居易《與元九書》,文曰:
其余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而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仆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眾樂娛他賓,諸妓見仆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有詠仆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
從上文記載可以看出,白居易的組詩《秦中吟十首》和長篇敘事詩《長恨歌》,都是當時被歌者所熟知的作品,也是在坊間里巷被反復吟唱的歌詩,甚至當時的宣宗皇帝在《吊白居易》中也寫下“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的詩句,可見其影響之深遠。
花間詞人的歌詞創作
晚唐時期,以溫庭筠、韋莊等人為首的花間詞派,其詩歌創作中雖然也有一些對初唐、盛唐的回憶、向往與留戀,但總體來說更多表現為對盛世已盡的無奈、悲傷與悵惘,反映出時代的盛衰變化,寄托著詩人的家國離愁。花間詞創作中,數量最多、藝術水平最高的當數那些描寫士人宴飲和民間樂舞表演的作品。
溫庭筠的詞詠閨怨別愁,被奉為花間派的開山鼻祖。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并州(今山西祁縣)人。宰相溫彥博之孫。他年少時即文思敏捷,天才雄贍,“能走筆成萬言”;他精通音律,善鼓琴吹笛,“能逐弦吹之音,為側艷之詞”;他才情綺麗,尤工律賦,每入試,押官韻,八叉手而成八韻,故有“溫八叉”“溫八吟”之稱。然因年少輕狂,恃才不羈,薄行無檢幅,經常與公卿貴胄家的無賴之徒蒲飲狎昵,醉而犯夜,譏刺權貴,污名聞于京師,以至于后來屢試不第,最后才做了個國子助教。他的詩詞辭藻華麗,濃艷精致,詩與李商隱齊名,時稱“溫李”;詞與韋莊齊名,時稱“溫韋”。從題材內容上看,溫庭筠的作品以描寫兒女艷情、離愁別緒和綺情閨怨為主,常常通過講述自己的故事來抒發個人的感情,或以第三人稱描寫人物,抒發情感,用多種手法層層渲染女性的纏綿悱惻和相思之苦。這類作品在題材和內容上恰好與此類流行樂的“女人歌”相重合,最著名的要數《菩薩蠻·小山重疊金明滅》和《望江南·梳洗罷》。
香軟濃艷華麗的語句是溫庭筠詩詞創作的一大特點。他特別擅長羅列與女性相關的一系列名物和意象,在不表明作者主觀情感的情況下,仍能給讀者描繪出生動而強烈的畫面感,令人不禁在腦海中浮現出一個古代美女深處閨中的畫面。在表達女性情感方面,從“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到“梳洗罷,獨倚望江樓”等生活細節,都生動地反映出女子孤獨苦悶的心情。而在這種愁緒的背后,也刻畫出溫庭筠想象中那些獨守空閨的女子日常的言行舉止與心理情態。溫庭筠經常流連于風月花樓間,擅從第三人稱的男性視角進行敘述,通過細膩華美的文字來描寫形形色色女子的生活和感情,在當時傳播甚廣,甚至連宣宗皇帝都非常喜歡吟唱他的作品。據《北夢瑣言》和《唐才子傳》等文獻記載,當時唐宣宗李忱很喜歡唱《菩薩蠻》詞,相國令狐借用溫庭筠新撰密進之,反復告誡溫庭筠不要泄露出去,他卻“遽言于人”。后來,溫庭筠又因令狐問其“玉條脫”的出處,對以《南華經》后,忍不住譏諷令狐讀書太少,“或冀相公燮理之暇,宜時覽古”,謂之“中書省內坐將軍”,令狐面上無光,漸漸疏遠了他。受盡冷落的溫庭筠,為自己的輕率言行付出了極大的代價,遂以“因知此恨人多積,悔讀南華第二篇”來自傷。當然,溫庭筠的詩詞創作收獲的并非全是好評,甚至有時歌妓的選擇也會影響到當時士人對其詩歌的評論。如范攄的筆記小說《云溪友議》卷下“溫裴條”記載云:“周德華在崔芻言郎中席上唱柳枝,如劉禹錫之‘春江一曲柳千條,賀知章之‘碧玉妝成一樹高,楊巨源之‘江連楊柳麥塵絲,而不取溫庭筠、裴所作,二人有愧色。”
花間詞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韋莊,字端己,京兆杜陵(今陜西西安)人。他是唐初宰相韋見素之后,自己做過五代前蜀宰相,官至吏部侍郎兼平章事,七十五歲卒于成都花林坊。韋莊四十八歲時所作長詩《秦婦吟》,真實地反映出戰亂期間廣大婦女的不幸遭遇,在當時頗負盛名,后人將此詩與《孔雀東南飛》《木蘭詩》并稱為“樂府三絕”。從寫作風格看,韋莊的創作風格并不像溫庭筠那么香軟華麗,而是表現出清逸淡雅、淺顯生動之美。如其《菩薩蠻·人人盡說江南好》一詞寫道:
人人盡說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
壚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作者通過描寫江南獨有的風景之美和生活之美,想起中原地區持續多年的戰亂,忍不住思念自己“壚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的妻子,把即將出門的游子肝腸寸斷的心境表現得淋漓盡致,所以發出“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的勸告,表現出超凡脫俗的藝術張力。王國維在《人間詞話》對其評價說:“端己詞情深語秀,雖規模不及后主、正中,要在飛卿之上。觀昔人顏謝優劣論可知矣。”
韋莊的另一首詞《思帝鄉·春日游》,描寫了一個女子春游時遇到一個風流多情的男子,情不自禁地表達出自己的向往和期待:“春日游,杏花吹滿頭。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詞句語言淺顯,清新明麗,讀起來獨具美感,表達出這位少女想要自由選擇婚姻生活的強烈愿望,雖有借男女之事隱晦表達了政治理想的嫌疑,但至少在字面表達上塑造出了一個在當時背景下顯得格格不入又特立獨行的女子形象。他用白描的手法,表現出了一個天真爛漫、敢于追求愛情的女性,凸顯了她感情的濃烈與真摯,字里行間傳達出一種難能可貴的女性啟蒙與解放的傾向。韋莊的詞不再只是一味“代言”,而是將抒發作者個人情感的功用漸漸拓展開來,在第三人稱和第二人稱之間轉換,不再必須借由寫男女之事來隱晦地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為詞的題材開拓埋下了伏筆。
南唐后主李煜在受到花間派影響的同時,也推動了詞的發展。李煜的詞作多為第一人稱,用大量的白描和比喻的手法直抒胸臆,用寫詞表現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寫盡人間悲歡離合,最終把詞變成了能夠抒發自己感情的工具。葉嘉瑩先生曾比較過李煜和溫庭筠的詞風,說李后主不是在字句上雕飾,沒有像溫庭筠“小山重疊金明滅”的這種裝飾和修辭,他寫“林花謝了”“太匆匆”就是表達客觀事實和感受,這種描寫的直白和簡單就是李煜的特點。
李煜《浪淘沙·往事只堪哀》其一寫道:“往事只堪哀”,這個開篇直接點明作者回首往事而惆悵的思想感情,接著用“一桁珠簾閑不卷,終日誰來”和“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對夢醒前后的場景加以對比,令人備感痛苦;“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清平樂·別來春半》),比喻淺顯易懂,卻又耐人尋味,發人深思,在平實的語言中透露出對人生的種種真切感受和深刻反思。“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把寫作的手法和意象的運用巧妙結合起來,使人完全能對他的愁緒感同身受。
花間詞對后世歌詞創作的影響
倚聲填詞是花間詞創作的一個重要規則。這種規則要求在既定旋律之下不能填入有違旋律走向之聲調的字詞,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作詞人的填詞空間,也考驗了作詞人的詞匯量和音韻感。歐陽炯在《花間集序》中寫道:“名高白雪,聲聲而自合鸞歌;響遏青云,字字而偏偕鳳律”,體現了花間詞人對侉聲填詞和唱辭合樂可歌特性的精準把控和孜孜追求。這種對唱詞的創作規范一直影響了后世各派的詞人,也影響到當代流行音樂歌詞的創作。華語樂壇上出現的一些“代言體”詞作,即由男性詞人從女性視角為流行歌填詞,就是最好的例證。
由李宗盛作詞作曲、辛曉琪演唱的歌曲《領悟》,收錄于辛曉琪1994年同名專輯中,比較有代表性。該首歌詞主要表達了三層意思:
第一段歌詞是:“我以為我會哭,但是我沒有,我只是怔怔望著你的腳步,給你我最后的祝福。這何嘗不是一種領悟,讓我把自己看清楚,雖然那無愛的痛苦,將日日夜夜在我靈魂最深處。”這段歌詞是作者想表達的第一層意思,即以女性視角來審視自身,在無愛的痛苦中反復品味咀嚼,叩問自己的靈魂,尋求思想的解脫。
第二段歌詞是:“我以為我會報復,但是我沒有,當我看到我深愛過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樣無助。這何嘗不是一種領悟,讓你把自己看清楚,被愛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從來不在乎。”作者想表達的第二層意思,即以女性視角來審視男性,“當我看到我深愛過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樣無助”。一方面,這位善良的女性雖然因男人對她造成的傷害非常痛苦,卻仍然用憐惜的眼光默默注視著對方。另一方面,她又希望男人能夠通過這場感情的糾葛反思自己的過往行為,認清自己的處境與責任。但男人可能還沒有意識到“被愛是奢侈的幸福”,因為“可惜你從來不在乎”,這才是最令女人痛心和遺憾的結果。
第三段歌詞:“啊!一段感情就此結束。啊!一顆心眼看要荒蕪。我們的愛若是錯誤,愿你我沒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應該滿足。啊!多么痛的領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來時路的每一步,都走的好孤獨。啊!多么痛的領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愿你掙脫情的枷鎖,愛的束縛,任意追逐,別再為愛受苦。”這段歌詞是作者想表達的第三層意思。作者巧妙地敘述了女人一波三折的心理變化:首先,女人從感情的結束和心的荒蕪出發,認真思索二人之間的愛是不是一個錯誤,并本著為愛負責的態度,喊出“我們的愛若是錯誤,愿你我沒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應該滿足”。其次,女人回顧了自己與男人交往的經過,領悟到當初自己愛得過于投入,“你曾是我的全部”,以至于失去了自我,如今回過頭來細細回味,才發覺“回首來時路的每一步,都走的好孤獨”。最后,女人再次對“你曾是我的全部”的沉淪狀態進行反思,最終痛定思痛,決心一切重新開始,對于自己曾經深愛過的男人沒有痛恨和報復,而是用中國傳統女性最為寬容的態度向對方表達了最為深沉的祝愿,“只愿你掙脫情的枷鎖,愛的束縛,任意追逐,別再為愛受苦”,用一唱三嘆的旋律進一步渲染了女主角的無限傷感。
其實,無論是《當愛已成往事》中“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風雨”,《給自己的歌》中“舊愛的誓言像極了一個巴掌,每當你想起一次就挨一個耳光”,“愛戀不過是一場高燒,思念是緊跟著的好不了的咳”,還是《夢醒時分》中“因為愛情總是難舍難分,何必在意那一點點溫存”,“有些事情你現在不必問,有些人你永遠不必等”,這些歌詞都倡導女性對愛情持要瀟灑的態度,不必像溫庭筠筆下的女子一般把愛情當成生活的全部,唱出了新時代女性全新的愛情觀,與花間派詞人所塑造的幽怨女子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顯然,此時的中國社會中的女性已經能夠站在愛情的制高點,告訴男伴不必執著于愛情,最好去找尋新的天空。男女在愛情方面真正做到了地位平等甚至女性處于更高之位,才能使得傳達這種訊息的歌曲被大眾所廣泛接受。
總之,詞的發展進程是一直被社會背景的轉變以及承上啟下的革命性人物的出現所推動的,從敦煌民間詞到花間代言詞,再到文人抒情詞,溫庭筠、韋莊、李煜等人無一不在此過程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他們的創作使歌詞有了更加豐富的情感表達方式和人文關懷形式;另一方面,他們也推動了詞雅化的進程,使詞不再僅僅是供王公貴族在歌舞宴會時欣賞的藝術,同時具有了像詩一樣詠物言志和直抒胸臆的作用。花間詞派作為奠定了早期詞的創作規范的一個流派,對后世詞的發展影響深遠。直至今日,我們還是能夠在當代的流行歌詞中找尋到與唐五代歌詞相似的題材、元素和創作方法,充分說明中國歷史上歌詞的傳承是從未間斷的,在經過歷史的洪流一次次大浪淘沙后,仍然能夠尋覓到古時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