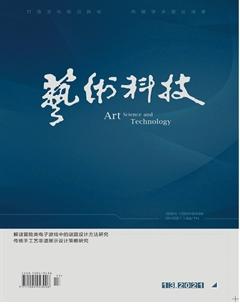《一個(gè)人的村莊》中獨(dú)特的手法及其生死觀的情感流露
摘要:《一個(gè)人的村莊》是劉亮程的經(jīng)典散文作品,全書從黃沙梁一個(gè)普通農(nóng)民的身份出發(fā),描繪了一個(gè)村莊里各種景物、動(dòng)物和人物以及他們的日常活動(dòng)。他與世間萬(wàn)物的相處交流,給全書增添了生氣和靈氣。作者用獨(dú)特的手法描寫鄉(xiāng)土生命和死亡現(xiàn)象,體現(xiàn)其通透的生死觀和對(duì)生死的考量,帶領(lǐng)讀者自覺(jué)思考領(lǐng)悟生死,形成積極的生死觀。
關(guān)鍵詞:《一個(gè)人的村莊》;獨(dú)特手法;鄉(xiāng)土生命與死亡;生死觀;情感流露
中圖分類號(hào):G634.3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4-9436(2021)13-0-02
《一個(gè)人的村莊》由“人畜共居的村莊”“風(fēng)中的院門”“家園荒蕪”三個(gè)部分組成。在筆者看來(lái),作者所描述的村莊可能并不是專門指一個(gè)有名字的具體村莊,也不專指他所居住生活的那個(gè)村子,而是一個(gè)在中國(guó)隨處可見(jiàn)且不足為奇的小村莊。在這個(gè)村莊里,每個(gè)生命都有自己的軌跡,即使狗或牛也是如此,人勞動(dòng)的時(shí)候,牛也勞動(dòng),人休息的時(shí)候,狗也休息。作者劉亮程在他筆下的村莊中扮演著閑人的身份。“閑人”不必憂慮莊稼的收成,只怕錯(cuò)過(guò)了感受世間萬(wàn)物的律動(dòng),在他的眼中,“人與事都有著明朗、飽滿的生命力”[1]。他躺在曠野里聽鳥語(yǔ)蟲鳴,享受田野間的微風(fēng)帶來(lái)的涼爽,品位每朵花、每棵苗帶來(lái)的芬芳。
1 劉亮程獨(dú)特的鄉(xiāng)土生命與死亡敘述
許多人鐘愛(ài)這本書,正是因?yàn)樗频L(fēng)輕的基調(diào),讓人在喧囂的城市生活中感受到鄉(xiāng)村的安寧,“用簡(jiǎn)樸的文字記錄一個(gè)村子,卻能讓人感受到真實(shí)有力的生活脈搏”[2]。而筆者看重的是作者描寫的鄉(xiāng)村生活背后所引發(fā)的關(guān)于生死的考量。本書中近百篇散文都源于對(duì)鄉(xiāng)土生活的記憶,卻始終以生死的話題貫穿。往往剛讓人嘗到生活的甜頭,就話鋒一轉(zhuǎn),表達(dá)對(duì)死亡的看法。死亡意識(shí)總是緊接在生命現(xiàn)象之后,“無(wú)可否認(rèn),中國(guó)古代生死觀都對(duì)死亡有一種隱形的抵觸”[3],但在劉亮程這里讀不到這種抵觸,更多的是一種毫不避諱的坦然。在他看來(lái),死亡只是一種正常的歸宿,我們來(lái)到世間不過(guò)是一場(chǎng)命中注定的歷練和體驗(yàn),既然死亡是任何人都無(wú)法避免的,那為何不正視它?正因如此,他才能輕易地直面生死。
劉亮程的“鄉(xiāng)村哲學(xué)”一直是人們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也是許多文人研究和探討的主題。但他獨(dú)特的死亡敘事卻沒(méi)有得到應(yīng)有的重視。他不像余華寫死亡那般濃厚,字字句句看似平淡,卻讓人倍感壓抑,喘不過(guò)氣來(lái);不像蕭紅對(duì)鄉(xiāng)土人物死亡的命運(yùn)充滿憐憫;也不像汪曾祺在筆下的鄉(xiāng)村小人物身上都傾注了自己內(nèi)心深處的向往和憧憬,帶有自己的理想。他只是用略帶調(diào)侃的語(yǔ)氣,用隨處可見(jiàn)的鄉(xiāng)土事物,重復(fù)寫著不足為奇的鄉(xiāng)土活動(dòng),卻能讓人切實(shí)感受到生和死,平淡卻迷人。
2 劉亮程的生死觀在書中的體現(xiàn)
在《馮四》中有這樣一句話:“這是多么簡(jiǎn)單純粹的一生。難道還會(huì)有比這更適合的活法?”他所謂的簡(jiǎn)單純粹的一生,僅僅指投生黃沙梁幾十年后死掉的一生,而他眼中最適合的活法也是和普通農(nóng)民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休的天天年年。村子是永恒的,而人的生命卻是有限的,村子存在的目的就是收容人在這里生存、繁衍、勞作。人的死亡,在作者眼里不過(guò)是搬離了他生活的村莊,去了另一個(gè)地界而已,而村莊所謂的永恒,也只是實(shí)體意義上的永恒,村莊的靈魂早就隨著村莊人生命的結(jié)束而消散。村里人也許并非有意識(shí)地改造村莊,但就是他們每天的日常勞作,才增添了這個(gè)村子的精神內(nèi)涵。村莊能保持最初的自然閑適,正得益于村莊人的“無(wú)為”,他們無(wú)心追名逐利,對(duì)這片土地只有播種和收獲的需求,勤勤懇懇只一心將簡(jiǎn)單的日子經(jīng)營(yíng)好,這樣村子才能一直保持最初的純粹,同時(shí)保留一代又一代人勞作、生活的珍貴剪影。
人的生死也許是我們一生中最重要的兩件大事,獲得自己和外界的過(guò)多關(guān)注無(wú)可厚非,但最值得我們思考和學(xué)習(xí)的是作者對(duì)非人類的死亡也解讀得如此透徹。作者得出結(jié)論:“任何一株樹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我們不難看出,莊子“天地與我并生,萬(wàn)物與我同”的思想對(duì)劉亮程創(chuàng)作的影響,并且他將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傳達(dá)給讀者。
3 書中表達(dá)生死觀念所用的手法
在《一個(gè)人的村莊》中,對(duì)生死觀的表達(dá),劉亮程用得最多的反倒是白描手法。他把千百年來(lái)鄉(xiāng)土世界的原貌直接呈現(xiàn)出來(lái),但我們可以看出,作者筆下的鄉(xiāng)土生死,既不重視歷史的時(shí)間性,也不刻意突出深刻的哲理性,大手筆的粗線條概括中帶著精雕細(xì)琢的細(xì)節(jié)描寫,白描中也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刻畫。不需要理性的語(yǔ)言加持,不需要強(qiáng)行套入所謂的鄉(xiāng)村美學(xué)和格格不入的鄉(xiāng)愁思想,更不用刻意強(qiáng)調(diào)農(nóng)民貧困、愚昧等問(wèn)題,畢竟這里“人的物質(zhì)欲望很低,而情感需求則很高”[4],靠零散的生活片段和記憶串聯(lián),始終貫穿生死的敘述主線。其實(shí),這些才是鄉(xiāng)土生活最真實(shí)的模樣,農(nóng)民在不知名的小村莊里生活勞作,潦草一生,在黃沙梁那樣的村莊中,無(wú)論是人或物的生死,不被重視才是常態(tài),無(wú)聲無(wú)息才最真實(shí)。這樣的白描留白,反而更能觸動(dòng)讀者。
除了白描外,書中的比擬手法也用得十分精當(dāng),通過(guò)巧妙的比喻修辭,賦予萬(wàn)物人性思想和人性特征,表現(xiàn)出作者對(duì)故鄉(xiāng)的情懷。“從生態(tài)自然觀角度來(lái)看,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是由人對(duì)自然的態(tài)度所決定的”[5],而對(duì)于讀者來(lái)說(shuō),平淡通俗的表達(dá)也能引發(fā)思考,形象貼切的比擬更容易引發(fā)詩(shī)意的想象,喚醒讀者內(nèi)心潛藏的浪漫。其實(shí)人與萬(wàn)物之間聯(lián)系的維持,絕大多數(shù)取決于人,想要達(dá)到真正的親近,除了不過(guò)分干預(yù)自然規(guī)律外,更要做到理解和尊重。可以向大自然學(xué)習(xí),但不能一味索取;可以與大自然互動(dòng),但不該一味保持強(qiáng)勢(shì)。“只有真正地尊重愛(ài)護(hù)自然,用平等的眼光看待萬(wàn)物,人和自然界的矛盾才能得到真正解決。”[6]他筆下的黃沙梁正是做到了人與大自然真正意義上的親近,才能讓村莊由內(nèi)生出一種親和之美。所以,他選擇的擬體通常都是常見(jiàn)的事物,尤其是在鄉(xiāng)土生活中隨處可見(jiàn)的事物,加上自己農(nóng)民的身份,選擇的擬體免不了俗套,卻又恰巧因此增強(qiáng)了生活氣息。不僅如此,《一個(gè)人的村莊》中選擇的都是一些勤勞樸實(shí)的擬體,映射出黃沙梁的農(nóng)民為了美好生活而艱苦奮斗的樸素思想,“勞動(dòng)這一行為本身是神圣的,但勞動(dòng)的主體——人,是極渺小的”[7]。如“一條狗能活到老,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最初讀到,只認(rèn)為在寫狗的一輩子,后來(lái)才慢慢悟出,作者正是用狗的不容易,側(cè)面烘托出人這一生的艱難,“生命很長(zhǎng),追尋生命的深度和寬度尚屬不易”[8],簡(jiǎn)單平凡的一生尚且不容易,更不必說(shuō)精彩燦爛人人羨慕的一生。但“最可怕的不是生活的艱苦,而是面對(duì)生活的消極”[9],所以盡管村莊里條件貧苦、生活不易,但還是能讓劉亮程如此著迷,筆者認(rèn)為主要還是村民的樸實(shí)樂(lè)觀和鄉(xiāng)土生活的充實(shí)純粹打動(dòng)了他,在這里,他可以做回最真實(shí)的自己。
4 作者在書中的情感流露和主旨升華
雖然《一個(gè)人的村莊》中作者對(duì)生死的態(tài)度還算豁達(dá)樂(lè)觀,但不難發(fā)現(xiàn),他也有對(duì)生活的焦慮和恐懼。比如“孤獨(dú)”“盲目”“荒唐”等大量貶義、消極字眼出現(xiàn)在文章中,暗示了黃沙梁生活的另一面和隱藏在作者內(nèi)心深處的恐懼和迷茫,那是一種只有真正生活在這里的人才能感受到的矛盾而又復(fù)雜的情感。“一個(gè)人”的村莊,是由千千萬(wàn)萬(wàn)孤獨(dú)的“一個(gè)人”構(gòu)成的村莊。在筆者看來(lái),這里的“一個(gè)人”既是作者這種孤寂情緒的發(fā)泄,也是他對(duì)所生活的村莊的一種占有欲和歸屬感。大自然有“物競(jìng)天擇,適者生存”的準(zhǔn)則,社會(huì)中也有許多潛藏的優(yōu)勝劣汰的生存法則,我們生活于其中,不會(huì)獲得絕對(duì)的自由,但在自己的“村莊”里,可以盡情放肆,脫下偽裝,分享自己的喜悅,宣泄內(nèi)心的苦悶和不得志,這些平日里不敢輕易釋放的情緒都可以在這里得到宣泄,因此人們能夠清楚地感受劉亮程“就算身處虛無(wú)縹緲之中,還是要去尋找那個(gè)干凈明亮的地方”[10]的信念。正是基于這樣的信念,他把生死轉(zhuǎn)化成了各種情感意象,比如鄉(xiāng)土生命的荒誕和無(wú)奈等等,透徹地表達(dá)自己對(duì)鄉(xiāng)土生死世界的直觀把握和情感隱喻。畢竟像黃沙梁這樣的鄉(xiāng)村,每個(gè)人都處于社會(huì)底層,無(wú)法與命運(yùn)抵抗,因此生活賜予什么樣的環(huán)境和條件,他們都只能欣然接受,這是鄉(xiāng)村人民骨子里一種怯懦卻又質(zhì)樸的最真實(shí)的情感展露。所以,他認(rèn)為“每個(gè)村莊都是孤獨(dú)的”,他在這片土地上留下自己同樣孤獨(dú)的腳印,“在他眼里,沒(méi)有什么是應(yīng)該或者不應(yīng)該的”[11],仿佛這里每個(gè)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軌跡和這樣生活的道理,好在他的想法和思維沒(méi)有被壓垮,所以劉亮程的散文既真實(shí)又空洞,既寫實(shí)又不乏浪漫,“社會(huì)活動(dòng)中的窮困庸碌與精神世界的波瀾壯闊形成鮮明對(duì)比”[12],因此才能用純粹的思維和黃沙梁村營(yíng)造出與世界不同的空間,這片空間能足夠吸引那些終日在城市勞碌的人。
劉亮程沒(méi)有選擇永遠(yuǎn)在這里扎根,他暫時(shí)離開了村莊。出于各種原因,他現(xiàn)在需要長(zhǎng)時(shí)間生活和奔波在城市中。但其實(shí)他永遠(yuǎn)離不開了,故鄉(xiāng)的種種都成了他的一部分,流進(jìn)了血液里。而“個(gè)體的命運(yùn)或許可以改變,群體的命運(yùn)卻自有其道路”[13],他可以通過(guò)努力改變自己的人生,讓自己活得更加精彩、更有意義,卻無(wú)法改變黃沙梁一代又一代人的命運(yùn)。劉亮程或許根本不想也不會(huì)借用自己的影響力給黃沙梁帶來(lái)任何資助或改變,他內(nèi)心一定是想讓這片天地始終留存記憶中最初的模樣,這樣屬于他的村莊便永遠(yuǎn)存在。這或許有些“圍城”的意味,村莊里的人拼命想走出村莊,而經(jīng)歷過(guò)大城市生活的人卻又無(wú)比想回到這個(gè)恬淡閑適的小村莊,唯一不同的是,被“圍墻”束縛的人往往帶有想改變卻改變不了的無(wú)力感,而回到“村莊”的人則更多擁有的是歷經(jīng)千帆后的從容,“而實(shí)際上,圍城生于內(nèi)心,也潰散于內(nèi)心”[14]。究竟是“圍城”還是“村莊”,終究還是取決于我們的內(nèi)心。或許是出于對(duì)村莊的歸屬感,又或許出于“落葉歸根”的傳統(tǒng)思想,他之后出版的《虛土》和《在新疆》,仍然是在說(shuō)村莊。“這樣的自我追求,是我們每個(gè)人一生都在努力尋找的生命中真善美的平衡點(diǎn)。”[15]這種追求是沒(méi)有絕對(duì)善惡、對(duì)錯(cuò)之分的,完全出自我們對(duì)自我的認(rèn)知。就像他自己說(shuō)的,他沒(méi)有天堂,只有故土。
5 結(jié)語(yǔ)
每個(gè)人對(duì)生死的看法都不盡相同,這種看法也會(huì)隨著年齡、閱歷的增長(zhǎng)而改變。《一個(gè)人的村莊》教會(huì)我們的絕不僅僅是在鄉(xiāng)土生活中的樂(lè)得自在,而是一種樂(lè)觀卻不乏思考的生死觀念和支撐生活的堅(jiān)定信念,讓我們有能力重新審視自己對(duì)生死的看法,并且積極地活在當(dāng)下。
參考文獻(xiàn):
[1] 張?zhí)瘢态q,李蕊芳.論沈從文小說(shuō)中的生態(tài)意識(shí)——以《邊城》《長(zhǎng)河》為例[J].大眾文藝,2019(08):28-29.
[2] 張悅,康潔.論葦岸散文中的生態(tài)意識(shí)[J].戲劇之家,2019(24):224-225.
[3] 關(guān)欣瑜.淺析電影《入殮師》里的生死觀[J].漢字文化,2019(11):99-100.
[4] 金珺垚,繆軍榮.淺析《邊城》之美[J].漢字文化,2019(03):77,81.
[5] 何婷婷.淺談“尋根文學(xué)”作品中的生態(tài)意蘊(yùn)——以作品《迷人的海》和《白海參》為例[J].漢字文化,2020(10):69-70.
[6] 周林曄.由《瓦爾登湖》看梭羅的生態(tài)觀[J].漢字文化,2019(15):91-92.
[7] 裴蕾.淺析路遙的勞動(dòng)觀——以《平凡的世界》為例[J].戲劇之家,2019(33):212-213.
[8] 周云菁.孫少平的平凡世界:人生就是苦諦,各有各的辛酸[J].漢字文化,2019(12):27-28.
[9] 余雅雯.淺析《小鞋子》里苦難生活中的人性之光[J].漢字文化,2019(18):102-103.
[10] 王學(xué)韜.一個(gè)干凈明亮的地方:虛無(wú)籠罩之下的個(gè)體生命追求[J].漢字文化,2020(19):120-121.
[11] 魏中華.淺析《局外人》中的荒誕世界與對(duì)本真的追求[J].漢字文化,2019(10):41-42.
[12] 余曉曉.淺析《月亮與六便士》思特里克蘭德死亡的魅力[J].漢字文化,2019(18):92-93.
[13] 雍文靜.沈從文湘西文學(xué)世界中的人性與命運(yùn)——讀《一個(gè)多情水手和一個(gè)多情婦人》[J].大眾文藝,2019(03):26-27.
[14] 王欣欣.從《圍城》中的知識(shí)分子形象看“圍城式”人生困境[J].大眾文藝,2019(03):29-30.
[15] 周林曄.生命短暫,價(jià)值恒久——淺析電影《變臉》與個(gè)人價(jià)值[J].漢字文化,2020(02):119-120.
作者簡(jiǎn)介:沈安琪(2000—),女,江蘇揚(yáng)州人,本科在讀,研究方向:生死觀念的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