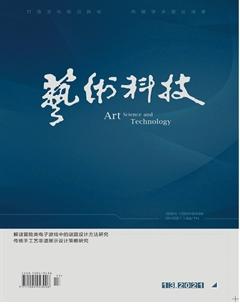論李成《晴巒蕭寺圖》形式與意蘊的整一性
摘要:中國古代山水畫作品的形式和意蘊之間存在嚴格的整一性,這既是深入理解作品的關鍵,也是評判作品的標準之一。本文試以此為視角探析李成的作品《晴巒蕭寺圖》。李成的《晴巒蕭寺圖》在保持外在形式上的高度秩序感的同時,其內在意蘊也具有明確的指向性,二者共同構建了一個雄偉剛健的華嚴世界,這與畫家早期以儒自業和晚期皈依佛教密不可分。
關鍵詞:山水畫;李成;《晴巒蕭寺圖》;秩序感;整一性
中圖分類號:J2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9436(2021)13-0-02
0 引言
在整個中國繪畫歷史中,最獨特輝煌的成就是山水畫。宋代是中國山水畫史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階段,宋代山水畫在11世紀中期達到了巔峰。北宋滅亡以后,宋代山水畫的藝術形式繼續在北方流行,也在12世紀、13世紀蒙古統治下的元代流行。山水畫這一題材是人類創作的永恒主題。中國第一部山水畫論的作者宗炳(公元375—公元443年)提出“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以及“澄懷味像”(《畫山水序》)等論點,這說明中國的山水畫是在“天人合一”的自然觀下孕育而成的。中國繪畫在這方面也有追求,但僅僅滿足于大致的透視比例關系,如遠小近大,所謂“迫目以寸,則其形莫睹,迥以數里,則可圍于寸眸”“去之稍闊,則其見彌小”(宗炳《畫山水序》)。
山水在成為獨立畫科之前,很多時候是作為人物畫的背景出現的,比較有代表性的如魏晉時期的《洛神賦圖》。目前發現的最早山水畫是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圖》,可見魏晉時期山水畫便已經萌芽。北宋山水,如范寬、許道寧等幾乎全都出自李成一系,可見其對北宋山水畫影響之深遠。郭若虛在《論三家山水》提出:“畫山水唯營丘李成、長安關仝、華原范寬智妙入神,才高出類,三家鼎峙,百代標程。”他認為,李成為一代“宗主”,其“氣象蕭疏,煙林清曠,毫鋒穎脫,墨法精微”[1]175。李成生活于五代和宋之間,善畫冬景。李成的山水畫以平遠千里著稱,本文以《晴巒蕭寺圖》為例,分析該作品的外在形式感及內在意蘊。
1 李成與其《晴巒蕭寺圖》
李成(公元919—公元967年),字咸熙,北宋初年營丘(今山東淄博臨淄)人,為唐代宗室后代。其家族世代業儒,李成自幼博通經史,為山水畫大家,被譽為“中國山水畫之父”,也是北宋前期貢獻最大的山水畫家。李成生性孤傲,處在五代亂世,只能在社會上賦閑,靠字畫為生,卻恥于承認以此為生計,他以“自古四民不同流”為名義,將文人學士作為特定的社會階層,先秦以來“士”的概念影響深遠。李成晚年皈依佛教,寓藝合道。李成開創的山水傳統,源于荊浩、關仝,又受到董源和巨然的影響,而后世如范寬、許道寧等更幾乎全都出自李成一系,成為北宋山水畫發展的主流,可見其對北宋山水畫影響之深遠[1]175。
李成善畫冬景,他的山水畫以平遠千里著稱,喜歡表現故鄉齊魯平原的風光,平遠遼闊,一望無際。李成喜好游歷,他的山水畫作品大多是長期觀察和寫生。他的山水畫擅長描繪質感、體積感和氣韻,且作品充滿秩序感,似乎有一種等級化的排序感,高聳的山脈與和諧統一的畫面,或許隱含著皇權威嚴,且有著崇高、剛健的風格。李成出生于儒士之家,因此解讀李成的山水畫作需參照山水畫與儒家“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思想,這對山水畫的欣賞也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審美參照。山水畫可以表達多種意義和價值,常與社會環境有關,通常意義上與文人士大夫相關聯的山水畫有多重象征性,如社會環境、宗教、文學、經濟或者政治等。
在藝術史上,山水畫的風格變化極有代表性,山水畫作為一種抽象的視覺語言,表達人與自然之間的各種關聯。而宋代的文化背景哲學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宋代哲學如理學的產生與出現,作為一種新儒學的演變,其儒學的系統化和世俗化大大加強了對社會的統治。另外,宋代哲學禪宗帶有平民色彩的南派禪宗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繪畫在宋代的高度成熟使繪畫也成為最能代表文人趣味性的視覺藝術之一。北宋山水畫大師,如李公年、宋迪都是北宋晚期李成風格的實踐者。宋初的山水畫基本是對特定地域的實景描繪和創作,畫家不僅實地考察,且尊重自然的真實風貌。因此,李成的作品無論是山石的體積感,還是亭臺樓閣的刻畫,都力求真實,充分體現出宋初山水畫寫實的風貌。
2 《晴巒蕭寺圖》外在形式的高度秩序感
李成所著《晴巒蕭寺圖》為一幅絹本淡設色畫,現收藏于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藝術博士館。這幅山水畫卷是表現成角透視法的經典嘗試。繪畫技巧以及空間感的處理手法在這幅山水畫中展現得淋漓盡致。正如李成在《山水訣》開篇寫道:“凡畫山水:先立賓主之位,次定遠近之形,然后穿鑿景物,擺布高低。”在《晴巒蕭寺圖》中,李成通過寫實的手法細致描繪重巒疊嶂的山脈,這種運用層次遞進的空間法處理畫面的方式獨具特色,畫面中山石輪廓線清晰且具有節奏感,明暗關系通過墨色濃淡得當處理,使山石塊面具有體積感[2]。從畫面看來,經巧妙設計的山石形狀獨特,有縱橫交錯的形式感,近景小塊山石錯落有致呈散落狀,刻畫極為精細,且寫實的亭子隱約可見,亭子融入山石與稀疏的樹蔭之中,使略稀疏的樹木不再那么蕭條,而精心刻畫的棧橋、騎驢挑貨郎及近處亭子里三五人正閑談歡笑著,畫面左側有一前一后兩處從高山流湍急下的瀑布,其構圖明暗虛實不同,前瀑布處于畫面明暗對比關系最為強烈之處,水流湍急,強勁有力,使整個畫面感充滿生機。另外一處則處于畫面遠景遠山之側,潺潺溪流與氣勢恢宏的遠山似乎處于同一維度的空間中,畫面整體動靜結合,仿佛聽到了流淌在山間的嘩嘩聲以及賣貨部的吆喝聲,這有趣生動的細節似乎與靜謐的秋冬山水圖像形成了鮮明對比;山巒靜穆,枯木稀薄,遠景處枯木如同剪影一般稀疏點綴在山巒之上。隨著近景與遠景的空間感,畫家考慮到虛實關系處理了近景具有立體體積感的山石與遠景呈豎著平面狀的遠山,這樣的處理手法在西方古典繪畫中出現得較為頻繁,刻畫山石采取線面結合的方式,通過墨色濃淡以及用筆用線變化如皴法等來增強體積感,畫面的視覺中間點主體物為塔寺,在構圖上把塔寺設計在視覺中心點,其構圖也符合成角透視法(兩點透視法),而局部山體石塊處理的方式符合一點透視法。而描繪如此精準有秩序感的塔寺,和寒林中的樹木有序交匯,這種高度的秩序感是否有某種意義上的象征性呢?
《晴巒蕭寺圖》畫面中間設置主體物亭臺,這種隱含的神圣感或者說儀式感,在尼德蘭文藝復興時期畫家凡·愛克兄弟合作完成的《根特祭壇畫》(1432年,板上油畫)中找到了類似的構圖:視覺中心點位于畫面正中間,前后左右人物略呈對稱狀分布,且前景人物造型及明暗處理風格較為寫實,遠景人物按照透視比例縮小且虛化了人物的刻畫。這與李成《晴巒蕭寺圖》對于山石的處理手法如出一轍。近代很多評論家稱李成為偉大的寫實主義者,從《晴巒蕭寺圖中》的構圖方式、描繪對象的細節中都能看到極為寫實的圖像,且能給觀者帶來身臨其境感。
談到繪畫中的寫實性及相關透視法的運用,不免讓人想起佛羅倫薩早期文藝復興的畫家喬托(Giotto di Bondone),他在空間與光影的處理上有所創新,以《基督進入耶路撒冷》(Christ Entering Jerusalem)為例,在設計畫面的構圖與布局時,主體人物以及起著加強空間感作用的風景(植物及遠山)設計得較為巧妙,將整個人物主體置于前(近)景,將人物分組由左至右,隨即再向左推進至畫面中景、人、物。對比《晴巒蕭寺圖》中人物設計與構圖方式,其人物排列的曲線狀與節奏感頗為類似。而在法國洛可可畫家華多(Jean-Antoine Watteau)于1717年創作的名作《舟發西苔島》中,風景處理手法及意境與中國宋代山水畫有相似之處。畫面中山坡石塊的輪廓是中國畫風格,畫中常見的近似單色的前景風景也是中國山水畫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3 《晴巒蕭寺圖》內在意蘊的明確指向性
中國山水畫中,人物形象永遠顯得那么渺小,甚至可以說是自然界的點綴,兩三人成群或者形影單只藏匿于山野之中。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題材的影響,還是和創作的材料媒介有關,西方風景畫中的人物形象總如同演員一般存在,風景顯得過于幾何化、理性化。而在中國山水畫中,一切顯得那么和諧有序,人與自然融為一體:一幅山水畫不再只是各種不同形象的集合,而是完整、和諧、有序境界的體現。畫面上呈現的是有深度意義的空間,或者簡單地說,是一個有深空間向度的空間。山水畫家們竭力展現的畫面無不充滿迷蒙森然的無窮天地感。這幅作品或許象征著李成作為儒者的宗教寄托,作品中自然景色、人物以及象征著宗教世界的塔寺,恢宏森嚴卻又和諧有序地成為一個整體。儒家美學思想的理念是以道德因素為主導,消除欲望。畫家的責任是摒棄私欲,在繪畫中創造一個純粹的世界。
黑格爾在《美學》第三卷繪畫章節提出:“繪畫內容的基本定性:外在形象、形式感以及內在的內容意蘊,構成繪畫真正內容的不是單按照它們的外在形狀和并列關系來看的單純的自然事物,如果是這樣,繪畫就會成為單純的臨摹;而是滲透到一切事物里去的自然界活潑的生命……只有這種親切的滲入才是精神和心靈活躍的時機……”就李成的山水畫而言,如果觀者試圖原樣復制李成的繪畫形式,不可能獲得他那種將山水融為一體的狀態[3]。李成的畫作展示了想象中的山水,也被認為能替代真實山水。《晴巒蕭寺圖》中近景有流水板橋、水榭茅屋,中景處有一座山丘,上有塔寺、亭臺樓閣工整精細[4]。近景和中景處的山上均有寒林枯木、枝丫在空中張揚。遠景處有山峰高聳,呈高遠之勢,山體多皴擦,表現出山的厚實體積感,另有瀑布從山間飛瀉而下。整幅畫作表現了北方山水的雄偉挺拔,但由于近景的臺閣流水、板橋人物等描繪,畫面又有清幽靜謐之氣。《晴巒蕭寺圖》精心刻畫的樹枝形態以及寒林所營造的某種靜謐的氣息與德國浪漫主義畫家卡斯帕·大衛·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1774—1840)《孤獨的樹》以及《橡樹林中的修道院》的孤獨神秘甚至是略帶悲傷的氣氛,有某種相似之處[1]178。作為崇尚自然的風景畫家,李成與弗里德里希的風景畫中都關注自然季節交替,并借體悟自然以表達內心深處的情感。
4 結語
宋代的藝術發展與朝代的政治命運密不可分,在文化藝術史上,宋代的藝術經典性、獨特性舉世公認。山水畫家在唐五代興盛,在宋代進入輝煌時期,宋代山水畫的特點凸顯了視覺藝術在中國文化藝術史上的重要性。宋代山水畫家把山水生動地描繪出來,使人們在朝堂上也可以欣賞山水的美。北宋著名山水畫家、理論家郭熙很好地說出了宋代包括宮廷貴族在內的上層統治階級對欣賞自然山水美的要求,某種意義上,他是用一種中和的態度將儒家的中庸思想融入了山水畫的創作中。而這種表達方式,在李成的山水畫中早已有據可尋。傳統的歷史傾向于只記錄最顯眼的英雄和他們最著名的事跡。宋代山水畫在不同時期都有不同的象征意義,直到晚期,中國山水畫藝術才從皇權的結構與枷鎖中解放出來,在一個現實與虛構并存的山水世界中尋求一個永恒的精神家園。宋代山水畫中運用高超的繪畫技術所營造的美好的空間感以及寫實細致且擬真的圖像,成為中國古代山水畫最為成熟的標志性特征。
山水畫這種寫實且神秘莫測的山水世界終結于宋代,對于山水畫寫實及多種方式的探究比歐洲畫家早了約兩個世紀。宋代的美學尤其是繪畫,無疑都受到了宋代哲學思想如理學與禪宗的影響。宋代的宇宙意識表現在宋代山水畫中,其中理學倫理本體是與天地宇宙本體不能分離的。因此,仁義與道德就和宇宙觀照密不可分。理學則改造和吸收了道家思想特別是莊子的“天下之大美”。北宋作為中國自然審美觀念發展的重要階段,是對魏晉及五代自然審美觀的傳承和發展,并受到北宋哲學的影響,自然審美注重“真”與“理”,重視對自然的深入體察和感悟,山水畫的實踐發展也為自然審美提供了圖式參照。
參考文獻:
[1] 丁寧.中國畫論導讀[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20:175-180.
[2] 俞劍華.中國歷代畫論大觀:宋代畫論[M].南京: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5:30-31.
[3] 黑格爾.美學[M].朱光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267-269.
[4] 盧輔圣.中國書畫全書[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92-94.
作者簡介:丁文星(1987—),女,湖南益陽人,博士在讀,助教,研究方向:美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