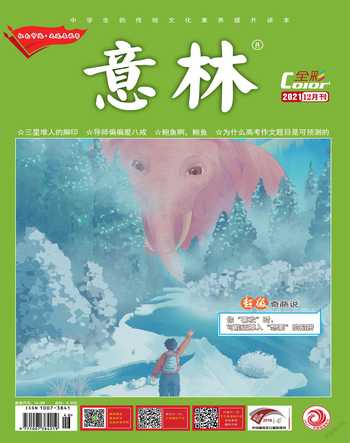“渴望”疾病的人
胡冰霜

她40多歲,多年來總感覺周身不對頭,喜歡看病,也常來精神科。每次,她都要掏出一份“病情清單”,上面詳細記錄著她的病情:長期頭昏腦漲;脖子經常咔嚓作響;喉嚨微微梗起,懷疑是食道癌前期;常常覺得心臟不舒服,喘不過氣來……
等她長吁短嘆地把病情逐條解說完畢,半個多鐘頭過去了。有時,她也會描述一些新狀況:“我經常覺得心慌,就像做賊被當場抓住那種感覺。”或者咧開嘴:“你看我的門牙是不是長得有點兒歪?”要不就掏出一面鏡子邊照邊嘆氣:“你看我是不是對眼?真的有點兒,你沒看出來嗎?”
我認真復查了她的一大包病歷,發現所有的檢查結果都正常。我勸她多鍛煉身體、多活動。她聽后不以為然:“我走不得路,要多多保養才行。人家都說,走路多了損傷關節。”
我漸漸發現,“我身體不好”對她而言不失為最好的護身符和擋箭牌,替她擋住了一切操勞和煩心事。她已經多年不上班,每天的生活就是調理、養生、休息、看病、檢查、吃藥。我抽時間耐心地和她聊天:“要不你做些家務吧?算是鍛煉身體,如果能做做飯也挺好的。”她眉毛一挑:“我從來不做飯,也不會做飯,都是我老幾(四川方言,指那家伙)做。我嫁的那老幾,只會煮個飯,不喊他煮飯才把他安逸死了。”
這場談話似乎全無用處。此后好久,我都沒有她的音信。
幾年后的一天,我騎自行車經過天府廣場,遠遠看到她身穿花衣衫,衫上的五色菊花閃爍飄動。隨后,她興沖沖地跑過街,手里揮舞著一袋X光片,喜形于色,沖我大聲喊:“你看嘛,我得了肺結核,結核菌痰培養都做了,已經開始上抗結核藥了。”
我從沒見她這樣高興過,有點兒詫異。我看了看片子,確實像是結核性胸膜炎,還好沒有肺實質感染。我對她說:“那你要好好地吃藥,抗結核藥至少要吃9個月,不能間斷啊。”她連聲答應:“是的是的,我就是要好好吃藥,還要增加營養。我老幾每天都要給我弄些八寶粥、銀耳羹、烏骨雞湯、藥膳……換著花樣來弄,哎呀,我都吃厭了。”她面有得意之色,然后踮起腳尖對準我的耳朵說:“我給你說嘛,原來我們單位有個女的也是得了肺結核,她老幾也是好生伺候她,天天抱上抱下、喂飯喂水、端屎端尿,她才好了的。”
我聽著實在沒忍住,當街大笑起來。她也笑,笑得很透徹、很幸福。
如今回想起來,我當年給她的一切建議,說了也是白說。其實,她的核心問題是生活毫無意義,對世界和他人的看法一片虛無、一片灰暗,所以才轉過頭來瞄準自己身體的細枝末節,才會發現和體驗到那么多不好的感受,才會推斷和相信自己身上有那么多毛病。而且,一個人如果選擇了她那種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把自己真真切切地引向疾病。
在服用了整整一年的抗結核藥后,她的胸膜結核完全好了,胸片看起來很清晰。抗結核這一年,她過得很高興。有娘家和婆家共同傾力照顧,她名正言順地過足了病人的癮。圍繞著結核的診斷和治療問題,她建立起新的交往圈子和生活內容。由此,她觸類旁通地關注起健身、行走、瑜伽、太極、按摩、烹調、縫紉、花藝、茶道等。家中氛圍日漸溫馨,丈夫和公婆的日子也都好過起來,人人如蒙大赦。
這件事讓我感慨良多,此后便很看重“高興”二字,久而久之,也有了一些心得:高興不愧是天下第一良藥,可以治百病。其實人們身體的許多毛病都是因為活得不開心。
(風行水上摘自《與病對話:全科醫生手記》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圖/ 羅再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