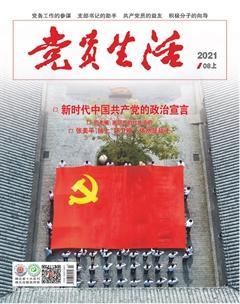多措并舉推動數(shù)字經(jīng)濟和實體經(jīng)濟深度融合
高寶俊
通過實體經(jīng)濟數(shù)字化變革帶來全社會、全產(chǎn)業(yè)、全要素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價值創(chuàng)造模式的改進,以實現(xiàn)經(jīng)濟整體效能的放大和經(jīng)濟的高質(zhì)量發(fā)展。
“十四五”規(guī)劃提出了加快我國數(shù)字經(jīng)濟發(fā)展的倡議。數(shù)字經(jīng)濟已成為我國新時代建設(shè)現(xiàn)代化經(jīng)濟體系的重要動力,是我國提升在全球價值鏈地位的重要支撐,是應(yīng)對逆全球化的有力武器。
一切直接或間接利用數(shù)據(jù)進行資源配置的經(jīng)濟形式都可以稱之為數(shù)字經(jīng)濟。數(shù)字經(jīng)濟包含數(shù)字產(chǎn)業(yè)化和產(chǎn)業(yè)數(shù)字化。數(shù)字產(chǎn)業(yè)化是通過現(xiàn)代信息技術(shù)的市場化應(yīng)用,推動數(shù)字產(chǎn)業(yè)形成和發(fā)展。產(chǎn)業(yè)數(shù)字化是指大數(shù)據(jù)、AI與實體經(jīng)濟融合,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用數(shù)據(jù)進行產(chǎn)業(yè)創(chuàng)新、服務(wù)創(chuàng)新、管理創(chuàng)新,更好地促進產(chǎn)業(yè)發(fā)展。
從2005年到2020年,中國數(shù)字經(jīng)濟增加值規(guī)模從2.5萬億元擴張到39.2萬億元,約增長了16倍。2020年,我國數(shù)字經(jīng)濟規(guī)模占GDP比重為38.6%。2020年我國數(shù)字產(chǎn)業(yè)化規(guī)模達到7.5萬億元,占數(shù)字經(jīng)濟比重的19.1%;產(chǎn)業(yè)數(shù)字化規(guī)模達31.7萬億元,占數(shù)字經(jīng)濟比重達80.9%。相比數(shù)字產(chǎn)業(yè)化,產(chǎn)業(yè)數(shù)字化對數(shù)字經(jīng)濟發(fā)展的促進作用更大,具有更廣闊的發(fā)展空間。
數(shù)字經(jīng)濟和實體經(jīng)濟深度融合的本質(zhì)功能在于,通過實體經(jīng)濟數(shù)字化變革帶來全社會、全產(chǎn)業(yè)、全要素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價值創(chuàng)造模式的改進,以實現(xiàn)經(jīng)濟整體效能的放大和經(jīng)濟的高質(zhì)量發(fā)展。推動數(shù)字經(jīng)濟和實體經(jīng)濟深度融合,要多措并舉。
推進企業(yè)數(shù)字化變革。傳統(tǒng)企業(yè)是推進數(shù)字經(jīng)濟和實體經(jīng)濟深入融合的主體。雖然許多實體經(jīng)濟企業(yè)已經(jīng)建立了信息系統(tǒng),實現(xiàn)了企業(yè)運營信息化,但是如果要進一步利用企業(yè)內(nèi)部數(shù)據(jù)和外部數(shù)據(jù),并基于數(shù)據(jù)作出科學(xué)決策仍然有相當(dāng)長的路要走。因此,實體經(jīng)濟企業(yè)要將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放在戰(zhàn)略層面考慮,利用好信息系統(tǒng),用數(shù)據(jù)改善管理,推進產(chǎn)業(yè)創(chuàng)新、業(yè)務(wù)創(chuàng)新、管理創(chuàng)新。
加快消費互聯(lián)網(wǎng)向產(chǎn)業(yè)互聯(lián)網(wǎng)轉(zhuǎn)變步伐。產(chǎn)業(yè)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為實體經(jīng)濟企業(yè)數(shù)字化轉(zhuǎn)型提供全流程服務(wù),通過優(yōu)化企業(yè)內(nèi)部流程、改善資源配置、提高運營效率、創(chuàng)新商業(yè)模式等,提高實體經(jīng)濟的運行效率和經(jīng)濟效益。當(dāng)前,我國消費互聯(lián)網(wǎng)一枝獨秀,產(chǎn)業(yè)互聯(lián)網(wǎng)剛剛起步,亟須補上產(chǎn)業(yè)互聯(lián)網(wǎng)的短板。
建立法律制度體系。要促進數(shù)字經(jīng)濟和實體經(jīng)濟的深入融合,國家需要建立數(shù)據(jù)資源產(chǎn)權(quán)、交易流通、跨境傳輸和安全保護等基礎(chǔ)制度和標(biāo)準(zhǔn)規(guī)范。針對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科技平臺的壟斷問題,要維護公平競爭,需打造一套適應(yīng)新時代要求的統(tǒng)一市場監(jiān)管綜合執(zhí)法的制度體系。
培養(yǎng)復(fù)合型人才。制約我國數(shù)字經(jīng)濟與實體經(jīng)濟深度融合的瓶頸之一,是缺乏既懂?dāng)?shù)據(jù)又懂業(yè)務(wù)的人才。行業(yè)和企業(yè)要培養(yǎng)能將數(shù)字領(lǐng)域的新技術(shù)與實體經(jīng)濟領(lǐng)域各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深度融合的人才。
加強關(guān)鍵核心技術(shù)和理念創(chuàng)新。我國在數(shù)字經(jīng)濟的創(chuàng)新上落后于美國。美國提出了關(guān)鍵核心技術(shù)如集成電路、微處理器、移動電話、PC和萬維網(wǎng),以及數(shù)字理念如共享經(jīng)濟、電子政務(wù)、電子商務(wù)、物聯(lián)網(wǎng)、智慧城市等。在數(shù)字經(jīng)濟與實體經(jīng)濟的融合中,我國應(yīng)該加強關(guān)鍵核心技術(shù)和理念創(chuàng)新。
推進數(shù)字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數(shù)字經(jīng)濟和實體經(jīng)濟的融合,倒逼數(shù)字基礎(chǔ)設(shè)施的建設(shè)。這包括5G基站、大數(shù)據(jù)中心、人工智能和工業(yè)互聯(lián)網(wǎng)等數(shù)字技術(shù)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平臺、電商、支付、物流等數(shù)字商業(yè)設(shè)施建設(shè),數(shù)字政府、智慧城市等提升公共服務(wù)與社會治理數(shù)字化水平的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
(作者系武漢大學(xué)經(jīng)濟與管理學(xué)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