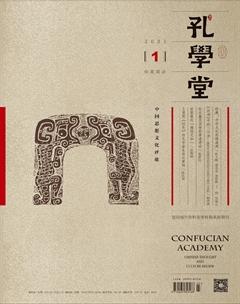論張載的“德性之知”
摘要:張載相信天地萬物合為一體,即天人一物。這個生命體的本源與主宰便是天地之心。心又叫做性。主宰宇宙的天地之心便是天地之性。對人而言,人類天生的氣質之性具有不確定性。它需要變化。變化氣質的方法便是將氣與太虛相結合。絕對的太虛具有超越性。氣質之性,經與超越性太虛相結合之后便轉化為德性或天地之性。德性是合乎天理的人性。正確的生存便是盡德性。盡德性便是德性之知。德性之知是一種擴充善良氣質的活動。這個擴充過程便是仁。仁便是成就德性。過程便是道。道即仁。仁義因此充斥于人間、彌漫于宇宙。這便是儒家的理想國。
關鍵詞:張載 ?仁 ?德性道
作者沈順福,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 ?濟南 ?250100)。
“德性之知”是張載哲學的重要范疇。它的內涵是什么呢?學術界有過一些討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就目前研究成果來看,大多數學者均將其與聞見之知對比,將其視為一種獲得經驗知識的特殊方式,即“德性之知是對性理、人理的認識,見聞之知則主要是對物理、事理的認識,后者要簡單得多”。這種知識,“不是來自外部世界,而是來自先天,即所謂的‘德性之知”。也有學者將其視為一種“以道德意識為核心的‘體天下之物、‘合天心的、‘盡心盡性的心理狀態”。認識說與心理說,僅僅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德性之知的某些內涵,卻不是全部。那么,德性之知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本文認為,“德性之知”中的“知”可以被視為一種活動,其活動主體則是“德性”。“德性之知”即德性的活動。這種“知”的活動,不限于一般的認知,還包含了理解和知道,是一種超越性
活動。
一、由天心到天地之性 [見英文版第50頁,下同]
天人關系論是我們理解德性之知的前提。張載繼承了魏晉時期天人一體的主張,認為“天人一物”:“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者。惑者指游魂為變為輪回,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圣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道陰陽,體之不二 。”天人共為一個物體。這便是天人一物或一天人。故,張載曰:“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我所喪爾(明天人之本無二)”,天人之間并無分離。在張載看來,“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世上萬物繁多,卻最終統一于一物。這便是萬物一體。張載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如此則是全與天地一體,然不過是大人之事,惟是心化也。”真正懂得世界原理的人比如大人、圣人等,自然懂得自己與天地本是一體的。張載甚至稱:“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天下萬物,如同一人,這便是萬物一體觀。
天地萬物合為一體。那么,誰是這個生命體的主宰呢?按照中國傳統哲學,對于生命體來說,心是其本源,同時也是其主宰者。照此邏輯,天地宇宙的本源便是“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自然也是宇宙的主宰。由此,張載等重提“天地之心”,并予以嶄新的解釋:“復言‘天地之心,咸、恒、大壯言‘天地之情。心,內也,其原在內時,則有形見,情則見于事也,故可得而名狀。……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則以生物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雷復于地中,卻是生物。”心是生物體固有的生命之源頭。天地之所以能夠生生不息,原因在于它有自己的心。這個心便是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不僅是宇宙生成的本源,而且是其主宰。這種天地之心,張載有時候簡稱為“天心”:“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聞見之狹。圣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天心即天地之心。這種天地之心不同于聞見或認知心。張載甚至提出:“天本無心,及其生成萬物,則須歸功于天,曰:此天地之仁也。仁人則須索做,始則須勉勉,終則復自然。人須常存此心,及用得熟卻恐忘了。若事有汩沒,則此心旋失,失而復求之則才得如舊耳。若能常存而不失,則就上日進。立得此心方是學不錯,然后要學此心之約到無去處也。立本以此心,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亦從此而辨,非亦從此而辨矣。以此存心,則無有不善。”天地之心并不是認知心。張載進一步指出:“天行何嘗有息?正以靜,有何期程?此動是靜中之動,靜中之動,動而不窮,又有甚首尾起滅?自有天地以來以迄于今,蓋為靜而動。天則無心無為,無所主宰,恒然如此,有何休歇?人之德性亦與此合,乃是己有,茍心中造作安排而靜,則安能久!然必從此去,蓋靜者進德之基也。”天心、天地之心并不思維,不屬于認知心。
面對生生不已的宇宙,我們又不得不相信,在這個生成過程的背后一定存在著某種力量左右著它。它便是天地之心,一個主宰宇宙生存的力量。天地之心不僅是宇宙的生存本源,也是決定者。既然天地之心是宇宙的決定者,那么把住了這個決定者之心似乎就可以主宰世界了。于是,張載提出了千古絕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為宇宙的生存尋找一個決定者,進而力圖通過它來決定宇宙萬物的生存性質和方向、最終成為宇宙生存的真正主宰者。林樂昌先生總結說:“總之,‘為天地立心的基本意涵,既不是人發揮其思維能力‘理解物質世界的規律,也不是由人‘賦天地以道德屬性,而是人(通常指儒家圣人)具有領悟‘天地之仁的能力,并以‘天地之仁的價值意蘊作為宇宙論根據,從而為社會確立仁、孝、禮等道德價值系統。”這一立場雖然消除了傳統誤解,逼近真理,卻依然有所不足。天地之心是宇宙的主宰。為天地立心即主導宇宙。主導的核心自然是仁。故,楊國榮先生說:“人為天地立心,實質上從價值的層面上,突顯了人的創造力量以及人賦予世界以意義的能力。它既是先秦儒學相關思想的延續,也是對這一思想的進一步深化。”張載的這一偉大志向體現了他彰顯人類主體性的意愿或理想。這也是傳統儒家的共同理想。
天地之心是宇宙生存的本源。作為本源,傳統儒家又把它叫做性。故,天地之心其實等于天地之性或德性。張載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性是宇宙萬物生成之源。這種本源之性同時也是主宰者。張載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天地萬物合為一個整體。其中,萬物是身體,而性則是這個整體的主宰者(“帥”)。故,同為本源,心、性同一所指:“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心即性與“知覺”的合一。此即:“心統性情者也。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發于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心統性情。作為本源的心與作為本源的性是統一的,天心即天地之性。
二、“性其總”與超越 [51]
性,在張載思想體系中,分為兩類,即氣質之性和天地之性。張載曰:“性于人無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于人無不正,系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幸,不順命者也。形而后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人天生即有氣質之性。這種氣質之性,其實是一種天生的稟氣。這種稟氣,雖然也叫做性,卻與天地之性相對立。張載曰:“大凡寬褊者是所稟之氣也,氣者自萬物散殊時各有所得之氣,習者自胎胞中以至于嬰孩時皆是習也。及其長而有所立,自所學者方謂之學,性則分明在外,故曰氣其一物爾。氣者在性學之間,性猶有氣之惡者為病,氣又有習以害之,此所以要鞭(后)〔辟〕至于齊,強學以勝其氣習。其間則更有緩急精粗,則是人之性(則)〔雖〕同,氣則
〔有異〕。”萬物稟氣有所不同,故而有氣質之性。這種氣質或氣質之性,具有偶然性和不確定性。張載指出:“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告子的天生之性觀,僅僅突出了人類的稟氣,而沒有突出人類的本性,因而是一種“妄”見。
因此,張載主張對天生氣質之性進行改造,這就是“變化氣質”。變化氣質的方法,張載稱之為“一”:“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有兩則有一,是太極也。若一則有兩,有兩亦一在,無兩亦一在。然無兩安用一?不以太極,虛空而已,非天參也。”一即統一。統一即兩者的結合,比如虛與實、動與靜、聚與散、清與濁等。這些看似對立的雙方,其實代表了兩種存在方式或存在者。比如動與靜,其中的動指向現實的、經驗的存在:我們只能在時間變化才能夠覺察到動。而靜,則指向超經驗的實體存在,即具有確定性的實在。動靜結合便是經驗存在與超越存在的統一。這便是哲學中的超越性關系。“感而后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圣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沒有氣,沒有虛,都不行。只有二者相結合,才能夠實現超越。
在超越性活動中,最主要的參與雙方便是太虛與氣。那么,什么是太虛?太虛和氣究竟是什么關系?關于這些問題,學術界討論已久,如馮友蘭“氣本論”和張岱年的“氣本根論”,均將氣與理分別開來。陳來則將太虛、氣、萬物等統一起來說,以為三者都是同一實體的不同狀態。楊立華則認為太虛即是無形之氣,氣和萬物是有形之氣。牟宗三則提出“太虛之神”的概念,以之為張載哲學的本原。丁為祥認為張載賦予了太虛形上本體義。林樂昌則認為“太虛”乃是超越的本體。這些觀點,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太虛與氣的關系,各有一定的合理之處。筆者贊同許多專家的觀點,即太虛乃是一個思辨哲學概念,具有本原義、超越義、無形義,并因此區別于形而下之氣質。這種區別于形而下的氣質的太虛,我們可以視為理概念的早期形態。其作用、性質等同于后來的理。
太虛以超越的存在的姿態出現。張載曰:“氣本之虛則湛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于太虛,而卒歸于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發之間,其神矣夫!”太虛是無形無體之存在,超越于經驗。這個無形的太虛和氣之間并非二物,而是統一的。太虛是氣的真身、真諦、究竟或本原。同時,太虛借助于氣而化為萬物。“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太虛是無形的,即不可以被經驗所識別。正是這個無形的太虛,才是氣的真身(“本體”)。反過來說,太虛并非真虛空,而是有氣。太虛是一種無形之氣。這種觀念,到了羅欽順時期,便發展為“理即氣”。
這個超越的太虛是萬物變化的終極性本原。張載曰:“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為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后身而為說也。”太虛是氣的本來真身(“體”)。或者說,太虛便是氣的終極性存在。張載曰:“氣之聚散于太虛,猶冰凝釋于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故圣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于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太虛如水,是變化的終極性本原。而現實之物即氣如冰。水是冰的真身。太虛是氣的真身或終極性本原。冰水關系揭示了氣與太虛的關系。其中,張載曰:“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虛空為萬物本原之性。張載曰:“毋四者則心虛,虛者,止善之本也,若實則無由納善矣。”虛是根據。虛無與氣質的結合能夠克服自然氣質的自然性與局限性。這便是一種超越。
這種超越表現為形而上的太虛和形而下的氣質的關系。張載曰:“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涂,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圣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無形的太虛便是氣的真諦或真身。太虛和氣構成了物體生存的兩個方面,即超越的實體與現實性存在。超越的太虛和氣質的結合,能夠產生超越性的萬般變化。張載指出:“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合一而為神。一旦完成了生存的超越,一切行為便無所不能而為神。“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于易者也。”虛空與氣的結合,便是有無、隱顯、神化、性命的結合。
超越的太虛與現實之氣質的結合,形成了合法的氣質活動。其最終成果便是德性或曰“性”。張載曰:“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物所〕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圣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性是統一的結果,即,絕對的、終極性虛空與相對的氣質相結合。經過這種超越性結合,天生的氣質之性便轉化為合理而合法的德性或天地之性。
三、“德性”之“知” [54]
超越的、形而上的太虛與現實中的氣質的超越性結合,產生了合理或合法的德性或天地之性(天性)。張載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太虛與氣的結合產生了性。這里的性并非初生之性,而是指被改造后的性即德性。這種性,是虛無之體與氣質之物的結合。張載曰:“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這種性乃是有無、虛實的結合。經歷了虛無的超越或虛空的純化,混雜的氣質轉化為合理的氣質。故,張載曰:“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礙則形。”太虛能夠清凈氣質。“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風行則)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如此這般之后,混雜的氣質便轉化為潔凈的氣質。故,張載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圣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由此,便可以貫通天地之間了。這種經歷了超越之后的性,首先屬于天地之性。只有經歷了變化(“反”)之后的性即天地之性,才是可靠而值得信任的。張載曰:“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天性即至誠。至誠即太虛與氣質相結合的活動。
天地之性即天性。所謂天性,從字面來看,即蒼天之性。張載曰:“天能(謂)性,人謀(謂)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圣人成能。”天性即天能。天性、天能是天的活動,自然符合天理:“雖則氣(之)稟(之)褊者,未至于成性時則暫或有暴發,然而所學則卻是正,當其如此,其一作不。則漸寬容,茍志于學則可以勝其氣與習,此所以褊不害于明也。須知自誠明與(自)明誠者有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于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窮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于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會,以推達于天性也。”天行便是天理的呈現,自然符合天理。所以,天行即循天理的活動。這種活動,無疑是合理而合法的活動。具體地說,它是天性依陰陽之變。張載曰:“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天行便是陰陽、乾坤之動。這種動不是單一的活動,而是絕對與相對的結合,屬于超越性活動。或者說,天性之動,乃是超越之動。比如,“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則以生物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雷復于地中,卻是生物。《彖》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天行何嘗有息?正以靜,有何期程?此動是靜中之動,靜中之動,動而不窮,又有甚首尾起滅?自有天地以來以迄于今,蓋為靜而動。天則無心無為,無所主宰,恒然如此,有何休歇?人之德性亦與此合,乃是己有,茍心中造作安排而靜,則安能久!然必從此去,蓋靜者進德之基也。”天地之動,動靜結合,乃能生物。這種生物活動具有超越性。
張載又將這種變化后的本性叫做“德性”:“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德性即文王的本性。這種本性或德性,與理相關。張載曰:“德不勝氣,性命于氣;德勝其氣,性命于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德性能夠主導氣,原因在于德性合理。正是天理才最終主導了氣的活動。這種理,在張載這里表現為太虛,即,在太虛與氣質交流中,太虛之理牢牢地掌控了其中的性質與方向。“為學大益,在自(能)〔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圣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里。”太虛與氣質相結合,便是變化氣質。變化氣質便是德勝氣。一旦德勝氣,性或仁義之性便獲得了合法的地位,即,符合天理。符合天理的本性便是德性。張載曰:“德性本得乎天者今復在天,是各從其類也。”德性依據于天、符合天理。張載曰:“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循天便是依天理。德性是合理的本性。徐洪興等提出這種“德性之知的根據在于‘天理。”這一觀點,不無道理。
這個善良實體即德性,在宇宙生存中具有本源性與主導性地位。張載指出:“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性是本源,宇宙萬物生存的本源。張載曰:“天所性者通極于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于性,遇之吉兇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后能至于命。”性已經超越了混雜的氣質,能夠貫通天地、實現與天地的貫通。這便是“知天”:“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知性便可以知天、進而知宇宙萬物。張載曰:“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于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于命,然后能成己成物,不失其道。”盡性、進而知萬物之性,最終通達天命。這種知便是德性之知。
這種所謂的德性之知,與其說是一種認知,毋寧說是一種活動,即它是德性的活動。這種活動是善氣的擴充、仁氣的流行與貫通。張載曰:“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養浩然之氣須是集義,集義然后可以得浩然之氣。嚴正剛大,必須得禮上下達。義者,克己也。”德性是一種善良氣質。成性便是滋養德性而成人。張載曰:“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后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于此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于廝殺,太下則入于啴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樂便是為了滋養德性之氣。滋養德性之氣便是充實:“己德性充實,人自化矣,正己而物正也。”充實德性便是做人。“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日益持久,德性便獲得了充實與穩固。結果便是成圣賢:“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為上智,安于見聞則為下愚,不移者,安于所執而不移也。”充實德性的成功者便是圣賢。這樣的過程便是德性之知:“‘樂則生矣,學至于樂則自不已,故進也。生猶進,有知乃德性之知也。吾曹于窮神知化之事,不能絲發。”滋養善氣、充實德性的活動與過程便是德性之知。故,楊儒賓曰:“‘德性之知顯然位階高于‘見聞之知,它被視為出自于人與世界的終極根基的一種朗照作用。”“德性之知”是一種朗照活動。杜維明將德性之知理解為“體知”:“德性之知是儒家特別的體之于身的認識, 它有本體論的基礎和實際運作的內在邏輯,它是先驗的但又和經驗世界的聞見之知有緊密的聯系。它的體現不僅在精神生命的高明處,也在人倫日常之間的平實處。如何通過超越的體會建立人格的主體性,并由社會實踐達到禮樂教化的大同世界,即是儒家體知的終極關切。”德性之知是一種身體活動。這部分揭示了德性之知的內涵。德性之知是一種活動或行為。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將德性之知視為“內在德性外化為德行實踐”的觀點有一定的道理。
德性同于天地之性或天性。充實德性的活動與過程便是充實天地之性的活動與過程。張載曰:“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樂教可以使天地之性持久、長大、充塞于宇宙之間。這便是成性:“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成,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也。”修身便是成性。成性便是擴充天地之性。擴充天地之性便是滋養天地之氣:“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涂,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圣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異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成性即讓符合天理的天地之氣充塞于宇宙間。成性即順理:“‘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成性便是得性命之理、進而合理。
這種成德性的過程便是“大”:“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后能有其大。”成性即擴充本性。這種擴充本性的活動,張載又稱之為“大其心”:“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聞見之狹。圣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擴大人心、從而延伸至天下萬物。這種心知便是德性之知。張載曰:“人謂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于耳目之外,則共共知也過人遠矣。”這種德性之知超越了耳目之知。因此,“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啟之之要也”。德性之知屬于合內外之知,也就是自身與萬物的合體。
成其性、大其心,最終還是為了合一。張載曰:“天包載萬物于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為蕞然起見則幾矣。”天的所作所為無不合天理,因此是合理的。人行如果也能夠如此,便也是合理的。所以,張載曰:“愛人然后能保其身,(寡助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能有其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于天,則成性成身矣。”成性便是通達于天地之間,實現天人一體。人行便是天行,符合天理。張載曰:“‘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兇,莫非正也;逆理則兇為自取,吉其險幸也。”誠同時也是太虛與氣的共同活動。因此,誠依賴于氣的感應。成性的過程,便是氣化流行的過程。張載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君子能夠讓自身的善良氣質流行于天下。張載借用了孟子的說法,指出:“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于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圣,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大、圣便是成性,便是與天地同流、萬物一體。張載曰:“有無一,內外合,(庸圣同)。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圣人則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經歷了這番合流,天地萬物與人類便渾然為一體。這便是天人合一、萬物一體,又叫仁。
四、由“知”而“仁” [57]
大心、成性即“誠”。張載曰:“何以致不息?成性則不息。誠,成也,誠為能成性也,如仁人孝子所以成其身。柳下惠,不息其和也;伯夷,不息其清也;于清和以成其性,故亦得為圣人也。然清和猶是性之一端,不得完全正,不若知禮以成性,成性即道義從此出。”誠即成。成即成就德性。“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誠即成性、成德性、成天地之性。張載曰:“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至誠即完善天地之性,同時也是生生不息的過程。由性至道的過程便是誠。張載曰:“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圣,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在誠之中,人類實現性與天道的合一。由誠而至明。這便是誠明。張載指出:“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誠明是天德與良知的統一。成就德性即德性之知。或者說,德性之知便是成就德性的活動。
誠引向仁。張載指出:“誠者,虛中求出實。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又曰‘思誠。”虛即太虛。由至虛之性即德性而產生實在之仁義,這便是誠。誠將德性導向仁。張載曰:“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后可以成人性矣。”仁是存太虛、化德性的結果。或者說,由德性之知最終產生仁。“言繼繼不已者善也,其成就者性也。仁知各以成性,猶(仁禮以成性)勉勉而不息,可謂善成,而存存在乎性。仁知見之,所謂‘曲能有誠者也。不能見道,其仁知終非性之有也。”成性便是仁。“性天經然后仁義行。”由德性而產生仁義。“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仁通于性。或者說,成性便是仁。張載曰:“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偽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仁產生于敦化。張載曰:“‘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敦化即德性的增強與完善,并最終指向仁與智的統一。
這種仁,張載認為,依然是愛:“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者也;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仁即愛人,愛人是一種情感性行為。情感性行為屬于一種氣質活動。故,張載曰:“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眾,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圣人之才,能弘其道。”仁道需要推廣和擴充。這便是德性之知。德性之知即擴充善氣。張載又稱之為“熟”:“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善氣成熟便是仁。
這種德性之知、誠或仁的活動方式,儒家稱之為道。張載繼承了傳統觀點,曰:“道,行也,所行即是道。《易》亦言‘天行健,天道也。”道即生存方式。宇宙的生存方式便是天道。張載曰:“今雷風有動之象,須(謂)〔得〕天為健,雖未嘗見,然而成象,故以天道言;及其(發)〔法也〕則是效也,
〔效〕著則是成形,成形則(是)〔地〕道也。若以耳目所及求理,則安得盡!如言寂然湛然亦須有此象。有氣方有象,雖未形,不害像在其中。”天行之道便是天道。對萬物來說,張載曰:“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圣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四時行、百物生便是仁、便是天道。“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天道生生不已。天道即合乎天理的行為。從個人修養的角度來說,萬物一體之仁便是修己以安人:“‘萬物皆備于我,言萬物皆有素于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于心,則樂莫大焉。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己以安人,修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愾于天下。”盡性便可以天下安仁。
能夠做到這一步的人便是圣人。“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愿無伐善施勞;圣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圣人能夠合內外、成德性。其方法便是誠:“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圣,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圣人至誠,進而貫通天地。“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于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天道也在于誠。
五、結語:新型世界觀的實踐意義 [58]
和大多數哲學家一樣,張載的中心問題也是“如何主宰宇宙?”張載在傳統的宇宙觀基礎上,借助佛教的思辨哲學,將自己的宇宙理論上升了一個臺階,由宇宙觀轉身為本體論或形而上學。在宇宙觀上,張載的基本主張是天人一體、萬物一道。張載曰:“合內外,平物我,自見道之大端。道德性命是長在不死之物也,己身則死,此則常在。耳目役于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惰,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當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萬物一道。由萬物所合成的整體根基于某個東西。這個根基,按照傳統儒家的立場,便是性。“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宇宙萬物,共有一性。后來程頤指出:“《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圣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后蓋未之見。”理一即一性。性進而發展為理。宇宙萬物立足于同一個本性。
在天人一體的宇宙觀下,張載認為由共同的性而可以推知天下:“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诐,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圣人,知鬼神。”天人合一,萬物無遺。萬物與我為一體。盡我之性自然與萬物之性相關。盡性是道。盡我之性便是萬物之道。由此便可以知天道、知性命、知圣人、知鬼神。至此,天下似乎無所不知。德性之知的核心是性通萬物。或者說,萬物一體而貫通。這便是“知道”。德性之知能夠“知道”。至此便實現了天下皆仁的理想。這便是張載《西銘》所描述的理想國。
更重要的是,張載不僅建立了萬物一體的宇宙觀或世界觀,他還力圖以性作為天地的根基,從而為天地宇宙奠定一個絕對的基礎,最終建立一個超越性世界觀或形而上學。張載曰:“性通極于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于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性貫通于無。性獲得了超越性品格。這個超越之“性通乎氣之外”。和早期儒家氣質之性的屬性相比,張載的性增加了一些思辨性或超越性,即,作為總的本源的性,不僅是氣質之物,而且經歷了太虛、虛空的抽象與超越,從天生的氣質之性轉化為德性或天地之性。太虛、德性等概念的出現,標志著張載哲學由傳統的哲學認識上升至抽象的思辨哲學或形而上學。傳統的宇宙觀或世界觀轉身為形而上學。這無疑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
新型宇宙觀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在《西銘》中,張載對傳統的天人關系做了另一種詮釋:“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唯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傀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萬物、眾生與我同類(“物與”),甚至是同胞兄弟(“民胞”),都源于天地父母。萬物生于同一個大家庭。萬物如兄弟。兄弟血脈相連。萬物因此一體。“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后,然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乾坤如同父母。這便是萬物一體的兩個內涵,即萬物為一個生物體,宛如一人,另一個就是萬物血脈關聯。無論是哪一種,其中心意思是萬物相互之間密切關聯,或為一個生物體,或為血脈相親。這種生物體或血親關系為儒家仁義之道提供了舞臺。
(責任編輯:陳 ? 真 ? 責任校對:羅麗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