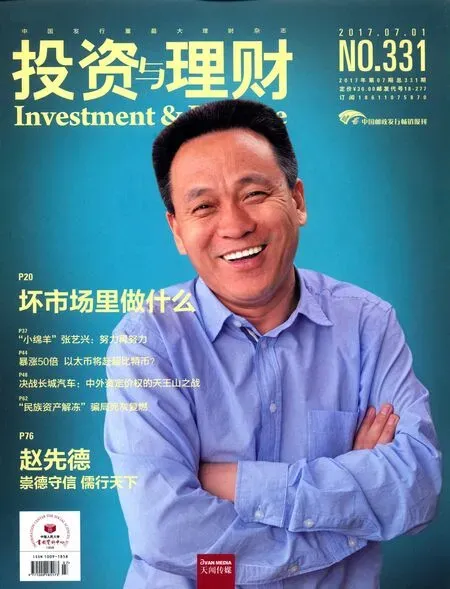放開三胎無法大幅提高生育率解決老齡化還得靠延遲退休
顧洋愷
一、育齡婦女人數下降是近幾年新出生人口下降根本原因
近幾年中國新生人口明顯下降,根本原因是育齡婦女人數在大幅減少,而育齡婦女人數減少則與人口結構有關。
中國存在人口結構不平衡的問題,由于60年代鼓勵人口多生,70年代又大幅收緊人口政策(70年代就開始提計劃生育),因此導致每個年代新出生人口規模有很大不同。65后人數遠多于75后,這間接導致85后人數也遠多于95后。
而當前的問題在于85后已經逐漸邁過生育高峰期,接任生育偉大事業的95后人數明顯不如85后,這就造成育齡婦女人數大幅下行。這就是所謂的生育慣性,由于育齡婦女人數將持續下行,未來10年我國將不可避免地面臨新出生人口大幅下降的問題。
二、教育水平提升導致的觀念轉變是生育率上不去的根本原因
雖然很多媒體將新出生人口下降的原因歸結于大家不想生、不愿生,但實際上并不是這樣。1995年我國育齡婦女生育率是4.9%,而2019年這個數據是4.3%,下降比例并沒那么夸張。從生育率走勢來看,近十年來我國育齡婦女生育率不降反升,特別是在2015年二胎政策放開之后生育率一度大幅反彈。
25-29歲婦女是我國當前生育主體,這部分婦女生育率并未大幅下降,特別是放開二孩政策之后其二孩生育率和三孩生育率均有明顯上升。
在過去,20-24歲婦女生育率是各年齡段中最高的,其一孩生育率一度高達13%。但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很多原本要去種地/打工/嫁人的年輕女勝進入大學,成為大學生,繼續享受接受教育的權力,進而大幅推遲了生育年齡,同時也導致很多女性更加注重生育質量而非生育數量。
三、結婚率對生育率的影響
一個常見的觀點是生育率之所以走低,原因在于現代人的婚姻越來越脆弱,很多人都不愿意結婚了,沒人結婚自然也就沒人生孩子。真的是這樣嗎?
總體來看,近十年來我國結婚率確實是在下降,對生育率產生—定拖累,假如未來結婚率進一步下降的話,生育率可能會跟隨一起下降。因為要么想辦法穩住結婚率不下降,要么引導社會進一步接納非婚生子的現象,以便讓女性在不結婚的隋況下也能養孩子。
四、放開三胎政策對刺激人口增長用處很有限
現在我們已經知道:新出生人口下降的中短期原因是育齡婦女人數下降,長期原因是高等教育普及導致生育觀念轉變,這兩個基本都是不可逆的。
這里,我們做一個粗糙的假設:三孩政策推出后,每個年齡段的育齡婦女三孩生育率上升x%,x%為二孩政策后該年齡段育齡婦女二孩率上升的百分比。也就是說,這里假定育齡婦女對二孩政策和對三孩政策的響應程度是一樣的,屬于較為樂觀的假設。
在考慮了人口結構的影響后,測算發現三孩政策可使三胎生育率從2019年的0.45%左右上升至0.7%左右,絕對值上升了0.25%左右。使總生育率則從2019年的4.3%左右上升至4.6%左右。
基于這個測算,假定生育意愿維持在2019年水平,三孩政策可使2022年我國新出生人口提升100多萬,之后逐漸回落,平均每年能新刺激生育80萬人口。
當然這個是比較樂觀的預測,實際的作用可能沒那么高。
五、我國人口政策面臨取舍兩難
有些網紅經濟學家經常抨擊我國生育政策,造成很多民眾對生育政策產生質疑,認為如果早點放開二孩和三孩政策就能避免老齡化問題,真的是這樣嗎?
首先要研究老齡化的成因是什么,人口老齡化的直接原因不是新出生人口太少,而是老年人太多。
一個合理的人口政策不是一味地提高新出生人口數量,而是降低新出生人口波動率,削峰填谷,如果單純靠刺激新生人口,那么等這些新生人口老了之后仍要面臨老齡化的問題。
我國不僅面臨老齡化問題,也面臨人口數量過多、環境負荷較重的問題。
將人口刺激力度分為三種場景:
第一種是立即采取人口刺激政策,將人口出生數量穩定在1400萬人,在這種場景下,老齡化問題將在本世紀末得到解決,穩態情況下的人口數量為11億人左右。
第二種是在2030年左右采取人口刺激政策,將人口出生數量穩定在1200萬人,在這種場景下,老齡化問題將在22世紀初得到解決,穩態隋況下人口數量為9.5億人左右。
第三種是2040年左右采取人口刺激政策,將人口出生數量穩定在1000萬人,那么老齡化問題要到100多年后,也就是2030年左右才能得到解決,穩態情況TA口數量為8億人左右。
由于我國既要調節人口結構,也要控制人口規模,因此生育政策更多遵循“輕踩剎車”的模式。因此自2000年以來我國年新出生人口呈階梯性下滑的趨勢,分別在1800萬、1600萬、1400萬的階段均出臺過人口政策(雙獨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未來預計也會在新出生人口掉到1200萬和1000萬的時候出臺新的人口政策,預計中國會存2027年左右全面放開生育政策,在2032年左右轉向鼓勵生育政策。
六、80后和90后面臨養老金缺口,只能延遲退休
哪怕從現在開始就鼓勵生育,由于00后和10后人數較少已經成為無法改變的既定事實,80后和90后必將無可奈何地面臨養老金缺口的問題。
我們假定60-70后的養老問題由80一90后承擔,80-90后的養老問題由00-10后承擔。60-70后有4.5億人,80-90后有4.3億人,人數差距不大,養老壓力較小。但00-10后卻只有可憐的3.2億人,比80-90后少了1.1億人,養老難度會大幅增加。
過去我國年輕人數量/老年人數量遠高于2.2倍(定義20-59歲算年輕人,60歲以上算老年人),養老金每年都能有大量盈余,養老壓力非常小。60年代甚至高達10倍,也就是說10個年輕人蕎1個老年人,養老幾乎不存在壓力。
但隨著近十年來我國老齡化加速,養老形勢越來越不容樂觀。從十年前的5.5倍快速下降至2019年的3.8倍,而且隨著未來10年我國老齡化進一步加深,這一比值會繼續快速下降。
我們假定未來男女均在60歲退休,且假定未來隨著內卷化加深,考研成為類似高考那樣的主流趨勢,大多數人24歲畢業以后才開始工作。未來幾十年我國年輕人口/老年人口的比值(25-59歲的人口/60歲以上的人口)會迅速下降,從2019年的3.8跌到2035年的1.6,再跌到2060年的1.1。
2035年我國最后一批75前出生的人變老,第一波老齡化加速期結束。這一時期對應的老年人撫養比是1.6,意味著1.6個年輕人養一個老年人,基本養不動。
2060年最后一批90后變老,到這個時候80后和90后都已經邁入60歲大關,成為老頭老太。這一時期對應的老年人撫養比是1.1,意味著1.1個年輕人養一個老年人,這根本不可能養得起。
那么有沒有可能在不推遲退休的情況下,解決老齡化問題呢?有的。
有六種典型的辦法來解決養老難題:
1、羅馬尼亞式,強制生育政策
上世紀60年代,羅馬尼亞為了促進本國人口增長,出臺過強制生育的政策。要求一對夫妻至少生四個孩子,否則就要面臨懲罰,羅馬尼亞甚至禁止夫妻離婚,以確保婦女充當生育機器。這一政策一度取得過很好的效果,羅馬尼亞人口大幅增長。但強制生育的代價卻是羅馬尼亞人均受教育水平下降、人口素質降低,以及人均壽命下降,到了90年代之后羅馬尼亞人口反而出現了下滑。這一政策宣告失敗。
2、日本式,借債養老
日本老年人占總人口1/3。由于日本是民主國家,老年人有大量選票,政府不敢得罪老年人。為了討好老年人的選票日本政府大力舉債來發養老金,政府債務占GDP比重超過200%,居世界第一。舉債不是沒有代價的,因為償債的主體是未來的年輕人,日本舉債發養老金的做法相當于將償債壓力轉移給了子孫后代。
3、美國式,引進移民,靠移民來養老
美國老年人占比也很高,但卻不存在老齡化危機,根源就在于美國是個移民國家,有源源不斷地年輕勞動力流入。移民既可以為美國帶去高科技人才,也能為美國帶來壯年勞動力。可謂是是性價比最高的方式。不過其他國家想學美國這套很難,比如德國也想學美國搞移民引進來解決老齡化,但德國引進的伊斯蘭難民卻跟本國居民產生很大的文化沖突,也帶來了一些治安問題。
3、南歐式,削減養老金
前幾年為了應對歐債危機,南歐一些國家采取過削減公共開支的政策,養老金就是其中之一。削減養老金可以直接降低養老壓力,立竿見影。但削減養老金勢必會影響老年人利益。
4、北歐式,提高養老保險占工資比例
北歐是福利性社會,年輕人要繳納的養老保險占工資比重比較高,這樣一來老年人的養老金就有了著落。但問題在于,這樣做會加重年輕人負擔,削弱經濟效率。
5、古典式,養老問題家庭自負
在古代,通常都是兒女來負責養老。但古代的人通常都會生很多孩子,而且古代人均壽命不長,基本不存在老齡化問題。
未來我國也不太可能將養老責任推給家庭,畢竟未來家庭規模可能會越來越小,而且啃老的也不少。不過未來以房養老或以資產養老的人可能會變多。
6、德國式,延遲退休年齡
為了應對養老難題,德國—直嘗試將退休年齡延遲,目前德國是66.5歲退休,未來可能會逐漸過渡到70歲退休。
目前看來延遲退休應該是可行性最高的選項,對我國來說延遲退休可能是必然趨勢。成本最低,效力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