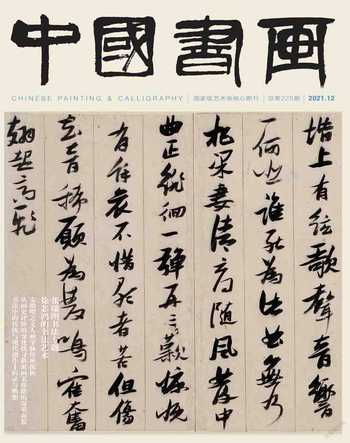浙江大學“巴蜀碑刻研究工作坊”綜述
呂商依 林怡志

繼2018年“山東兩漢北朝碑刻研究工作坊”和2019年“陜西漢唐碑刻研究工作坊”之后,浙江大學藝術史研究所于2021年再次舉辦“巴蜀碑刻研究工作坊”,旨在重返碑刻所處的自然與文化環境,考察碑刻的物質性。巴蜀地區有多處古蜀文明遺址,如兩漢的地面建筑、刻石、畫像石、畫像磚,以及在多種文明交織中形成的佛教文物,而此前未受充分關注的巴蜀碑刻和石闕更是本次工作坊考察與研究的重點。
工作坊成員除浙江大學藝術史系白謙慎、薛龍春、陳軼婷等十余名師生之外,還邀請了蘇州大學華人德、毛秋瑾、蔡春旭,復旦大學陳麥青,成都中醫藥大學王家葵,西南大學曹建,故宮博物院秦明,國家圖書館盧芳玉,西安碑林博物館陳根遠,天一閣博物院陳斐蓉,香港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林霄,山東大學陳碩,中國美術學院林梢青,以及獨立學者賀宏亮、馮陽、凌楓和付玉婷等。
一、訪碑部分
2011年7月10日,工作坊成員先后參觀四川博物院、成都博物館及武侯祠博物館。四川博物院是西南地區最大的綜合性博物館,館藏文物全面呈現巴蜀文明,尤以漢代石刻為最富,也有一部分文物體現了西藏、云南以及中亞文明與巴蜀文明的交融。華人德在觀摩時提到,石棺的兩面稱“墻”,《王孝淵碑》或是墻之一面。他還提到另一名碑《簿書碑》當為二次制作,先刻字再刻畫像,原為石碑,后被改造成墓門。成都市博物館的兩件漢碑名品《裴君碑》與《李君碑》也吸引了學者們的注意,薛龍春與王家葵指出《裴君碑》的刻工較粗糙,刀口似平鏟,刊刻工具與眾不同,白謙慎則從碑的布局、字距與結字談論了巴蜀漢碑與山東漢碑的區別,而華人德注意到二碑形制與漢代陶樓的聯系。
11日,前往雅安,首先觀摩城郊的《高頤闕》。此闕建于東漢建安十四年(209),是我國現存雕刻最精、保留最善的石闕,其子闕、闕前石獸與闕后之碑均存。華人德推測,漢人或許先將石塊壘成石闕再刻字,《高君頌碑》題額在右,紋飾在左,他和林霄認為這一形制可能是從埃及或兩河流域傳入。此后,工作坊成員先后觀摩了雅安博物館的《趙儀碑》、蘆山縣的《樊敏闕》并《樊敏碑》及滎經縣的摩崖刻石《何君尊楗閣刻石》。與四川出土的很多漢碑相似,《趙儀碑》無界格,石上刻字大小相間,甚至互相交疊,出土時已是斷口平整的三段,薛龍春指出該石或許在建立后不久就被改造利用。華人德補充稱其中一塊上的空白區域原或為雕刻畫像所留,因漢時許多碑都既有畫像又有文字。《何君尊楗閣刻石》在宋代已有記載,于21世紀初重新被發現。作為迄今存留最早的東漢刻石,它顯示了篆隸嬗變的微妙消息,在書法實踐與書法史視野之下都很有意義。此外,作為武帝略通西南夷路線的直接證據,此碑亦有極高的文獻價值。
12日,登凌云山。樂山以嘉州凌云寺大彌勒石像聞名,另有盛行于東漢至南北朝時期的崖墓。數百座崖墓層疊分布于岷江兩岸,規模不一,大家著重參觀了景區內原地保護的麻浩崖墓博物館。崖墓內為仿木結構建筑,其梁飾與壁畫多為出行、宴樂等世俗場景及蜀郡百姓所崇拜的西王母形象。
13日一早,行至都江堰,訪治水功臣李冰像上的漢代題刻,隨后至金沙遺址博物館。作為古蜀王國都邑,金沙是繼三星堆之后成都平原的又一個文明中心,其遺址出土有大量象牙原料、象牙器、金器、銅器、玉器、石器與漆器等珍貴文物。
14日上午,抵桂湖碑林公園,《王稚子碑》《石門關碑》等皆藏于此。薛龍春比較《王稚子碑》與漢闕文字風格,認為或非漢人手筆。華人德指出《石門關碑》原是墓門,其文字乃幾代人多次補刻。午后,前往廣漢三星堆博物館。華人德認為,三星堆青銅像及其他銅器的風格在十六國成漢陶俑中或有所延續。隨后,又行至綿陽市博物館觀摩兩漢至清代的各種搖錢樹。搖錢樹主要流行于漢代,是漢代貴族生活的縮影,也是時人信仰之寫照。
15日傍晚抵渠縣,翌日于鄉野田埂民居間走訪漢闕。渠縣有漢代仿木結構建筑石刻墓闕6處,其漢闕完整性不及高頤闕,子闕已佚,僅留有石基的痕跡,但我們仍能通過數量可觀的石闕,系統了解其建造手法、雕刻技藝、內容與書法藝術。尤其是《沈府君神道闕》與《馮煥神道闕》,隸書的末筆多舒展恣肆,突破界格,很可能與周邊有較大空白有關,讓人聯想起崖墓題字中的“朱秉”。
17日一早,在重慶三峽博物館內,工作坊成員就熹平二年(173)《景云碑》的內容、表現風格與其碑穿的獨特形制進行了深入探討。由于出土較晚,該碑書法如新發于硎,從中可以揣摩刻工程式參與了碑刻書法風格的塑造。隨后前往大足石刻。大足的摩崖造像始建于唐乾元元年(758),至兩宋時期達到鼎盛,體現了宗教的世俗化與佛教的本土化發展。
二、研討會部分
7月18日,在一周的考察之后,“巴蜀碑刻研究工作坊”在成都舉行閉門會議。上午場由薛龍春先作引言,其后華人德、陳麥青、王家葵、陳根遠、秦明與毛秋瑾等6位學者就近日于巴蜀地區所見石刻或相關引申內容依次發言,并進行交流。下午場由白謙慎主持,與會嘉賓參與討論。
在引言中,薛龍春首先闡明實地考察對書法史研究的意義,并強調了白謙慎主張的“面對原作以理解原作”“以原作為中心的藝術史研究”。他指出浙大藝術史系近年連續舉行碑刻工作坊,旨在讓參與者通過對碑刻所處環境、空間位置、類型、大小與質地的接觸與認識,綜合考察碑刻的、風格與意義。這種以解釋作品為中心的研究并非是對藝術社會史的有意區分,而是在藝術社會史取得豐碩成果的今天,提醒研究者不要忽視“作品”本身。
長期以來,巴蜀地區的碑刻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視,除偶見于宋代著錄之外,此地區的碑刻甚至在乾嘉時期都不曾被金石學者真正了解,直到劉喜海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任四川按察使后才開始被大量收集,且借由《三巴孴古志》一書逐漸進入學界視野。本次訪碑所見有一些是2000年之后新出土的文物,然而相應的考古報告卻少見關注。
薛龍春從三峽博物館藏帶銘刻的劉宋泰始五年(469)石柱出發,聯系其與南京蕭景墓神道“反左書”石柱之間的相似性,以神道石柱銘文面“左右相對”而非垂直于神道方向的實際空間位置入手,指出巫鴻以“透明之石”來討論“反左書”的意義或許存在一些局限。他還推測,在漢闕遺存豐富的四川地區,有相當多的闕并無銘刻,很有可能是因為“闕”總是與有銘文的“碑”共存。通過實地考察,薛龍春也發現《高頤闕》枋頭文字實為“貫光”而非宋人所擬寫的“貫方”,兩闕皆屬高頤而非高頤兄弟。薛龍春指出,《王孝淵碑》并無界格,字距較小,類似于山東畫像石題字,而隨書寫而逐漸擁擠縮小的碑陰字體,也顯示出碑文字數并未經過精心計算。對于《趙儀碑》,薛龍春推測碑陽中部內容為趙儀所屬,而左右部分都是題名,故字較小且分布略低。另外,通過對單字“屬”的筆畫特征分析,確信碑陰、碑陽乃一人所刻,它們之間存在的視覺差異,或因陰陽兩面漫漶程度不同所致。該碑存在的隸書簡化趨勢與王暉石棺上的銘文非常相似,接近于東晉墓志的風格,弧線減少,波挑不顯。
隨后有六位學者就相關內容做主題報告。華人德表示此次訪碑重點在于對四川地區占比最巨的漢闕之考察,并且認為除目前記載在冊的29件漢闕之外,還有一些殘缺或形制較小的沒有統計,而一些六朝“神道柱”其實也應歸于石闕一類。四川的闕最有名者即為《高頤》《馮煥》與《沈府君闕》等,因其上有字,故格外受金石學者重視。此次訪碑活動共觀摩了14件闕或其局部,幾乎占到有記載的全國漢闕的半數。那么,眾多石闕為何會涌現于巴蜀地區?闕在西漢不曾出現,于東漢一度盛行,無銘闕很可能原為當地富者所有,后受黃巾起義之影響,闕主在書刻前即遠走避難。華人德又以《幽州書佐秦君神道石闕》為例,指出“神道”“神道闕”均屬闕之稱謂,“神道”原為兩闕之間的道路,而后人往往將“神道”與“闕”連稱,如《太室神道闕》《少室神道闕》。關于渠縣石闕,他認為這些現存單闕前身或為子母闕,子闕易丟失或被村民挪為他用,至今尚存的單一母闕并不等同于畫像石呈現的單闕形制,或《幽州書佐秦君神道石刻》那樣本身即不配置子闕的單件石柱。闕雖都是石質,但其造型模仿木結構建筑。在現存畫像石中,部分石闕位于大門兩側,故他猜測位于側面的子闕具有“墻”的含義。華人德引征相關文獻,分析闕最早可能來源于周公擇都洛陽時,注意到伊水兩岸香山與龍門之形。此外,樓觀與闕在古代或屬同類,如漢畫像石或磚中都有闕存在,《榖梁傳》中亦載“(晉景公)八年,使郤克于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此處的樓或也指闕。另,西漢上林苑中也曾因“仙人好樓居”而建有益延壽觀,《古詩十九首》中也有“西北有高樓”句,說明漢代已有高樓建筑。那么,立在墓前的闕是否是通向天門的標志?結合畫像磚繪有人于兩闕間迎接,兩者之間或有相似性。華人德還細數《秦君神道石刻》《泰始五年石柱》與《梁蕭宏墓闕》等帶有波斯、印度風格的望柱形制,以佐證當時與異域的交流程度遠超今人想象。華人德最后指出,蜀國的碑闕體積天然大于中原地區,乃得益于四川地區能就地取材,無須從遠方運輸。
陳麥青報告的是《延年石室題字刻石》的發現年代、地點及其遞藏傳拓情況。根據原拓,其上所刻內容為“陽嘉四年三月造作延年石室”,現存于上海圖書館的有題跋的拓片被裝裱成軸,上有端方、繆荃孫、惲毓鼎、翁斌孫、楊鐘羲等人題跋,另有羅振玉觀款,羅還在1915年將題字雙鉤收錄于《漢晉石刻墨影》中。在羅振玉《俑廬日札》《漢晉石刻墨影》《石交錄》、方若《校碑隨筆》、劉承幹(實出自褚德彝之手)《希古樓金石萃編》與柯昌泗《語石異同評》中,關于此碑的發現年代有不同說法。柯昌泗另有《漢晉石刻略錄》稿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陳麥青結合盧芳玉《柯昌泗〈漢晉石刻略錄〉的成書體例及貢獻》與相關引文,得知此石在四川巴縣被發現,并被收錄于1900年去世的王懿榮之《漢石存目》,不過此目錄經羅振玉校補刊行,不能作為關鍵依據。關于此石的發現地點,陳麥青詳考羅振玉、鄧少琴、柯昌泗、馬子云與高文等著錄與上圖藏本中題跋內容,總結出兩種可能,一為郫縣,二為巴縣,聯系到龍王洞向多煤礦資源,而郫縣并不以山脈與礦產見長,他更認同巴縣一說。《延年石室刻石》先后經于溥倫、柯昌泗與慶云堂遞藏,最后傳至故宮,其間伴隨著不同拓本的產生。陳麥青認為,文物“原地保護”既有其益處,也有其難處。結合《延年石室刻石》的遞藏與現狀,他認為相較于“只藏不拓”,影印是一種更理想的保護形式。
王家葵以《瘞鶴銘》研究作為開篇,隨即切入《何君閣道碑》。建立于東漢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的《何君閣道碑》最早在南宋被發現,作為“建武中元”紀年的實物證據,在當時引起金石界與史界的轟動。但明人楊慎曾在蜀地尋找六次而不獲,可見再次湮沒。此碑在晚近至少兩次出現于著錄,一為清代二馮所撰《金石索》,二為清末沈賢修重刻并立于雅安的《何君閣道碑》,不過兩者均與現存實物相去甚遠。王家葵隨后依據南宋幾種隸書字典如《隸韻》《漢隸字源》等記錄的《何君閣道碑》字樣重新拼湊,又結合實物證據,發現宋人著錄中載“尊”字的特殊寫法實為碑中筆畫殘破處,可見南宋時人所見與今日所見相同,此結論是只根據拓片所不能及的。王家葵還就顏真卿傳世書跡有別于其他唐人書跡的形制問題申發了個人見解。
陳根遠的報告以西安新出碑志所見唐代柳公權、顏真卿、李商隱與韋應物等名家書法為中心。柳公權《楊承和神道碑》于2021年3月17日于西安棗園發掘出土,今藏西安考古研究院。《楊承和神道碑》為恢復晚唐名宦楊承和名譽之用,其撰文者為王起,從事件的發生時間與官銜署名等推斷,此碑或許是柳公權59歲所書,與目前存世最早的柳書《回元觀鐘樓銘》為同一年。2020年夏,顏真卿所書《羅婉順墓志》出土,陳根遠否定此碑為他人代筆之可能性,書此志時顏氏39歲,個人風格雖尚未完全形成,但開張環抱之勢已見端倪。通過對比《元大謙墓志》與《羅婉順墓志》,雖后者有界格,但兩者行列排布都十分整齊,這也反映出唐代墓志應是先書丹再摹勒鐫刻入石,界格并非必須保留之物。
李商隱撰書的《王翊元暨夫人李氏墓志》十幾年前出土于長安。該志書法帶有晚唐瘦硬風貌,也盡顯李氏個人的書寫水準。而大歷十一年(776)的《韋應物妻元蘋墓志》為韋應物撰文并書,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撰”字與永泰元年(765)《李璀墓志》如出一轍,很可能當時并不區分撰者和書者,雖然后者只署“韋應物撰”,其實也應是韋應物所書。
秦明以黃易鑒藏《王稚子闕》舊拓為例,探究清代金石學視野中的蜀中漢刻。故宮博物院藏有四川漢刻拓本12種,相較于中原地區的漢碑而言,并非重點。馬衡跋所藏剪裱本《樊敏碑》說當時拓本因“視為奇貨,索值極昂”,可見《樊敏碑》的市場作假行為已不稀見。故宮博物院藏《樊敏碑》達13件,也證實了此碑在彼時已成收藏熱點。雖然近現代的漢碑著錄已頗為可觀,但黃易《小蓬萊閣金石目》中僅著錄五種四川漢碑,包含被證偽的《孝廉柳敏碑》與《漢故王君之碑》。相較于記錄在案的179件漢碑,四川漢碑占比并不顯著。黃易在著錄《王君稚子闕》時,特地注明是明末拓本,可見當時蜀中地區還沒有專事拓碑的工作團體,故市場上沒有新拓流通。正因為黃易的著錄與收藏,《王稚子闕》被清代金石學的集大成著作《金石萃編》所收錄。而《王稚子闕》真正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要歸功于劉喜海《三巴金石苑》的收錄與廣泛傳播。劉不僅是重要的金石學家,也有專門的工作班子。
毛秋瑾從漢碑銘刻工的角度出發,涉足冶金技術與銘刻工具的跨學科研究,以考察材料、工藝與石刻面貌之間的關系。原石的雕刻方式從拓本上無法直接感知,以漢中博物館藏《漢鄐君開通褒斜道刻石》為例,毛秋瑾認為其字口由鑿子鑿出,而非以刀刻出,并提出了一個問題,即此次訪碑中見到的《何君閣道碑》為何種工具所刻?她認為,漢中博物館所藏三件《漢鄐君開通褒斜道刻石》《石門頌》《石門銘》之間的原始距離或許對研究其刻鑿工具有所助益,不過現在三碑均陳列于博物館中,已經脫離最初的環境。參考褒斜棧道的建筑類型與出土的相關漢代鐵錘鐵斧,不同的建筑工具或許也會在銘刻工具上有所投射,并關聯于風格呈現。而就冶煉技術而言,毛秋瑾猜想,東漢蔚為大觀的畫像石制作或與當時煉鋼技術的進步有關。
下午場由白謙慎主持,他講述了小型工作坊之于學術研究的意義,并且強調了藝術史中傳統的技法、物質與文獻等內容對研究的重要性,與會人員隨即開始自由討論。
蔡春旭提出,關于華人德在上午的會議中所講到的《幽州書佐秦君神道石闕》,當時出土的殘件共有16件,屬于神道的部分計4件,其余為闕的殘件。如果其同屬一組,則一組中均包含柱與闕。結合現存的南朝等時期的石柱,現存石闕的形制或許是后世不斷成形。此外,從上述石闕所存的各類殘件看,早期的各種部件似乎是自由組合,而“闕”這樣的觀念似乎是在形制固定之后才得以產生。華人德回應,事物都會經歷不斷完善的過程,比如墓志形制在歷朝歷代的呈現也有所不同,因此“闕”的發展規律也大抵有其相似性。他還提及《書法叢刊》四川碑刻專號上刊登的石獸類型或是從其他石闕處零碎所得,因此欲知曉闕的形態流變,必然離不開對原始環境的審視,而目前我們對石闕的稱呼還稍欠統一。對上午毛秋瑾談論的議題,華人德表示目前學界對于雕刻工具的關注很少,但工具與石刻的風格關系甚密,甚至導致石刻最終呈現出與書丹相去甚遠的視覺特征。他認為西漢與東漢畫像石之間存在的線條區別,似乎也與雕刻工具不同有關。除了工具,也需要考慮其受體即作品的材質。
隨后蔡春旭又向薛龍春提出關于神道柱與碑之間的方位關系,發現不同的墓也存在神道柱朝向之別。薛龍春回應說,雖然朝向有所不同,但神道柱的放置方式始終相對稱,其上的反左書無疑與對稱性所帶來的禮儀感有關。那么厚的石頭,無論如何不能是“透明”的。華人德、白謙慎、薛龍春、陳碩與蔡春旭等還就反左書的書寫方式與意圖進行了交流,認為當時類似于美術字且用左手書寫的反左書被時人視作一種特殊本領。王家葵補充說,理解反左書也需要從宗教、信仰或民俗的角度進行考慮,陳麥青則表示反左書的出現可能與高等級陵墓儀仗制度的對稱要求有關,或許與“誹謗木”到“華表”的演變和“闕”從實用的木質樓觀到象征禮儀制度的石質構建的發展相類似,只是缺乏文獻記載。
陳碩提出的問題是,中國人用置于公共場所的大型刻石來表達崇高,為何會在東漢出現?他引用趙超“文化西來說”的說法,認為通過絲綢之路,中國逐漸將古埃及與兩河流域的石碑形制內化為自身文化,其形制的確立可以通過相應的考古材料溯源,因此,“工具”或許還無法成為大量刻石在東漢出現的決定因素。白謙慎認為,雖然埃及早有碑刻出現,中國石碑也與之類似,但兩者之間的地理范圍仍存在著顯著的空白區域,其中的過渡性與聯系要如何建立?毛秋瑾舉人類學“文化飛躍帶”之例回應白謙慎的疑惑,認為“空白區域”的出現在其他文明中也確實存在。華人德在認同“西來說”的同時,也從中國本土的需求考慮,如東漢提倡名節與孝道的社會風氣在無形中要求人們借立碑記錄其聲望。位于偏遠一帶的渠縣竟然還留存6處漢闕,這正是當時盛行立闕的證據,而在文字尚未通行的沙漠、草原等地則并無立碑之需。陳碩繼以考古學中的“以時間換空間”,指出碑在埃及的出現時間畢竟領先于東漢四千余年,而其中大規模的系統挖掘還有待完成,如果僅根據少量的文獻記載來填充復雜遼闊的流傳過程,是不現實也不必要的。其后譚頻璇提問,《高頤碑》底座的“龍虎銜璧”是否也是西來說的產物?白謙慎、毛秋瑾、蔡春旭等指出,文化遷移往往呈現出整體性,會滲透進文化受體的方方面面。
賀宏亮在發言時強調,應將四川地區的碑刻與曾屬蜀地的漢中碑刻一并比較,根據陳麥青提到的鄧少琴《益部漢隸集錄》,他提出是否應該確立一個有別于中原漢隸風格的“益部漢隸”概念,并猜想《大開通》《石門頌》《新都石門關》與《王孝淵碑》等風格的相似性,是因特殊的書丹者與特殊工具刻鑿而致。陳文波認為,“益部漢隸”的獨特面貌更取決于雕刻方式的不同而非書寫,并以《樊敏碑》刻工劉勝為例,推測蜀地一帶可能存在流動性較弱、組織松散的石工、刻工集團。蔡春旭認為刻工往往根據當地石質“因材施刻”,并且多以家族為單位形成刻工集團,在某一較為固定的區域工作。白謙慎參肯定了刻法與工匠團體對風格的影響,但又舉例說,蜀地《景云碑》等與中原地區的漢碑亦十分相像,說明某種刻工程式也會流動。陳麥青補充說,有體勢的摩崖與工整細膩的石碑之間要求不同的鑿刻方式。華人德亦持類似觀點,他以刻碑與刻帖之異為例,認為摩崖石工只需掌握大致字形,并非照書丹原樣摹刻。建碑的目的是記功頌德,重要的是文字內容,與刻帖傳承名家墨跡的功能有所區分,故碑與帖也很難融合。
在上述討論的基礎上,陳碩又引出如下內容—當我們在討論碑刻風格的時候,我們在討論什么?顯然,從拓片及其圖像出發的研究,只憑個人審美經驗而忽視了實物本身,巫鴻所述的拓片“物質性”中也包含了諸多可塑性與欺騙性因素。只有排除上述不確定性,才能確定拓片的“物質性”能在何種程度上得到討論。他還就《景云碑》風格問題進行提問,其接近直角狀態的美術字波尾是否能等同于銘石書?而如《西狹頌》中宮打散、四角填滿的非日常書寫字形是否在彼時也屬于一種美術字?如果我們能夠辨明美術字的強化成分與實際書寫之間的分野,或許能突破朱彝尊所說的“漢隸凡三種”。白謙慎回應說,朱彝尊的“美”也經過分類,但他并未使用“風格”概念,因“風格”為西方術語,那么陳碩所述的“特點”能否等同于“風格”?風格通常是一種有意識的自覺追求與傳承,如《曹全碑》《禮器碑》,但有些表現較為隨意,只能稱作“特點”,創作者往往不偏好于風格的總結,而更追求作品的完美。今天在書法研究中引進風格的概念雖便于論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對書法現象的思考。碑刻審美的產生既包括書寫者有意識的追求與后人追加的評價,也與材料本身的屬性緊密相關。有鑒于此,我們要盡量追求對歷史的還原,同時警惕語言與概念的陷阱。
附記:香港近墨堂書法基金會資助了本次工作坊的部分費用,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