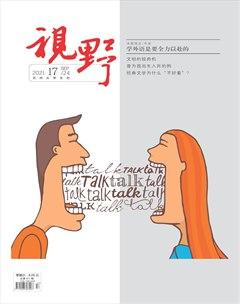如果古人想學外語
黃梓怡
耶和華在那里變亂天下人的言語,使眾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別。
今天的我們走進書店,打著各類旗號的英語輔導書足以讓選擇恐懼癥們落荒而逃;走在大街上,鋪天蓋地的英語輔導班廣告早已讓我們再懶得掃上一眼。然而,你是否思考過,在這一切還沒有出現之前,如果古人們想學外語,他們該怎么做?
古人為什么要學外語
的確,古代交通不便,各個民族溝通交流的機會相對較少,外語需求也很低,但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們相互之間不可能是完全隔閡的,他們相互之間“交流感情”,通常有如下四種方式:
貿易
古代的貿易主要發生在邊境交匯區,來自不同國家的商人在那里販賣各自的物品;也有充當“聯絡員”角色的商人,如絲綢之路上的阿拉伯人,他們往返于不同的國家,為東西方的商品交易牽線搭橋。
移民
在古代,平民百姓的生活極易受到天災人禍的沖擊。一旦遇上蝗災、雪災、戰亂等,賴以維生的田地往往顆粒無收。日子過不下去了,只好去其他地方另謀生路。到了一個新的地方,快速融入當地的最好辦法,當然就是學習當地的語言。
戰爭
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為了方便打探敵情,古代打仗時軍中常有隨行的翻譯。在軍中充當翻譯的常常是使臣,也有一些胡人軍官或和尚兼任翻譯。
文化傳播
除了暴力的方式,古代國家同樣也通過和平友好的文化交流進行溝通。其中典型的代表是西方的傳教士和東方的僧人,他們為了傳教,往往會學習掌握一門甚至多門外語。
對于中國來說,自秦始皇統一六國語言和文字后,中原大地上原本分裂的各諸侯國真正結成一家。但在此之前,中國各地的方言還是存在不小的差別的。比如在春秋戰國時期,南邊的越國人說的方言在中原人看來簡直是火星語。不信來看一下春秋早期的這首《越人歌》——
濫兮抃草濫予昌
枑澤予昌州州鍖州
焉乎秦胥胥縵予乎
昭澶秦逾滲惿隨河湖
翻譯版如下——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
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翻譯版看起來舒服多了對不對?
這么懸殊的差距,交流起來必定會產生困難,因此我國先秦時期就已經有翻譯這個職業了。在《周禮》里,這些翻譯人員有一個神奇的稱呼——舌人。不過隨著版圖的擴大,這些難解的語言也漸漸消失。然而直到今天,在中國南部仍保留有一些語言的“活化石”,如閩南語、客家話等,在外地人聽來同樣是如墜云霧,不知所云。
知名外語學院
外語學習離不開教育機構,古今皆然。古代的外語教育雖不如今天這般成熟,但還是誕生了幾個較具有代表性的外語學院——
國子監
國子監又叫國子學,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教育管理機關和最高學府,由朝廷直屬管理,是專門研習儒家經典的經學學校。
隋唐時期對外交流空前繁榮,唐都作為世界大都市吸引了各地商人、留學生,相應催生了外語學習的需求,國子監因此設立了多國“外語系”,培養精通外語和翻譯的人才。除此之外,國子監還吸引了來自高麗、琉球、日本等國的留學生。因此國子監設有號舍,專供留學生居住。
四方館
四方館最初是隋煬帝楊廣下旨設置、用來接待四方少數民族和外國大使的辦事處,相當于現在的經貿辦。
到了唐代,佛教在中原大行其道,順應時代潮流,四方館變成了佛經翻譯館,主要負責將梵語佛經譯成漢語,玄奘也在此工作過。
四夷館
四夷館由明成祖朱棣于永樂五年(公元1407年)在南京創立,是我國古代第一所真正意義上的外國語學校,也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為培養翻譯人才而官方設立的專門機構。四夷館置譯字生,教習亞洲各民族的語言文字,以培養了解鄰國歷史地理的翻譯人才。
到了清朝雍正時期,四夷館改名為四譯館,并有了統一的外語課本《華夷譯語》。有意思的是,這本書沿襲了漢譯佛經的宇宙最強漢字注音譯法。
同文館
1861年1月,恭親王奕訢奏請開辦同文館。同治元年六月,同文館開辦招生,以培養翻譯人才為目的。學生多是來自八旗貴族的官二代,專職學習翻譯和外交。課程開始時只設英文,后來增設法文、德文、俄文、日文。同治六年又添設算學館,教授天文、算學。
1902年1月,同文館并入京師大學堂,改名京師譯學館,并于次年開學,仍然是外國語言文字專門學校。
學外語,古人可是認真的
在四夷館、同文館這些官辦的翻譯培訓學校出現之前,想要系統地進行外語學習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外語的習得說到底,最重要的是“浸入”式的環境。更何況,一種語言和另一種語言往往并非完全沒有關系,而是會互相影響、相互融合。比如漢唐的絲綢之路上,來自中國、印度、西域各國的商人之間的通用語言是一種粟特語,因為粟特人是活躍在絲綢之路上并且善于經商的民族,而且恰好處于中國和印度之間,他們的語言也就混雜了很多漢語和梵語的成分,為漢人和印度人學習帶來了便利。
當年絲綢之路上的商人是如何學習語言的,今天的我們已很難考證。不過,廣州十三行的商人們學習英語的方法或許能讓我們略知一二。這些商人們學習英語用的祖傳秘訣就是上文提到過的漢字注音法!乾隆年間,出現了一本叫《紅毛番話》的小冊子,上面收錄了英語、德語、法語、意大利語、拉丁語等六種外語,單詞按照粵語發音標注,例如one的標注發音為“溫”,house的標注發音是“孝士”。通過這種簡單粗暴的學習方法,一邊比劃一邊學,就能學到最基本的經商用語了。而這樣一種經典但低效的方法倒也沿用至今,成了現代人和古人難得的共同經歷。
實際上,一直到20世紀,古人們對學外語興趣都不大,朝廷禁止教外國人漢語,也不鼓勵國人學外語。直到科舉制度廢除之后,外語學習才真正為人們所重視。我國上下五千年的漫長歷史中,唯一一次出現過的學習外語的持續興趣只在于梵語。
過去缺乏成熟的教學、學習方法,人們為了學習外語常常是絞盡腦汁,有時甚至要冒生命危險。從下面列出的幾位苦練外語的典型代表中,大家可以管窺過去人們學習外語摸著石頭過河的漫漫長征路。
玄奘
一代高僧玄奘家庭世代為官,從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成年后他四處游學,拜訪了不少國內外高僧,學習經綸和梵語。其中一位老師、印度和尚波頓告訴玄奘,在印度的那爛陀寺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僧人,可以去拜他為師。于是,玄奘踏上了“西天求經”之路,在19年的留學生涯中,邊走邊學,幾乎通曉所到國家的各種語言,可謂是那個時代的多語種人才。
利瑪竇
明朝萬歷年間,利瑪竇以一位意大利傳教士的身份,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一踏上中國的土地,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就深深地吸引了他。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國,也為了更方便在中國傳教,利瑪竇開始向當地居民學習漢語。開始學習漢語的利瑪竇對與拼音文字完全不同的漢字感到很興奮,覺得非常不可思議。由于當時教外國人學漢語是非法的,利瑪竇的老師們都是冒著生命危險給他上課,“補習班”也都是秘密開展。有意思的是,利瑪竇在澳門歷經千辛萬苦終于掌握漢語,自以為可以動身北上進京,可到了北方才發現,自己跟著澳門人學的所謂“漢語”竟是方言,和真正的漢語大相徑庭,中原人說的話他依舊聽不懂。沒辦法,一切只好重新來過,從頭學習真正的“漢語”。
如此一波三折的歷程,利瑪竇的恒心和決心著實令人欽佩。他后來官至尚書,成為第一個在朝廷任職的西方人;并和徐光啟等人合作翻譯了《幾何原本》等西方科學著作,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溥儀
末代皇帝溥儀對英語學習抱有極大的興趣,他的老師是牛津畢業的英國人莊士敦,莊先生送給溥儀一個英文名“亨利”。溥儀從學習英文單詞和一些淺顯的口語對話開始,隨后開始讀《伊索寓言》《金河王》《愛麗絲漫游記》以及許多英文的短篇故事和西洋歷史、地理;莊士敦還會把日常用語、童話、成語故事和很多儒家經典名言翻譯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學中。在莊士敦的教導下,溥儀的英語水平進步很快,甚至能用英語翻譯《四書五經》。
為了跨越語言所帶來的障礙,古今中外的人們都在做著不懈的努力。語言可以是一種工具,也可以是一扇窗,供我們窺見不同文明的寶藏。一路走來,我們學習外語的資源越來越多,越來越優質;我們從對不同民族的猜忌與排擠,到求同存異、互相學習。道路雖仍漫長,但或許這種開放包容的心態,才能幫助我們真正沖破巴別塔的阻隔,合為一家。
(摘自微信公眾號“校友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