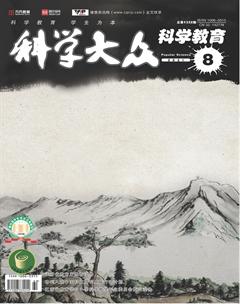中國傳統文化視域下的汪曾祺小說研究
周林曄
摘 要:2020年是汪曾祺的百年誕辰,他被后人敬為“永遠的汪曾祺”。許多年過去,汪老的作品仍廣受關注。本文著眼于中國傳統文化,擬從傳統民俗文化、傳統思想文化兩個方面研究汪曾祺之筆所傳達的人事、人情和人性。
關鍵詞:汪曾祺; 中國傳統文化; 文化審美; 小說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6? ? ? ? 文獻標識碼:A? ? ? ? ?文章編號:1006-3315(2021)8-114-002
汪曾祺說:“小說是談生活,不是編故事。”他是一位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作家。因此,汪曾祺的作品大多以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和審美經驗為基礎,且“納外來于傳統”,刻畫中國本土的好山好水好風景,傳達自己對悠久中國文化和自由人生境界的理解,抒發具有獨特中國審美意味的思想感情。
汪曾祺的小說創作生涯始于40年代,80年代后進入文學創作的高峰期,這一時期的作品也最能體現個人審美風格。他的作品執著追求“藝術地表現美,再現健康人性”這一審美追求。汪曾祺寫江蘇高郵的傳統民俗,展現故鄉歷史悠久的風土人情;寫社會中各行各業的從業者,彰顯小人物身上積淀的中國文化思想和傳統美德;寫一個地方的歷史更替,發展變遷,贊美亙古傳承的中國精神和人性之美。
一、傳統民俗文化
傳統民俗是民間流傳的各種風俗習慣。汪曾祺出生在江蘇高郵,一生中到過云南、北京等許多地方。一方水土,一里人事,構成了一幅幅精美的風俗畫卷。
汪曾祺的許多作品都是在故鄉地域的影響下完成的。汪曾祺故鄉江蘇高郵的人與自然也就成為其小說情節中最基本的因素,作品中人物的生活、情感都與這自然地域息息相關。汪曾祺在《端午的鴨蛋》一文中介紹了高郵人民在端午節的各項習俗:系百索子,貼五毒,喝雄黃酒,吃“十二紅”等。此外,還有吃高郵盛產的“咸鴨蛋”。故鄉所獨有的食物,對于在外的游子來說,是一個標簽,是一股自豪,是一陣回憶,更是家的味道。汪曾祺寫道:“高郵的咸鴨蛋,確實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鴨蛋多矣,但和我家鄉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經滄海難為水,他鄉咸鴨蛋,我實在瞧不上。”他更是直言,看到袁才子的《腌蛋》一文覺得“與有榮焉”。汪老的筆觸平實且不乏幽默,輕快的短句讓人讀來覺得這是一個揣著對自家獨有的東西視若珍寶的可愛心思的孩子。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事實上,一個地方的民風民俗早已在不經意間影響了人們,無論是佳節的盛典,還是歡慶的習俗,都是一個地域居住的群體致以生活崇高的敬意。
《故里三陳·陳四》一篇中汪曾祺詳細地描摹了鄉里迎神賽會的熱鬧場景。從準備看會時到處點燃的香燭、懸掛的香燈,到茶擔子、花擔子、舞龍、高蹺各種玩藝,讀起這樣的文字,讀者仿佛自身也能置身于那樣生動歡慶的場景中,而這無不彰顯著一個地方民俗文化的特殊魅力。就連汪老自己也說道:“我們那里的賽會和魯迅先生所描寫的紹興的賽會不盡相同。”這更加體現出每個地域民俗文化的獨有性,讓人讀來覺得新鮮有趣,不禁被文字所描寫的場景所感染。
汪曾祺還在《戴車匠》一文中提到了故鄉清明的習俗:清明當天吃螺螄,孩子們除了吃,還可以玩,用螺獅做弓把。戴車匠是傳統的手藝人,技藝精湛,每年照例要給他的兒子做一張特號的大弓,人們將對自然、對親人、對生活的情感寄托在一項又一項或大或小的儀式中,而在清明這一天,戴車匠對兒子的關愛便全都傾注在了這令所有孩子羨慕的一張弓中。
人們借助淵源流傳的民俗活動表達情感體驗和文化理想,同時也在其中找尋到自我的價值,這份價值薪火相傳,弦歌不輟,由此衍生出傳揚千年的民族力量和民族精神。
二、傳統思想文化
汪曾祺是一位深受中國傳統思想影響很深的作家。他的筆調浸透著濃濃的中國味兒。汪曾祺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常常在文章中深刻表現中國傳統的人情美、人性美。這都源于他對人、對事、對生活的一顆仁愛之心。儒家道德的核心正是仁愛。汪曾祺愛他人,愛家人,愛自己,愛事業,愛祖國,愛家鄉,愛祖國的山山水水,愛家鄉的風光、風物、風情、風俗。或許正是因為汪曾祺的作品中包含這一樸質而又珍貴的情感,他的文章才顯得不說教、不矯情、不沉重,沒有高高在上的距離感,帶著鮮活的煙火氣,極容易帶入和共情,歷經數年,歷久彌新。
汪曾祺筆下,故鄉的街上侯家銀匠店、戴家車匠店和楊家香店緊緊相鄰。戴車匠是一位勤快精細的手藝人,在別家店鋪才卸下鋪板的時候,戴車匠已經吃了早飯,選好了材料,看看圖樣,坐到車床的坐板上了。汪老對戴車匠工作時的場景也作了細致的刻畫:“戴車匠踩動踏板,執刀就料,旋刀輕輕地吟叫著,吐出細細的木花,木花如書帶草,如韭菜葉,如番瓜瓤,有白的、淺黃的、粉紅的、淡紫的,落在地面上,落在戴車匠的腳上,很好看。”戴車匠雖只有一家小小的門面,店里的板壁上卻懸掛著“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的對聯。戴車匠不在意居住環境的大小,他堅守在自己小小的一方店面里謀求生活,他把手藝練就得爐火純青,他與鄰居交往自在,孩子們也愿意上他這兒來。在我看來,戴車匠正是用自己的雙手在這方雅室中采擷花香的人。
與戴車匠比起來,侯銀匠整天拿著一把小錘子叮叮當當地敲,少了一絲美感,多了些許的沉悶和繁瑣。侯銀匠所求的,便是用自己的一錘又一錘,為女兒爭取一個能夠勉強維持的生活。侯家銀匠的女兒侯菊出嫁前能自己改裝花轎,引得許多人羨慕;出嫁后懂得經營生活,賢惠體貼。侯菊的聰明能干是與父親侯銀匠勤勞、精細的品質一脈相承,侯菊的幸福生活更是老侯銀匠的全部所求。女兒到了待嫁的年紀,侯銀匠千挑萬選才選好了一家合適的人家。侯菊出嫁前,他費盡心思搜羅了點金子打了一對耳墜、一條金鏈子、一個戒指給女兒作嫁妝。直到陸家一刻也離不開侯菊,老侯銀匠又過起了獨自一人淡茶慢酒的日子。
又如在午門歷史博物館門前蹬三輪車的祁茂順,他從前不是蹬三輪車的,他有著令人驚嘆的糊燒活、裱糊頂棚的手藝,但卻為了順應時代的發展,迫不得已改行。許多傳統的手藝人為現實的沖擊所迫,被迫改行,歷史的長河里他們的身影也逐漸消逝。但在汪曾祺的筆下,他們永遠鮮活地存在著。他們仍舊生活在某個民風淳樸的小城鎮、小村莊,遠離了城市的喧囂,他們在古樸的小城里浸染出寧靜、清遠的性格。他們靜默地堅守著自己的崗位,同時又在與人的交往中傳遞著人性之初的溫善與友愛,感受著生活的閑適與詩意。這些人物雖然平凡,但在他們身上又常常閃現出優秀品格的光輝,汪老通過書寫這些平凡而不平庸的人物,引導人們向善、務實、求美。
如今傳統的工匠技藝已經能夠得到保護和珍惜,獨特的匠心依舊能夠煥發光彩。這些人物為謀得生活學成一門手藝,學成是十年磨一劍,堅守則是一生煉一心。他們是“大國工匠”的先行者,是工匠精神的守門人。
汪曾祺還將道家灑脫自然的生活觀念及自然無為的處世態度中的積極部分納入筆下。在汪老的筆下,儒道兩家互補融合,同時,他還賦予了儒道精神新的時代意義,煥發新的光彩。
《釣魚的醫生》中的王淡人便是儒道思想的結合體。初次看到標題中的“釣魚”,我的腦海中便浮現出江邊一凳一釣竿的隱士,一人度一日的圖景。王淡人人如其名,人淡如菊,但其風骨卻熠熠閃光。汪曾祺寫了王淡人的“兩件傻事”。其一是拿命換匾。村里遭遇水災險情,王淡人撐蒿救人,不顧自身安危,只身犯險救人,后來村里人合送了他一塊匾額,上面寫著“急公好義”。其二是王淡人救治、援助幼時的朋友汪炳。王淡人將落魄、患病的朋友留在家里住,“管吃、管喝,還管他抽鴉片”,汪炳甚至“把王淡人留著配藥的一塊云土抽去了一半”,“王淡人祖上傳下來的麝香、冰片也為他用去了三分之一”。王淡人的這些行為無不體現著儒家思想的影響。不顧自身安危、不為金錢利益治病救人、為滿身惡習的汪炳治病正是儒家精神的仁德仁心、正義寬厚,而王淡人生活清苦,安貧樂道,治病救人時英勇向前又不圖一絲回報,轉身卻釣出魚就在岸邊烹飪“起水仙”,在院子里養花弄草種蔬菜,與窮朋友喝酒聚會,又體現出了道家思想的豁達超然、適意隨性。
一庭春雨瓢兒菜,滿架秋風扁豆花。這是醫生王淡人掛在醫室中、他最喜歡的對子。讀到這里,一幅農家院落的畫卷仿佛就在眼前慢慢展開。古人常說:“春雨貴如油。”一場場連綿的春雨過后,滿院的瓢兒菜煥發生機。轉而兩季,秋風習習,落葉簌簌,架上的扁豆藤蔓上又開滿了各色的花兒。王淡人也正如這院中的一草一木,帶著中華民族最原始、最純真的質樸思想在世間過著自己的生活,遵循自然規律,四季循環往復,閑適安然,自在瀟灑。
在王淡人身上,既能看到儒家的積極入世,醫者懸壺濟世,仁心博愛,又能看到道家的閑適愜意,漁夫歸山隱林,親近自然。在汪曾祺筆下,儒道精神的精髓得以現代化、生活化。新時代的“仁”是重人權、重民生的“仁”,而非傳統的“克己復禮”。而現代的“道”也不再是一味地追求“無為”與“避世”,人間草木皆有情,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煙火氣中也可以找到一種踏實安逸、回歸自然本質的“道”。市場經濟大背景下,儒家仁愛的君子風范、道家曠達的人生態度,匯入汪曾祺的筆下,旨在啟迪讀者們在喧囂的鬧市中也要找到一塊供心靈棲息的凈土,在繁雜塵世中保持自然的純凈,在瑣碎生活中找尋生活的樂趣。
三、結語
汪曾祺其人正直、善良、真誠、通達、平和。他眼中的世界和筆下的人物亦是如此。不需要太多跌宕起伏的波折,傳統精神的美、語言文字的韻便自然地從字里行間流露出來。汪老的文章簡短精煉,但淺顯易懂的幾行文字卻蘊含著貫通古今的時代性和民族性。汪曾祺擅長刻畫社會底層人的生活,他們所展現的是舊時候中國社會最普通、最平凡的勞動者的風貌。隨著他們逐漸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一行行傳統工藝和工種也日漸沒落。幸運的是,他們在汪老的筆下得以再現。汪曾祺用細膩的筆觸摹其技、贊其魂、傳其神,用平實質樸的語言寫盡百態人生。而近年來,工匠精神的豐富內涵又常被人們提起。匠,須有技藝,又有匠心。數年流逝,汪曾祺筆下許多傳統的民間手工藝行業如今都已不在,但是每一位匠人熱忱的匠心卻得以代代相傳。
2020年是汪曾祺老先生的百年誕辰,我們重新去回味汪曾祺作品中一幅幅江南水鄉的歷史風俗畫、各行各業的謀生特色和種種規矩、四季節令風物和古老風俗……作為新一代的青年人,站在新世紀的起點上,我們從中國傳統文化的視域再看汪曾祺作品,納外來于傳統,將傳統融入現代,在體悟藝術審美意味的同時,更加力求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蓬勃發展和盎然生機。
本文系江蘇省大學生創新創業項目—— 中國傳統文化視域下的汪曾祺作品研究(項目編號:2020NFUSPITP0757;指導教師:張興春)項目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汪曾祺.此間風雅[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
[2]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
[3]陸建華.汪曾祺的春夏秋冬[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4]夏希.論汪曾祺“高郵故事”的發展演變[J]小說作家作品研究,2012(5)
[5]朱毓瑤.汪曾祺小說的民俗價值[J]文學教育,2018(1)
[6]張守仁.汪曾祺:“最后一位文人作家”[N]文學報,2019-11-21(012)
[7]王奎軍.汪曾祺小說中的地方(高郵)民俗文化[J]河北工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6)
[8]王晶.“寫小說就是寫語言”——汪曾祺小說語言美研究[C]廣西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