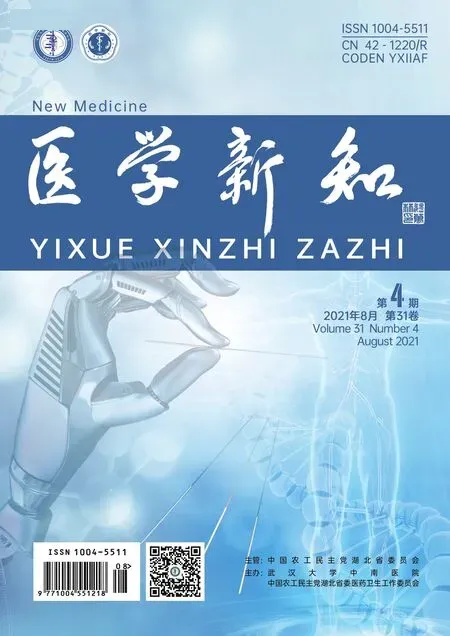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藥物預防、診斷、治療與出院管理臨床實踐指南:證據評價(二)
王永博,羅麗莎,蘆麗葉,婁佳奡,靳英輝
1.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循證與轉化醫學中心(武漢 430071)
2.邯鄲市永年區婦幼保健院(河北邯鄲 057150)
3.武漢科技大學醫學院(武漢 430081)
自2019年12月以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迅速蔓延至全國以及全世界多個國家與地區,對人類的健康與社會經濟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影響[1]。國家衛生健康委于2020年1月23日公開發布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三版)》[2],并于2020年8月19日更新至第八版[3]。世界衛生組織2021年3月2日公布的數據顯示,全球現有確診病例114 140 104例,累計死亡病例2 535 520例[4]。本研究團隊根據WHO的快速建議指南手冊[5]基于間接證據發布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斷與治療的快速建議指南》[6]。疫情暴發后國內外針對COVID-19的大量臨床研究陸續發表,為COVID-19的臨床實踐管理提供了直接研究證據。這些證據推動本團隊更新《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藥物預防、診斷、治療與出院管理臨床實踐指南》(以下簡稱指南)[7]。但在COVID-19特殊情形下,人力和時間都非常緊張,很多研究者并未進行嚴格設計,只是選取日常臨床診療產生的數據進行研究,產生大量的非隨機干預性研究,其研究質量參差不齊。因此,本文旨在全面評估指南中COVID-19藥物預防、治療部分的非隨機干預性研究(non-randomised studies of the effects of interventions,NRSI)的偏倚風險,以期為COVID-19后續指南的制作及更新提供證據支持。
1 資料與方法
以下方法學部分均來自于已發表指南的相關內容[7]。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研究類型為NRSI;②研究對象為確診為任何臨床類型的COVID-19的成年患者(≥18歲,不包括孕婦),其性別、種族、發病時間、嚴重程度等均不限;③干預措施為藥物治療,治療方式不限;④主要結局指標為死亡率、危重轉化率、重癥監護室的入住率或入住時間以及序貫器官衰竭估計評分,次要結局指標為氧合指數/氧合血紅蛋白飽和度、RT-PCR檢測陽性轉陰性時間/比率、胸部或肺部影像學改善或病變吸收時間/比率、臨床改善時間、臨床治愈時間/比率、肺炎嚴重程度指數、體溫/體溫恢復正常的時間、住院時間、機械通氣的發生率/時間以及病毒載量。
排除標準:①重復發表的研究(保留信息最全面或最新的研究);②無法獲取全文的研究;③無法提取數據的研究;④非中英文的文獻。
1.2 檢索策略
檢索文獻類型限定為NRSI,其主要包括觀察性研究如病例對照研究、隊列研究以及類試驗。詳細檢索策略見已發表的系列文章(一)[8]。
1.3 文獻篩選
詳見已發表的系列文章(一)[8]。
1.4 資料提取
提取納入研究的基本信息,包括原始研究數量、納入研究類型、樣本量、主要結論等。數據提取完成后,2名研究者進行交叉核對。
1.5 研究質量評價
采用NRSI評價工具ROBINS-I(risk of bias in non-randomised studies of interventions)對納入的研究進行質量評價。ROBINS-I為Cochrane協作網在偏倚風險工具ROB1.0基礎上研發,用于隊列研究、病例對照研究、類實驗等多種非隨機研究類型干預效果的評價工具[9]。
ROBINS-I是領域評估式工具[10-11],共有7個領域,分為干預分組前、干預分組時和干預分組后。干預分組前包括混雜偏倚、研究對象選擇偏倚。干預分組時為干預分類偏倚。干預分組后包括偏離既定干預的偏倚、缺失數據偏倚、結局測量偏倚和結果選擇性報告偏倚。每個領域都由多個信號問題組成,共計34個信號問題。先對各領域的特定信號問題作出“NA(不適用)/N(不是)/PN(可能不是)/Y(是)/PY(可能是)/NI(無信息)”的回答,然后進一步形成該領域總偏倚風險,最終形成總體偏倚風險。
總體偏倚評估原則:7個領域均為低風險,則總體偏倚風險“低”;若7個領域中至少存在一個中風險,但不存在高和極高風險時,則總體偏倚風險為“中”;若至少一個領域風險高但無任何領域為極高風險,則總體偏倚風險“高”;7個領域中至少有一個領域風險極高則總體偏倚風險“極高”;若風險高或極高/不清楚/缺乏關鍵領域的相關信息則總體偏倚風險“缺乏信息不能評估”。
2 結果
2.1 納入研究基本特征
本文共納入40篇NRSI,其中前瞻性隊列研究5篇、回顧性隊列研究30篇、非隨機對照試驗4篇、準實驗1篇。研究主題涉及藥物預防、治療,其中中藥治療4篇、免疫治療16篇、抗病毒藥物20篇。研究人群涉及8個國家,其中中國23篇、意大利6篇、西班牙4篇、美國2篇、法國2篇、巴西1篇、古巴1篇、印度1篇。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見表1。




2.2 納入研究偏倚風險評估結果
ROBINS-I評價結果顯示40篇研究總體偏倚風險均為“中”或“高”,其中15個研究(37.5%)總體風險“高”,25個研究(62.5%)總體風險“中”。結果顯示,ROBINS-I評價工具的7個領域中有3個偏倚域風險為“中”或“高”,其中15個研究(37.5%)混雜偏倚風險“高”,25個研究(62.5%)混雜偏倚風險“中”,16個研究(40.0%)偏離既定干預的偏倚風險“中”。7個領域中有2個偏倚域風險“低”,其中38個研究(95.0%)研究對象選擇偏倚風險“低”,40個研究(100.0%)缺失數據偏倚風險“低”。結果選擇性報告的偏倚域雖然有38個研究(95.0%)研究偏倚風險“低”,但仍有1個研究(2.5%)偏倚風險“高”。7個領域中有4個領域存在評估信息不全、不清楚的現象,其中研究對象選擇偏倚域、干預分類偏倚域和偏離既定干預的偏倚域“無信息”各有2個研究(5.0%),結局測量的偏倚域有1個研究(2.5%)。具體評價結果見表2。

表2 ROBINS-I工具評價結果Table 2.ROBINS-I tool evaluation results
3 討論
隨機對照試驗(RCT)是評價干預效果的金標準。然而,臨床試驗并非總能做到隨機,NRSI在臨床治療性研究中比較常見,但容易造成研究結果受各種潛在偏倚的影響。本文采用ROBINS-I對納入的COVID-19藥物預防、治療類的NRSI進行偏倚風險評價,結果顯示大部分文獻總體偏倚風險較高。
本研究發現,納入文獻的混雜偏倚風險均為“中”或“高”。大部分文獻僅簡單提及兩組暴露前具有可比性,其中15個研究(37.5%)并未提及采用何種方法對關鍵混雜因素進行控制,如采用分層分析標準化率分析或多因素分析等來控制混雜因素對結果的影響,即文獻沒有表明暴露組和非暴露組間均衡性如何,所以評價偏倚風險為“高”。
有研究顯示,患者年齡≥50歲、基礎疾病、肺部CT分級、發熱癥狀、發熱持續時間、消化道癥狀、潛伏期≥7 d、就醫延遲、居住環境差、個人防護差和吸煙史等均會影響COVID-19患者的治療效果和預后[52-54]。因此,評價不同干預措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時,必須在研究設計階段對可能的混雜因素進行控制或調整,包括基線混雜因素和時變混雜因素。暴露前不同組間患者的一般特征,如年齡、臨床分型、合并癥等因素需組間均衡,否則將引起混雜偏倚,從而掩蓋或夸大干預措施的效果。
本文結果顯示,有38個研究(95.0%)的研究對象選擇的偏倚風險為“低”,所有滿足標準的受試者都被包括在研究中,并且他們的隨訪開始時間與干預開始時間一致,僅有2個研究(5.0%)沒有提供條目相關信息,評價為“無信息”。納入的文獻中大多數研究明確表述了該研究遵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辦公室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三版至第七版或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疑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造成嚴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的臨床處置指南》[55]或本國官方文件擬定的納排標準。
本文納入文獻的研究設計大多是回顧性隊列研究,大部分文獻的數據是從病歷系統中采集的,并且這些數據都是實時記錄的,干預措施在隨訪前明確界定,不存在回憶偏倚。但我們需注意到,在臨床實際治療COVID-19過程中,患者常因常規治療/標準治療干預效果不佳加用或改用另一種治療措施,干預的分配若以最初的干預措施劃分,而未考慮到后續的病人換組,或因強烈的回憶偏倚導致干預分配出現較大錯誤,就會產生暴露組與對照組的錯誤分類。
COVID-19的治療一般為綜合治療,納入的文獻中大部分研究者將常規治療/標準治療作為對照組,常規治療/標準治療聯合待觀察干預措施作為觀察組進行各個結局指標的比較。但部分文獻對常規療法或標準治療,并不予以具體說明或僅進行簡單描述,可能存在重要的伴隨干預措施組間不均衡的情況。本研究納入文獻的研究目的均為干預依從效應,其中16個研究(40.0%)顯示,干預的實施和依從性與預期有偏離,但對結局的影響很小,或重要伴隨干預措施組間不平衡,但采用了合適的統計方法分析干預實施和依從性效果,并考慮了可能影響結局的偏離,偏離既定干預的偏倚風險為“中”。
本文所納入的文獻,基線及隨訪數據較完整,或各組間缺失原因和比例相似,或采取了合適的統計分析方法處理缺失數據,所以40個研究(100.0%)的缺失數據偏倚風險評價為“低”。
本研究關注的主題是COVID-19的藥物預防和治療,關注指標包括癥狀恢復時間、核酸轉陰時間、胸部或肺部影像學改善時間、退熱時間和住院天數等。5個研究(12.5%)顯示結局的測量與預先計劃一致,沒有選擇性分析和報告結果的跡象。34個研究(85.0%)顯示沒有從多個分析中選擇報告結果的跡象。只有1個研究(2.5%)因文章中信息太少無法做出判斷。所納入文獻整體而言,干預組間結局測量方法可比,即使無法實施盲法,結局測量不太可能因知曉研究對象接受的干預而受到影響或結局評估者不知曉研究對象接受的干預,結局測量的所有誤差與干預狀態無關。
本研究納入文獻的干預方式主要為抗病毒藥物治療、免疫治療和中藥治療等。多個研究顯示,洛匹那韋/利托那韋在COVID-19患者中有良好的治療效果,體現在病毒核酸轉陰時間、肺部影像學改善時間或體溫復常時間方面短于對照組[14-16],與相關指南推薦的一致[56]。而有研究顯示,在病毒核酸轉陰時間方面,洛匹那韋/利托那韋組長于對照組,并且不良反應也高于對照組[13,17]。因此本指南暫不推薦洛匹那韋/利托那韋治療任何類型的COVID-19患者[7]。李曠宇等研究顯示,與常規抗病毒治療(奧司他韋、阿比多爾、洛比那韋/利托那韋)相比,清肺排毒湯加常規抗病毒藥物治療組的住院時間、退熱時間、肺部CT好轉時間均顯著縮短[47]。因此,本指南指出輕型、普通型COVID-19患者可考慮使用清肺排毒湯治療,這與我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最新版診療方案的推薦意見一致[56]。
本文納入文獻的研究設計大多是回顧性隊列研究,設計不嚴謹、研究納入病例數少、混雜因素多,得出的結論可靠性受到一定的影響,但其滿足了COVID-19疫情背景下對臨床試驗結果的需求,仍可為后續開展COVID-19前瞻性病例對照研究、病毒陰轉規律探索等提供一些借鑒與參考。由于指南的檢索日期截至 2020 年 7 月 8日,隨著突發事件的發展,未來會獲得更多的數據和資源,故后續證據可能會發生變化。
綜上所述,雖然指南基于NRSI的相關證據對COVID-19患者的治療給出了推薦意見,但部分結論尚不能確定,仍需大樣本、長期隨訪的高質量隨機對照研究來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