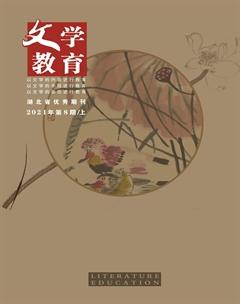作家聲音
●余華稱自己的作品都是有對應關系的
余華日前在接受采訪時說:好多讀者,甚至是一些年輕的當代文學研究者,他們都沒有讀過我過去的中短篇。我發現現在大學里面的碩士和博士,哪怕他們的論文是寫《活著》,他們也沒讀過我的中短篇。而當年那些跟我們同一時期成長起來、有些現在已經退休的評論家,閱讀風氣是完全不一樣的——如果他們研究一個作家,不讀完他全部的作品,他們是不會輕易發言的。國際上也是,當年《第七天》出版,日文版的翻譯者——一個日本教授馬上就說,這個小說讓他想到了《世事如煙》。其實我的作品,都是有點對應關系的。如果你不是做我的作品研究無所謂,如果你的論文是研究某個作家的作品,你應該把他所有的作品全部讀了,這是最起碼的要求。況且我的作品又不多,300萬字,也不是讀不過來。你說要是有3000萬字,要求太高了。現在反而有一些記者,倒是讀過我很多作品。
●張惠雯稱故鄉仍然是她寫作的富礦
張惠雯日前在接受采訪時說:還鄉者有還鄉者的孤獨,異鄉人有異鄉人的孤獨。如果說兩種孤獨感帶給讀者的感受不同,那大概是因為《在南方》里人物的孤獨是“現在進行時”,而且他們身處異鄉,這種孤獨感在讀者看來也許更可理解。而還鄉者呢,當他看到一個變了的、自己不再熟悉的故鄉,或者說“失去了”的故鄉,他的孤獨不會不強烈,但因為他本來也早已離開了此地,所以這種孤獨顯得更獨屬于他,“此地”的人或許更難以理解、共情。像我這樣旅居海外的作家,要寫的故事通常是這樣兩種:故鄉的事、居住地的事。故鄉的事總和記憶有關,也可以說,和童年、個人成長有關。而還鄉者講述有關故鄉的事,那其實并非純粹的故鄉的故事,其中肯定雜糅著還鄉者的異鄉目光、童年記憶、鄉愁基調等因素,那樣的故事和單純的中國故事就有不太一樣的風味了。我覺得這個是身居異鄉的作者才可能寫出來的,寫來也是最自然的。我17歲離開我生長的中原小縣城去了新加坡,在新加坡生活了15年之后來到美國,如今在美國又生活了11年。所以,我在國外的時間早已超過我在故鄉的時間,但我還在寫故鄉的故事。故鄉就和母語一樣,是在一個人的生命里鐫刻最深的東西,成為了我們的潛意識。就像我在小說里寫的一樣,我對它的落后、封閉、陳規陋習無論有多不滿,它仍然在我的記憶深處,是我寫作的富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