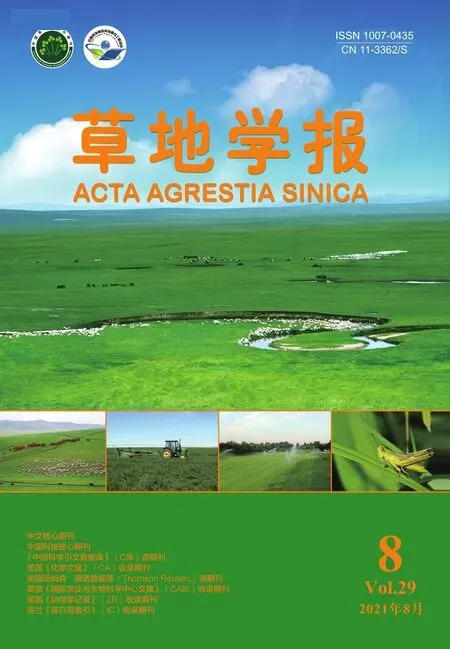呼倫貝爾草原不同利用方式對(duì)土壤微生物群落結(jié)構(gòu)的影響
曲 艷, 宋 倩, 楊合龍, 趙 坤, 趙 敏, 劉玉玲, 王德平, 戎郁萍*
(1.中國(guó)農(nóng)業(yè)大學(xué)草業(yè)科學(xué)與技術(shù)學(xué)院, 北京 100193; 2.中國(guó)草學(xué)會(huì), 北京 100193;3.包頭市園林綠化事業(yè)發(fā)展中心, 內(nèi)蒙古 包頭 014030)
土壤微生物數(shù)量龐大,種類繁多,是土壤生物的重要組成部分[1]。土壤微生物占有機(jī)質(zhì)比例較小,但直接或間接參與幾乎所有的土壤過程[2]。土壤微生物群落組成、結(jié)構(gòu)及功能發(fā)生微小的變化,表征土壤生態(tài)系統(tǒng)環(huán)境的變化[3-4]。
放牧和割草是草地資源的主要利用方式,通過移除植物地上部分,改變草地植物群落及其生長(zhǎng)環(huán)境,影響土壤微生物群落。此外,草地放牧還通過家畜排泄物的返還以及踐踏作用,直接改變土壤微生物生存環(huán)境,進(jìn)而影響土壤微生物群落[5]。長(zhǎng)期不合理或過度利用使草地植被退化,土壤環(huán)境惡化[6],影響土壤微生物群落組成及功能。關(guān)于草地利用方式對(duì)土壤微生物的影響是近年的研究熱點(diǎn)之一,李玉潔等研究表明,刈割處理下內(nèi)蒙古呼倫貝爾草原的土壤微生物磷脂脂肪酸(Phospholipid fatty acids,PLFA)總量顯著高于圍封與放牧草地,且刈割明顯提高了土壤細(xì)菌含量,但對(duì)真菌含量無顯著影響[7];邵玉琴等[8]研究發(fā)現(xiàn)土壤微生物數(shù)量隨割草頻率的增加而降低,但長(zhǎng)期圍封降低微生物在土壤養(yǎng)分轉(zhuǎn)化過程中的作用;張立朝指出叢枝菌根真菌在羊草被刈割后的補(bǔ)償生長(zhǎng)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9]。近些年關(guān)于不同利用方式對(duì)呼倫貝為草原影響的研究雖較多,但尚不完善。
本文通過對(duì)內(nèi)蒙古呼倫貝爾草原在封育、割草、連續(xù)放牧、不同時(shí)間休牧處理下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研究,系統(tǒng)地探討土壤微生物各類群組成及比值對(duì)草地利用方式的響應(yīng)特征,厘清不同的草地利用方式下土壤微生物群落結(jié)構(gòu)的變化規(guī)律及關(guān)鍵土壤環(huán)境驅(qū)動(dòng)因子,準(zhǔn)確評(píng)估土壤生態(tài)系統(tǒng)動(dòng)態(tài)變化過程,對(duì)呼倫貝爾地區(qū)合理利用草地資源具有指導(dǎo)意義。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yàn)設(shè)計(jì)
試驗(yàn)區(qū)位于內(nèi)蒙古呼倫貝爾市陳巴爾虎旗中國(guó)農(nóng)業(yè)大學(xué)草地農(nóng)業(yè)生態(tài)系統(tǒng)試驗(yàn)站(49°20′~49°26′ N,119°55′~120°09′ E,海拔628~649 m);屬半干旱大陸性季風(fēng)氣候,年均氣溫—1.2℃,年均降水量約355 mm,多集中在7—8月份;土壤類型為黑鈣土或暗栗鈣土,土壤(0~10 cm)有機(jī)碳含量為36.7 g·kg-1,全氮含量為3.7 g·kg-1,全磷含量為0.5 g·kg-1[10]。該地草地類型為溫性草甸草原,建群種為羊草(Leymuschinensis),主要植物種包括:貝加爾針茅(Stipabaicalensis)、無芒雀麥(Bromusinermis)、草地早熟禾(Poapratensis)、糙隱子草(Cleistogenessquarrosa)等。
2016—2019年,設(shè)圍封、割草、連續(xù)放牧,生長(zhǎng)季早期休牧、中期休牧及晚期休牧6個(gè)草地利用方式處理,每個(gè)處理6次重復(fù),采用拉丁方試驗(yàn)設(shè)計(jì),共36個(gè)小區(qū)。每小區(qū)面積20 m2(4 m×5 m),小區(qū)間設(shè)2 m的隔離帶。草地圍封處理(EN)全年不利用;割草地處理(CP)每年8月中旬刈割,留茬高度8 cm;放牧樣地采用模擬放牧處理,留茬高度6 cm,其中連續(xù)放牧處理(CG)每年6月中旬—9月中旬連續(xù)利用;生長(zhǎng)季早期休牧處理(GR1)于每年6月中旬—7月中旬不放牧;生長(zhǎng)季中期休牧處理(GR2)每年7月中旬—8月中旬不放牧;生長(zhǎng)季晚期休牧處理(GR3)每年8月中旬—9月中旬不放牧。放牧小區(qū)除進(jìn)行地上部分的留茬處理外,還進(jìn)行踐踏和撒施糞便處理,體重約55 kg的成年人穿釘有羊蹄的鞋子在小區(qū)內(nèi)走動(dòng),直至均勻踏遍,每次走動(dòng)可在土壤表面施加約92 kPa的壓力,符合羊在實(shí)際踐踏中產(chǎn)生的壓強(qiáng)值[11];放牧小區(qū)均撒施羊糞100 g·m-2干物質(zhì),其中連續(xù)放牧小區(qū)分3次施入,生長(zhǎng)季不同時(shí)間休牧小區(qū)分2次施入[12]。
1.2 樣品采集與處理
2019年8月底,用內(nèi)徑5 cm的土鉆在各小區(qū)四角及中間方位區(qū)域各隨機(jī)取10 cm土壤樣品,充分混合后,取出約500 g裝入自封袋,放入冰盒帶回實(shí)驗(yàn)室。土壤樣品過2 mm篩子后均分2份,一份室內(nèi)風(fēng)干,用于土壤理化指標(biāo)測(cè)定,另一份放入—80℃冰箱中保存,用于測(cè)定土壤硝態(tài)氮、銨態(tài)氮,微生物量碳、氮及土壤微生物磷脂脂肪酸含量等。
1.3 土壤指標(biāo)測(cè)定
1.3.1土壤理化指標(biāo) 土壤容重測(cè)定采用環(huán)刀法;土壤pH值測(cè)定采用酸度計(jì)(上海雷磁儀器廠,上海);土壤電導(dǎo)率測(cè)定采用電導(dǎo)儀(上海雷磁儀器廠,上海);土壤全碳和全氮含量測(cè)定采用元素分析儀(Elementar Vario EL C/N analyzer,Germany);土壤全磷和速效磷含量采用鉬銻抗比色法測(cè)定[13];土壤銨態(tài)氮、硝態(tài)氮含量測(cè)定采用流動(dòng)分析儀(AutoAnalyser 3,Seal Analytical,Norderstedt,Germany)。
1.3.2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含量測(cè)定 準(zhǔn)確稱取40 g新鮮土樣放入燒杯中,調(diào)節(jié)土壤含水量(田間持水量的40%)后放入底部有少量水的保鮮盒中密封,于25℃下預(yù)培養(yǎng)7 d。每個(gè)預(yù)處理后的樣品取20 g,均分為2份,一份在真空干燥器中用無水三氯甲烷熏蒸處理,一份為不熏蒸的對(duì)照樣品。兩份樣品均加40 ml的K2SO4溶液(0.5 mol·L-1),振蕩過濾后,用總有機(jī)碳氮分析儀(Multi N/C 3100,Analyticjena,Germany)測(cè)定濾液中的有機(jī)碳、氮的含量[14]。
1.3.3土壤微生物磷脂脂肪酸(PLFA)的測(cè)定與分析 參考孫建[15]的方法,采用Agilent 6890氣相色譜儀(Agilent Technologies,Palo Alto,CA)與微生物辨別軟件(MIDI Inc.,Newark,NJ)分析磷脂脂肪酸種類。含量以PLFA 19∶0作為內(nèi)標(biāo)來進(jìn)行定量計(jì)算,其公式如下:

式中,A為19∶0的峰值,B為目標(biāo)PLFA的峰值。總微生物生物量用各PLFA含量加和表示。
根據(jù)已發(fā)表的文獻(xiàn)中特定磷酸脂肪酸(PLFA)標(biāo)記[16],對(duì)土壤微生物群落類群進(jìn)行表征。其中將14∶00,15∶00,16∶00,17∶00,18∶1ω7c,18∶00,20∶00表征為一般性細(xì)菌;13∶0 iso,14∶0 iso,15∶0anteiso,15∶0 iso,16∶0 iso,17∶0 iso,17∶0 anteiso,18∶0 iso表征為革蘭氏陽(yáng)性菌;6∶1ω9c,16∶1ω7c,17∶0 cycloω7c,18∶1ω5c,19∶0 cycloω7c表征為革蘭氏陰性菌;18∶3ω6c,18∶2ω6c,18∶1ω9c表征為真菌;16∶1ω5表征為菌根真菌;16∶0 10-methyl,20∶0 10-methyl表征為放線菌。
1.4 數(shù)據(jù)處理
采用Microsoft Excel 2019進(jìn)行原始數(shù)據(jù)整合,利用SAS 9.4軟件對(duì)不同草地利用方式間的土壤理化性質(zhì)與各類群土壤微生物含量作單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差異顯著性水平為P<0.05,并借助Canoco 5軟件對(duì)土壤理化性質(zhì)與土壤微生物群落結(jié)構(gòu)進(jìn)行RDA冗余分析。利用Sigmaplot14.0將數(shù)據(jù)可視化處理,采用箱式圖展示土壤微生物量碳、氮數(shù)據(jù)位置及分散等信息。數(shù)據(jù)均以平均值±標(biāo)準(zhǔn)誤差表示。
2 結(jié)果與分析
2.1 草地不同利用方式下土壤理化性質(zhì)分析
草地利用方式對(duì)呼倫貝爾草原土壤理化性質(zhì)的影響不同(表1)。土壤pH值、土壤容重和全磷含量在各個(gè)草地利用方式下均無顯著性差異。而CG,GR2,GR3處理下土壤電導(dǎo)率顯著高于CP處理(P<0.05),分別提高了17.69%,10.47%,19.79%。土壤全碳和全氮含量在各處理下的變化趨勢(shì)一致,均在CG處理下達(dá)到最高值,顯著高于CP處理,且與其他處理無顯著差異。EN處理下的土壤有效氮和速效磷含量均最高,其中土壤硝態(tài)氮含量較CP,GR處理顯著升高,并分別提高了58.55%,40.57%,28.24%,23.28%;土壤銨態(tài)氮含量顯著高于CG,GR2處理下,分別提高了26.41%,23.73%;而土壤速效磷含量則顯著高于CP處理,提高了39.95%。

表1 草地利用方式對(duì)呼倫貝爾草原土壤理化性質(zhì)的影響Table 1 The influence of grassland utilization on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Hulunbuir grassland soil
2.2 草地不同利用方式對(duì)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的影響
不同的草地利用方式下(EN,CP,CG)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含量均表現(xiàn)為CP>CG>EN;隨著生長(zhǎng)季休牧?xí)r期的延后,土壤微生物量碳含量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趨勢(shì),而土壤微生物量氮含量卻呈逐漸下降的趨勢(shì)(圖1)。草地利用方式對(duì)土壤微生物量碳/氮的影響無顯著差異(圖2)。

圖1 不同草地利用方式對(duì)呼倫貝爾草原土壤微生物量碳、氮含量的影響Fig.1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grassland utilization methods on soil microbial biomass carbon and nitrogen content in Hulunbuir grassland

圖2 不同草地利用方式對(duì)呼倫貝爾草原土壤微生物量碳/氮比值的影響Fig.2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grassland utilization methods on the soil microbial biomass carbon/nitrogen ratio in Hulunbuir grassland
2.3 草地不同利用方式對(duì)土壤微生物群落結(jié)構(gòu)的影響
土壤微生物PLFA總濃度及各類群濃度在不同的草地利用方式下存在一定的差異(表2)。CP處理下微生物PLFA總濃度低于其他處理,且顯著低于GR3處理(P<0.05),降低37.60%,休牧處理(GR1,GR2,GR3)下PLFA總濃度均高于EN,CP,CG處理,且隨著休牧?xí)r間的推后,PLFA總濃度呈升高趨勢(shì);各微生物類群含量與PLFA總量在各處理下變化情況大體一致,但值得一提的是,真菌與革蘭氏陰性菌PLFA含量在休牧放牧下有所改變,真菌PLFA含量在GR2處理下最低,而革蘭氏陰性菌則在GR2處理下濃度最高。

表2 不同草地利用方式對(duì)呼倫貝爾草原土壤微生物菌群PLFA含量的影響Table 2 Effects of different grassland utilization methods on the PLFA content of soil microbial flora in Hulunbuir grassland
土壤微生物PLFA比值變化(表3)結(jié)果顯示,細(xì)菌/真菌PLFA濃度比在各處理下均無顯著性差異,GR2與GR3處理下變異系數(shù)同時(shí)達(dá)到最大,CP處理下最小;對(duì)革蘭氏陽(yáng)性菌/革蘭氏陰性菌(G+/G-)PLFA濃度比而言,CG處理下比值最高,顯著高于GR2處理(P<0.05),但與其他處理差異不顯著。EN,CP與CG處理下G+/G-整體上高于休牧處理(GR1,GR2,GR3)。從比值變異程度來看,CG處理下的G+/G-比值變異系數(shù)最大,而GR2處理最小,與細(xì)菌/真菌相反。

表3 草地利用方式對(duì)呼倫貝爾草原土壤微生物PLFA比值的影響Table 3 The influence of grassland utilization on the ratio of soil microbial PLFA in Hulunbuir grassland
2.4 土壤微生物群落結(jié)構(gòu)與土壤理化性質(zhì)的關(guān)系
對(duì)土壤理化性質(zhì)指標(biāo)和微生物群落結(jié)構(gòu)間的關(guān)系進(jìn)行冗余分析(圖3),結(jié)果表明,土壤pH值、電導(dǎo)率、硝態(tài)氮和銨態(tài)氮含量等變量可以解釋69.2%的微生物群落變異,擬合效果較可靠。其中細(xì)菌、革蘭氏陽(yáng)性菌、革蘭氏陰性菌、真菌、放線菌及總磷酸脂肪酸含量與土壤電導(dǎo)率、銨態(tài)氮含量呈顯著的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與土壤pH值呈顯著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且真菌與硝態(tài)氮含量具有顯著的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細(xì)菌/真菌與土壤硝態(tài)氮含量、電導(dǎo)率呈顯著的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與土壤pH值呈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與土壤銨態(tài)氮含量幾乎無關(guān);革蘭氏陽(yáng)性菌/革蘭氏陰性菌與土壤硝態(tài)氮含量、pH值呈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與電導(dǎo)率和銨態(tài)氮含量呈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此外細(xì)菌、革蘭氏陽(yáng)性菌、革蘭氏陰性菌、真菌、放線菌及總磷酸脂肪酸含量的正相關(guān)性極強(qiáng);土壤電導(dǎo)率與銨態(tài)氮、硝態(tài)氮含量呈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與土壤pH值呈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而銨態(tài)氮和硝態(tài)氮含量卻呈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

圖3 呼倫貝爾草原區(qū)土壤微生物群落結(jié)構(gòu)與土壤理化性質(zhì)的冗余分析Fig.3 Redundancy analysis of soil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in Hulunbuir grassland area注:銨態(tài)氮;硝態(tài)氮;pH,pH值;Ec,電導(dǎo)率;bacteria,細(xì)菌;G+,革蘭氏陽(yáng)性菌;G-,革蘭氏陰性菌;fungi,真菌;actinomycetes,放線菌;Total PLFA,總磷脂脂肪酸;bacteria/ fungi,細(xì)菌/真菌;G+/G-,革蘭氏陽(yáng)性菌/革蘭氏陰性菌Note:N nitrogen;pH,pH value;Ec,conductivity;bacteria,bacteria;G+,Gram-positive bacteria;G-,Gram-negative bacteria;Fungi,fungi;actinomycetes,actinomycetes;Total PLFA,total phospholipid fatty acids;Bacteria/fungi,bacteria/ fungi;G+/G-,Gram-positive bacteria/Gram-negative bacteria
3 討論
土壤微生物對(duì)土壤元素和養(yǎng)分的循環(huán)及轉(zhuǎn)化具有關(guān)鍵的作用。此外,土壤微生物作為周圍環(huán)境變化的指示因子,能夠敏感且快速做出甄別性反應(yīng)[7,17]。草地利用方式的差異通常會(huì)導(dǎo)致土壤環(huán)境因子(包括土壤物理及化學(xué)特征)出現(xiàn)強(qiáng)烈變化,進(jìn)而影響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數(shù)量及結(jié)構(gòu)[18-20]。對(duì)圍欄禁牧、連續(xù)放牧和休牧(早期休牧、中期休牧、晚期休牧)3種草地利用方式下土壤的理化性質(zhì)指標(biāo)及土壤微生物群落結(jié)構(gòu)的變化進(jìn)行研究,發(fā)現(xiàn)禁牧處理下土壤總PLFA量最高,可見禁牧有助于土壤肥力的恢復(fù),斯貴才等[21]也曾指出圍封利于土壤微生物生長(zhǎng)繁衍。在放牧形式下,隨著休牧?xí)r間推后,各類群PLFA含量總和呈增高趨勢(shì),這可能與植物體生長(zhǎng)發(fā)育程度有關(guān),當(dāng)植物進(jìn)入生長(zhǎng)發(fā)育的成熟階段,對(duì)土壤養(yǎng)分的需求更大,并促進(jìn)土壤中微生物的活動(dòng),使土壤微生物PLFA含量升高;從微生物類群比值角度看,革蘭氏陽(yáng)性菌比革蘭氏陰性菌對(duì)養(yǎng)分的吸收能力強(qiáng),更能適應(yīng)不良的環(huán)境條件[22],二者比值可反映土壤底物即有機(jī)質(zhì)供應(yīng)水平,底物養(yǎng)分有機(jī)氮與其比值(G+/G-)呈負(fù)向關(guān)系,即前者越多,比值便越小,進(jìn)而對(duì)微生物的營(yíng)養(yǎng)脅迫越高[23];表3結(jié)果顯示連續(xù)放牧(CG)下G+/G-最高,說明連續(xù)放牧下草地土壤底物供給碳、氮等養(yǎng)分的能力最低,造成了微生物的營(yíng)養(yǎng)脅迫。當(dāng)草地連續(xù)放牧利用時(shí),地上、地下生物量均降低,凋落物量減少,養(yǎng)分循環(huán)減緩[24]。而中期休牧處理下的G+/G-最低,可見生長(zhǎng)季中期休牧使微生物得到很好的營(yíng)養(yǎng)供給,有助于整個(gè)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可持續(xù)運(yùn)行。此外細(xì)菌/真菌比值可表征兩個(gè)微生物類群的相對(duì)豐度及生態(tài)系統(tǒng)穩(wěn)定性,比值越低說明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緩沖性和抗干擾能力越強(qiáng)[23],表3結(jié)果顯示各草地利用方式下細(xì)菌/真菌均無顯著性差異,表明不同草地利用方式對(duì)生態(tài)系統(tǒng)的緩沖性能和抗干擾能力無明顯影響。但這僅為單一特征的指向,不足以說明生態(tài)系統(tǒng)復(fù)雜的功能特性,因此關(guān)于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抵抗性和緩沖性對(duì)草地利用方式的響應(yīng)機(jī)制還需更多的指標(biāo)進(jìn)行全面的研究。
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數(shù)量和組成等特征可快速的反映土壤質(zhì)量情況[25-26],土壤理化性質(zhì)的改變便成為了致使微生物代謝特征發(fā)生變化的關(guān)鍵原因[27]。草地利用方式的不同,土壤物理性狀及養(yǎng)分含量會(huì)出現(xiàn)較大的差異[28],進(jìn)一步土壤微生物結(jié)構(gòu)功能受到顯著影響[29]。根據(jù)對(duì)土壤理化性質(zhì)指標(biāo)及土壤微生物群落組成結(jié)構(gòu)進(jìn)行約束排序,權(quán)衡模型的可靠性,僅篩選出土壤電導(dǎo)率、pH值、銨態(tài)氮和硝態(tài)氮4種土壤環(huán)境因子來分析與微生物間的相互關(guān)系,可見土壤環(huán)境因子雖眾多,但不一定均可直接作用于微生物。冗余分析(RDA)結(jié)果顯示總磷酸脂肪酸及各微生物類群均與土壤電導(dǎo)率和銨態(tài)氮呈極強(qiáng)的正相關(guān)關(guān)系,卻與pH值呈極強(qiáng)的負(fù)相關(guān)關(guān)系。土壤電導(dǎo)率的升高可在一定程度上加強(qiáng)土壤養(yǎng)分的轉(zhuǎn)化,改變其存在狀態(tài)及有效性,且土壤底物氮的數(shù)量對(duì)于微生物數(shù)量及功能存在直接的影響。偏堿性土壤會(huì)為微生物各類群提供更利的生存環(huán)境,這與馬大龍等[30]在大興安嶺多年凍土區(qū)及韓世忠等[31]在中亞熱帶地區(qū)米櫧天然林對(duì)土壤微生物進(jìn)行的研究結(jié)果相悖,可見氣候因子中的氣溫及降水等對(duì)此過程產(chǎn)生的復(fù)雜調(diào)控是不可忽視的。土壤pH值、電導(dǎo)率不僅對(duì)微生物群落數(shù)量、組成及結(jié)構(gòu)存在一定的影響作用,還積極調(diào)控著微生物功能走向,由此推斷土壤鹽堿度與pH值可作為呼倫貝爾地區(qū)草原區(qū)域微生物的關(guān)鍵預(yù)測(cè)指標(biāo)。
4 結(jié)論
通過對(duì)土壤微生物群落結(jié)構(gòu)對(duì)草地利用方式的響應(yīng)研究,發(fā)現(xiàn)休牧處理下土壤微生物數(shù)量高于其他的草地利用方式,且休牧期推后更利于土壤微生物的生長(zhǎng)繁殖;此外生長(zhǎng)季中期休牧?xí)岣咄寥赖孜锕┙o微生物養(yǎng)分的能力;冗余分析顯示電導(dǎo)率高且偏堿性土壤會(huì)為微生物提供更有利的生存環(huán)境。因此,將土壤鹽堿度和pH值作為呼倫貝爾草原區(qū)域微生物群落結(jié)構(gòu)及功能的關(guān)鍵預(yù)測(cè)指標(biā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