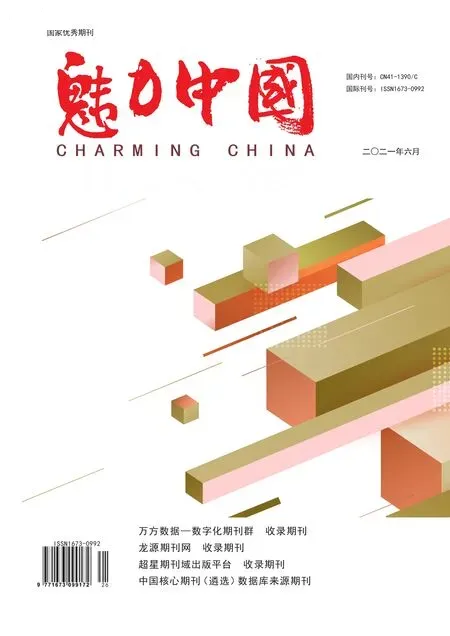江南文化視野下朱熹蒙學教育的思想探究
張怡
(銅陵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 銅陵 244000)
江南文化,以徽州文化和吳越文化為代表,其中徽州文化是中國三大地域文化之一。在徽州文化所涉獵的各個領域中,可能以新安理學作為其突出代表。眾所周知,新安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對理學乃至整個徽州社會經濟文化將近產生了600 多年的影響,時至今日,其思想仍是各學術界探討的重要對象。而在朱熹的教育思想中,以其蒙學為基點,對當代啟蒙孩童教育仍有值得借鑒之處。
蒙學是中國古代對幼兒早期教育的一個總稱,由于孩童“智識未開”,需要經過蒙學對智力上的啟發、道德涵養的積淀,從而培養“圣賢坯璞”。《易經·蒙卦》有曰:“蒙以養正,圣功也。”其意可見蒙學實為啟蒙之學,是為了培養孩童純正不雜的品質修養,以造就君子人格。
《小學》《童蒙須知》是朱熹在其教育領域里的兩部代表之作,在一定程度上總結了先秦教育理念和自身的教育經驗,其中的修心、立身、明德等思想與儒家先賢具有一脈相承之處。當然,這些理念對于我們在當代塑造孩童品格修養的形成過程中起著打好根基的基礎性作用。
一、修心
在孟子的修養論體系中,孟軻的道德修養標準之一是“不動心”,何為“不動心”,即內心牢守道德原則,不為外界的誘惑所動。而這個過程的歷練非一日之功,所以就需要在童蒙之時給予慢慢修養,即是修心。而怎樣修心,古人覺得讀書是最能修心的。在《童蒙須知》讀書寫字之篇中,處處提及該如何讀書,將讀書寫字之規范表述的尤其細致,但朱子實則在表達在讀書寫字過程中應該怎樣修心。如“凡讀書,須整頓幾案,令潔凈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子細分明。”朱熹認為在讀書時須得書桌整齊,端正書本,仔細閱讀,這個其實是一個讀書態度的問題,而態度則體現了讀書時心緒是否靜和且集中,這一過程就是在修心了,如若在讀書時心不在焉、心有旁騖,自然“讀書百遍,其義不自見”;又如“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草。凡寫文字,須要子細看本,不可差訛。”寫字時須得一筆一畫、字跡端正忌潦草,不是要求寫的多么好看,但至少工整潔凈,這些要求在現在的教育體系中仍是受到極大關注的,特別是在電腦、手機等一系列電子產品的相應問世,很多孩童的寫字規范都難以得到重視,而練字這一必修課在現今的教育體制下不光是童蒙之學還是受知之學,乃至大學之學,都應該得到提倡與普及的,練字是修心的一個比較好的方法,所謂“字如其人”,一個人的字跡潦草以至難以識辨,在其背后,多半也是心緒浮躁、隨意散漫之人,所以孩童在學寫字過程中不可心浮氣躁。
讀書可修心,日常行為細致,也略可修心,如《小學》有云:“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小學》強調在平時的生活中,孩童要對父母孝、對兄弟愛、對知識博,對父母兄弟的孝、愛要在與他們交往中顯現出來,對知識的寬博要涵于內心,不可外揚,學無止境,不要刻意彰顯自己的文識,而這就是在實踐的過程中實現修心,書本上的知識要運用到具體生活當中才會有所切身感悟。儒家之學的一個根本體現就是知行合一:“先行其言而后從之” (《論語·為政》),乃君子也。所以孩童在讀書寫字的過程中可獲得修心的要領,在后期的實踐活動中了解修心之本,然則“智識可開”。
“修心”相比較于當代孩童的啟蒙教育是有相似之處的。現今的早期教育活動可謂從胎教即已開始,那么古代修心這一過程也有異曲同工之處。《小學》有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之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若孕婦身懷正氣,那么孩子會先天受稟此氣,自然過人。這可能算是中國胎教之“鼻祖”。現在盛行的胎教的諸如音樂、運動、視力等課程,與這里所說的母體感化子體,是有很大的相似性的。可見,“修心”對于孩童之蒙學啟發已于幼小,甚至是胎兒時期就已經有之教育目的,那么,心之修明,則可立身。
二、立身
立身可謂是為人處世之根本,身立正,則為人處世之道則然。“立身行道,揚名於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孝經·開宗明義》)《孝經》是儒家倫理典籍之范,強調孝道是立身的基礎,才能流芳千古。“百善孝為先”,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家長制無不體現著孝道,而我們現在所提倡的和諧社會的內容之一就是行孝悌,愛家人。那么作為立身的根本——孝,對于接受童蒙之學的孩童應該如何培養呢?《童蒙須知》雜事細宜中曰:“凡出外及歸,必于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凡侍長者之側,必正立拱手。有所問,則必誠實對,言不可忘。”這里說的是與長輩相處之道:二意。何為二意,即敬意與誠意。出門與歸來向長輩打招呼;在長輩面前端正身姿是對長輩的尊重,即是敬意;長輩與你說話,回答皆是實話,不帶謊騙,既是對長輩的尊重,也是對長輩表達的誠意。孩童時期是很難理解孝道的踐行,朱熹在這里所說的相處原則對于童蒙來說是易于做到的。《小學》在明倫篇中所講的“父子之親”“長幼有序”皆是對孩童應該如何實現孝道的具體條目的規范,雖然其中有些內容是不適應現在教育的模式體系,但是對于啟蒙孩子立身的根本還是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的。
當然,立身也不完全取決于孝道的施行,對于當代的啟蒙孩童心智,立身還需要知禮:“子曰:‘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 “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孔子對于君子人格形成要求其一就是要知禮:言語謹慎不僭越,做事勤勉,文采有眾,這些其實都是立身知禮的表現。朱子對于孩童立身知禮方面也有所規定,如《小學》有云:“《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立必正方,不傾聽。’”這是說要教育孩子不打誑語,誑語即是撒謊,并且站立端正,聽話不側耳,這就是知禮。孩童心性不定,心緒不穩,需要一定的約束規范,而在與人交往中的言行舉止即可看出孩童的知禮程度,不撒謊、忌站立搖晃、不側耳,這三點對于當代的孩童立身也是需要強調的,孩童在平常的細致生活中注重禮儀規范,定心性、穩心緒,則“心智應開”。
俗話說:“正心先正身,正身先正衣。”或者我們也說:“人靠衣裝馬靠鞍。”這不是說我們穿的衣服需要多么昂貴多么奢靡,而是在強調衣履的端正整潔。在《童蒙須知》衣服冠履篇中曰:“大抵為人,先要身體端整。自冠巾、衣服、鞋襪皆須收拾愛護,常令潔凈整齊。”朱熹認為,做人首先得做到身體端正整潔。現在由于經濟水平高,孩童的衣服樣式紛繁多樣,雖然不需要刻意要求服飾的莊重干凈,但是要求孩童在穿衣戴帽時注重儀表還是必要的,在這個過程中是在培養孩子對生活的一種認真、尊重的態度。那么身之立正,即可明德。
三、明德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這是《大學》里的第一句話,而后對于明德的表述多用于帝王之道,意為帝王自身德明而后明德于天下,如“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成相》) “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太王也。”強調的是君王應該具備的德行。對于孩童來說,所謂“明德”則是辨是非,知道義。孩童心智不純熟,性情不成型,在日常的生活中就需要慢慢完善,這一過程就可“明德”。“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孔子教育弟子時要求其弟子要相互學習,取其之長補己之短,,這對于孩童乃至成人都是需要的品德,可以說這是評價一人德品與否的標準之一。《童蒙須知》言語步趨篇:“凡聞人所為不善,下至婢仆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爾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這是說我們在面對別人的錯誤時應該采取的態度,朱熹給的答案是給予寬容,使其知改,并反省自身。孩童在對自己及別人的錯誤時,要不逃避,要不宣揚,這對于自身及旁人的品格修養的塑造都是有所鐫損的。孩童蒙學之時,在面對自己的錯誤和別人的錯誤時所持有的心態是關系到成人之后為人處事、待人接物的態度,所以當出現這樣的情況時,孩童首先需要一份真誠的心志去對待錯誤,然后寬容的心態去允許別人或自己改正錯誤,而后在進行反思,所謂“君子坦蕩蕩”正是擁有這份坦蕩的胸懷與涵養。對于現時代的孩子來說,培養了這樣坦蕩的德品,同時也明白了是非如何取舍、道義如何實現。在教育孩子的過程中,讓他們敢于面對錯誤,不管這種錯來自于誰,這樣他們的成長環境就是真實的,而不是現在出現的一些包裝。
《小學》以立教、明倫、敬身這三章來教予孩童應該如何明德自身、修正德品,雖然其中一些內容放在當今有許多有待商榷之處,但其中內含的愛親、敬長、尊師、親友之道義是當今兒童直至成人都應該借鑒于當世之道的,如“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宴席之間,長幼座位,這都是有講究的,我們平常所說的“坐上席”即是對于長者、長輩的一種尊敬,也體現了一種德品。孩童不諳世事,在平常的行為中加以教導,那么孩子等長大進入社會后,他的這種“明德”之智也是其在社會立足的優勢之一。修心、立身、明德皆備,其蒙學之思仍難以全論,童蒙之學的精髓綿延至今,其深刻可行之處不亞于今日之啟蒙早教,略論一二,以求深知。
江南,意為江之南,半城山半城水,山水養才子,水山育文化。江南文化所涉及的領域紛繁多雜,對于當代城市繁榮與社會發展起著一定的思想借用之處,尤其是近些年對國學的探討之熱,更引發了對于當下孩童之蒙學深思。徽州文化作為江南文化的一條分支,其蘊含的新安理學及徽派考據學中深藏的童蒙之思對于現在教育界內引發的兒童早教之浪潮仍有許多可考可慮之處。蒙學啟發余多,只稍微探,仍有許多漏缺之處,見諒余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