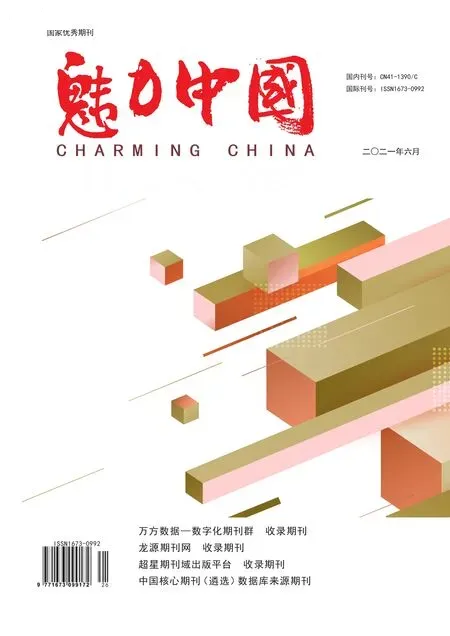學科交叉融合建設的實踐與思考
——以坭興陶書法雕刻裝飾課程教學為例
李琦苑
(北部灣大學陶瓷與設計學院,廣西 欽州 535000)
書法創造伊始,就在實用的基礎上走上藝術美的方向,成為表達民族美感的工具,記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燦爛成就。她屬于造型藝術的范疇,具有藝術的一般特點和共同性質。在生活中應用非常廣泛,陶瓷、楹聯、牌匾隨處可見。陶瓷除了其實用性外同樣也以文化的符號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
一、書法入陶的美學個性的表現
書法入陶,從古就有,從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的陶片上我們會發現有刻畫或者繪制的文字符號,從當時實用角度來講,陶文字承載的是記錄的使命,而今天我們更多的是從欣賞的角度出發,挖掘它們的美學價值。今天我們看到很多古今陶器都刻有書法,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都能體現出一定的審美價值。書法與陶,其二者的結合富有鮮明的美學個性,主要體現出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和諧自然的追求
中國傳統藝術思想重視人與物、用與美、文與質、形與神、心與手、才與藝等因素相互間的關系,主張“和”與“宜”。對“和”與“宜”之理想境界的追求,使中國傳統藝術呈現出高度的和諧性:外觀的物質形態與內涵的精神意蘊和諧統一,實用性與審美性的和諧統一,感性關系與理性規范的和諧統一,材質工技與意匠營構的和諧統一。
(二)對思想意涵的體現
書法入陶,它強調物用的感官愉快與審美的情感滿足的聯系,而且同時要求這種聯系符合倫理道德規范。受制于強烈的倫理意識,中國傳統工藝造物通常含有特定的寓意,往往借助造型、體量、尺度、色彩或紋飾來象征地喻示倫理道德觀念。從歷代各種材質的器物上看,其附帶的文字內容多與作者的主觀情感、審美情趣、思想觀念以及社會生活息息相關。在作品中,根據不同的需要,以不同的詞句表達,通常以吉祥、祝福、美譽、勵志等積極向上的文字作為主題。從此方面看,書法元素在陶器裝飾上的應用,不單是視覺享受的需要,陶更是成為一種載體,形成獨特的文化藝術,賦予深邃的內涵,蘊含了藝術家的情感和智慧,體現了社會生活的特征,成為消費者情感需要和人文需要的追求,這也可視為是對傳統文化的一種呼喚。
(三)對情懷意趣的寄托
中國傳統藝術思想重視材料的自然品質,主張“理材”、“因材施藝”,要求“相物而賦形,范質而施采。”中國傳統工藝在造型或裝飾上總是尊重材料的規定性,充分利用或顯露材料的天生麗質,這種卓越的意匠使中國工藝造物具有自然天真、恬淡優雅的趣味和情致。書法在使用的基礎上更講究的是藝術內涵。陶瓷裝飾以書法藝術,除注重精神文化內涵外,同時書法應用于陶質材料上裝飾書法,比布帛、竹簡、紙張上書寫文字更易于保存。
陶器上的刻畫文字,發揮了漢字本身所包含的形象性的特征,加上運用到刻刀以表現體態風格的要求,和我國傳統書畫的審美原則聯系起來,借以抒發作者的思想情感,并給人以美感享受。刻在陶器上的字,其存在性即表明了其藝術范疇,它不能與作為應用工具的文字等量齊觀,正如不能把走路和舞蹈,交談與演講混為一談一樣,而應該有它自身的規律。
藝術,它總是以形象來反映生活的,這種反映,不是簡單機械的,而是積極能動的。我們每看到一幀好的書法作品,往往被激發而產生一種情緒的震動,而面對著一般印刷體或者抄寫得平庸的手筆,即使是同樣內容,也很難激發起共鳴。
二、書法藝術在陶器裝飾上的技能保障
書法作為一種文化符號應用于陶器裝飾上,審美觀賞的立場最為優先。作品視覺效果的優劣要以書寫技能作為保障和根基。書法與陶器的藝術性格既獨立又相互依附。技法、技巧、技術、技能、意蘊等諸多因素的相互融合與支撐如何恰到好處的作用于最終作品,是教師在開展課堂教學過程中需要關注和思考的焦點。在高校產品設計專業課程設置中,應加大書法課程比重。對于陶器書法雕刻裝飾而言,純粹依仗書法技能,并沒有絕對的意義。書法藝術只有作用于陶器作品整體而恰到好處地發揮其局部能力的技能,才能造就令人滿意的藝術效果。一件完美的作品,應是審美、文化、技能的綜合體現,包括視覺形式、主題內容、技法表現、氛圍塑造和創新點、獨特點。書法作為一種“漢字符號”,這是其他視覺藝術所沒有的。它既是視覺圖像的一個組成部分,又有著作為歷史文化以及古文字學到現代文字學學術的屬性。陶器造型的完美與其裝飾上“漢字符號”應用的準確同等重要。
書法作為一種裝飾元素,既可作為具體抽象符號的表達,又具有可讀的實用價值。它沒有直接對應的自然物象,不如繪畫中的人物、動物及景象,沒有直觀的視覺印象,觀賞者不能根據常識和經驗直接判斷好不好、像不像。如果沒有經過系統的視覺訓練、沒有足夠的文史領域知識儲備,很難從專業角度對其藝術效果的優劣做出評價和判斷。這就要求在實施教學過程中,必須先從漢字入手,掌握從古至今漢字的書體類型及風格特征;其次掌握書法美學的表現形式及欣賞方法;最后在遵循漢字規范、書法形式法則及設計美學認知的基礎上確定創作思路。
書法藝術融入產品設計專業陶器雕刻課程教學,作為一種表現美的裝飾元素,其載體是陶器本身。它與陶器的互相配合,使并非一定與美搭上關系的純粹物質具有了美的價值。書法與陶的結合,因材料的特殊性影響(質地、外觀形狀、表現手法),形成了有別于竹書、木書、絹書、帛書和紙書的獨特美感。陶,作為一種物質載體,誘發了書法藝術表現朝多樣化發展,并為其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場地。
陶器堅實的質地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書法線條的構成,但通過人為的藝術構思和對材料的駕馭,這種制約或許會變成成就另一種藝術效果的產生。
陶器上的書法通常不是通過書寫完成,而是以刻鐫的方式,因此很難保留書寫產生的枯、濕、濃、淡,只能看到輕、重、粗、細的線條痕跡。
三、書法作為一種裝飾元素在陶器上的應用方式
(一)刀法
陶刻一般分為干刻和濕刻兩種,干刻通常為燒制前刻,即待陶器塑型完成風干定型后刻,經摹寫后單刀完成、輔之以復刀,可也直接單刀刻寫。濕刻即在濕坯上進行,主要借助木質泥塑刀或塑料片進行勾勒、描寫,通常見于浮雕和透雕。
陶刻的刀法與書法的筆法相似,又不完全相同,二者在審美標準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卻不能機械類比。在執刀姿勢上,有三種常用的方法:一是五指執刀,大拇指、食指、中指、無名指執刀,小拇指抵住無名指,刀口向下,刀桿傾斜;二是三指執刀,大拇指、食指、中指執刀,無名指、食指抵住中指;三是五指握拳執刀,大拇指在外,其余四指卷向掌心。前兩種執刀法較靈活,發力及運動軌跡接近于書寫的狀態,第三種執刀法力量較強,適合刻鐫大型器物表達粗獷的風格。陶刻的刀法既有毛筆的情趣又有刀刻的趣味,有厚重感、有金石味、筆意刀味,能表現輕重頓挫的變化。明朱簡《印章要論》指出:“刀法者,所以傳筆法者也。刀筆渾融無跡可尋,神品也;有筆無刀,妙品也;有刀無筆,能品也;刀、筆之外而有別趣者,逸品也。”雖然論述的是篆刻刀法,但與陶刻同理。以刀代筆,單刀側入,刻鐫于晾干后的砂質泥坯上,崩屑紛落,金石氣十足。此外也有少數在燒制好的陶體上進行刻鑿,但由于燒成后的陶土質地堅硬,直接刻在器形上的成功率較低,不適用于刻制精美的器物,可用于陶印或者碑版刻制。
借鑒紫砂器的刻款,其在20 世紀初開始,在茶壺上一面刻山水花鳥、一面刻文字的情況多有,當時出現了專門從事刻款的藝人,詩文多見于《唐詩三百首》《千家詩》。陶藝與金石書畫相結合,使得一般意義上的器物充溢著書卷氣。
(二)章法
陶以書法作為裝飾,視覺效果是刻成后刀法的顯露。一件作品有無神采,往往是刀法決定的,而刀法也要依賴于字法與章法才能顯現其價值。章法主要是字與外觀形狀的關系。原則是自上而下,從右往左。根據詩文內容與器形,在尊重字勢的前提下,保持自然韻味的同時,通過字法的增減、挪移和取勢,從局部到整體,宏觀把控字形結構、線條、章法之間的關系,既要慘淡經營,又要出自自然。
(三)格調
縱觀中國陶瓷發展史上的的每一個品類、造型和紋飾的創新和審美變化,都是由當時的審美導向所左右的。它可體現雄渾、濃烈的陽剛之美,也可體現純真、樸素的自然之美。中國人崇尚自然,所以常常要講究“天人合一”,應用到藝術上,就是“心物合一”。書法作為一種裝飾元素應用于陶器的美化,書體風格的選擇可直接影響整個陶器的氣質。在循序外化的紋飾美和內化的質地美相符、文質相契的藝術主張前提下,哪種書體更適合表達浪漫意味,頌揚英雄氣概的詩文更適合哪種風格的字體,這便需要有文字學和書法美學基本常識和原理的支撐。書法美學大致可分為端莊雄偉美,如《張遷碑》《張猛龍碑》《麻姑仙壇記》等;怪誕奇崛美,如《爨龍顏碑》《爨寶子碑》《天發神讖碑》,張旭《古詩四帖》,懷素《自敘帖》等;工整精細美,如王羲之《樂毅論》《唐靈飛經》,文征明《草堂十志》等;飄逸秀麗美,如《虢季子半盤》,王羲之《蘭亭序》,楊凝式《韭花帖》等;古樸美,如王羲之《黃庭經》,鐘繇《宣示表》,陸機《平復帖》等。
陶器制作,一方面作為滿足日常使用需求的實用品,一方面又是以滿足視覺感官為主要目的的藝術品,是實用性和藝術性的結合。中國陶瓷有著優秀的歷史,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發展取決于政治、經濟、思想、民族和宗教等諸多因素,并受審美觀念和手工技術水平的影響。其與同樣作為中國文化精髓的書法相結合,實質是藝術修養、天賦悟性、哲思人格、心靈理念的巧妙融合,通過型制和紋飾來表達。
在高校藝術課程教學中,解決如何使不同藝術學科在表現形態上實現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真正融合,形成復合的藝術整體的問題,除了引導學生在藝術專業上必須有良好的造詣之外,還必須在文學、史學、哲學上有所積累與建樹。吸收不同學科文化的營養,在產品設計專業教學中,融于詩、文、書、畫等傳統文化思想內涵,使學生的思想和創作手法更為豐富,創作出更多更優秀的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