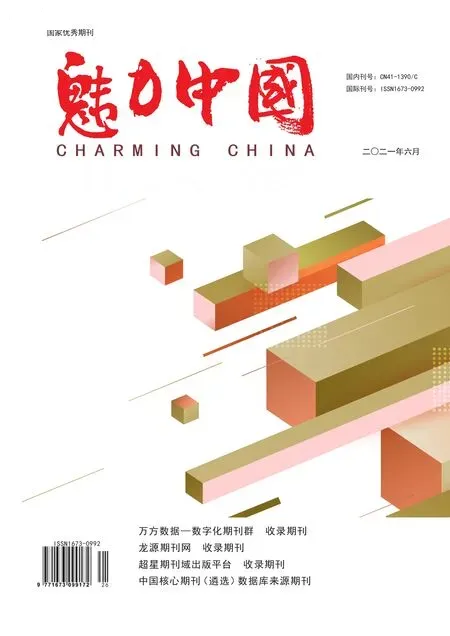淺談太康道情戲曲的“須生”表演
羅愛華
(河南省太康縣道情藝術保護傳承中心,河南 太康 475400)
太康道情是我國少數劇種之一,其唱藝新穎,唱詞通俗易懂,唱腔歡快流暢,具有濃厚的鄉土氣息,多年來,豫東地區流傳者。“寧叫面發酸,也要看看太康道情班,少鋤二畝地,也要聽聽太康道情戲”。
我在太康道情戲曲舞臺上已有20 多個春秋了,我用心體會每個角色的心理,把自己融入到每個角色當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鮮活的人物形象,得到了領導、專家們很和戲迷們的認可,取得一些成績,參演了好多個劇目,連續多次榮獲省市級的獎項。
我曾塑造過幾十個不同性格的生角的人物,在《王寶釧》一至五部中飾演薛平貴(小生、武生、須生)、《王金豆借糧》飾演王金豆小生、《玉梳記》飾演趙春安(小生)、《白玉樓》飾演張彥小生、大型歷史劇《王鈍》飾演王鈍(須生)等,以下就是在自己不同人物不同形象性格方面,談一些認識和體會。
戲曲行當,是戲曲特有的表演體制,是把人物類型程式化進行創造形象,一種特有的藝術形式。所謂行當,既是角色的總稱。行當劃分,是把社會地位各不相同,年齡、性格、氣質千差萬別的人物納入幾種類型。為了適應舞臺表演的需要,隨著戲曲藝術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完善。由于行當分類便于演員表演人物,便于觀眾辨認人物,又由于每一種行當,都有各自一套完整的程式,更便于培養訓練演員,所以,行當類型的劃分,已成為創造各種人物的有效手段。
道情藝術的須生,按照不同的人物、年齡、性格、特征可分為小生、老生、須生、武生,我們太康道情常稱的還有須生、小生、武生,
老生唱和念白都用真聲,風格上講究剛勁、挺拔、質樸、醇厚,動作造型也以雍容、端方、莊重為基調,并專門有一套髯口上的表演功夫。
一、《王寶釧》中的薛平貴——小生、須生行當
薛平貴從一個古代貧苦小生到武生、須生,第一部的薛平貴是貧困潦倒流浪漢,靠沿街乞討為生,那日乞討路過相府花園,花園大門開著,聽說相府有喜事臨門,趁大門未關,不免進的花園觀賞一翻,進的花園,平貴大開眼界,天上莫過神仙府,地上莫過宰相家,平貴觀看一番風景過后,久病的身體就倒在湖邊睡著了,這時候相府千金王寶釧帶著丫環來花園上香,丫環看見在一旁睡著的薛平貴,便告訴小姐,寶釧上前一看,雖是穿著一身乞丐衣服,但卻不是一般凡人,就讓丫環喚醒盤問一番,薛平貴對小姐道出內心痛苦和悲慘,平貴這段唱中表現了平貴雖是流落乞討,但胸懷大志意,人窮志不短,好男兒要志在四方,王寶釧聽了一番訴說,十分高興和敬仰,寶釧決定幫助平貴渡過難關,平貴感動地說,來日若得凌云志,一層恩當報十層還。此時的薛平貴是窮困小生,他的舉止謙卑,說話語氣溫和,但他的本性剛毅,人窮志不短,不失英雄氣概。
二、《薛平貴征西》中薛平貴——武生行當
《薛平貴征西》中的薛平貴,一出場身穿白色大靠,靠旗在背后飄蕩,出場走了旗把,這個人物的形象、力度要與一部的人物形象完全兩個不同的造型,這個武生出場臺步要有力度,山膀拉圓臺步每走一步要穩、準、狠。該劇中的薛平貴既有剛健有力的一面,又有鐵漢柔情的一面,如在“別窯”一場,薛平貴回到窯旁見到寶釧,心中有天大事要說,可欲言又止,進得窯內,寶釧看平貴神色不對,便苦苦逼問,平貴無奈說出了要去西涼征戰,不知此去三年五載才能回來,也不知是生是死。這段戲表現了薛平貴對寶釧的難舍難分,牽腸掛肚,萬般依戀。
雖說寶釧此時此刻一萬個舍不得,可寶釧是個知書達理、愛國的女中豪杰,只有忍痛割愛,送平貴西涼征戰。此時,平貴拉馬走的每一步,腿上像灌鉛一樣沉重,心中像刀扎般的痛,不舍也得舍,想哭不敢哭出聲,最后平貴心意已決,拔出青龍劍割袍,又割斷馬韁繩,揚鞭而去了。這段戲表現出薛平貴為了保家衛國,放下兒女親情的堅毅性格。
三、大型歷史劇《王鈍》中王鈍——須生行當
大型歷史劇《王鈍》講述了一位清廉正直的官員智斗豪強的故事,具有鮮明的價值導向。“權傾朝野,呼風喚雨”的康閣老,明知兒子康三“打死人命把禍惹”,還欲使慣用伎倆,為兒子拿錢消災,讓王鈍處于進退維谷的境地。王鈍表面上收下了康閣老的銀子,卻秉公處理了康三的案子,欲將其斬首。
惱羞成怒的康閣老,以王鈍的女兒小蘭要挾。王鈍夫人得知消息后,悲痛不已,懇求王鈍以康三質換女兒性命。在至親性命與伸張正義面前,他“心顫抖”,“眼發紅”,左右為難,最終決心為民除害,除掉禍根,將康三斬首示眾。
三年后,王鈍升遷上任杭州知府,路遇通判接到密告,查辦“王鈍貪污銀兩”一案,打開寶箱里面竟是王鈍妻子紡織的線穗子,原來王鈍早已將康閣老送的500 兩紋銀交于山西銀庫。
該劇通過王鈍查辦地方豪強、為民除害的故事,塑造了王鈍以人為本、民比天大、清廉正義的人物形象,彰顯了王鈍為民無私奉獻的精神。
王鈍這個角色屬于戲曲行中的官生行當。在演出中要求官生演員演唱爽朗,念白剛勁有力,節奏分明,以體現官威;在表演上要,注意與鑼鼓的配合,掌握功架的寸度和美感,與一般小生瀟灑倜儻的表演風格有所區別。在表現審案時猶疑不決或是矛盾難解時,還要運用耍(紗帽)翅的專門技巧表演。
王鈍一出場,是一家四口,一妻一女一侄,王鈍在上任的路上就聽說康三少是地霸,絞盡腦汁去對付這個地霸,須生的做派就是沉穩,每個動作要大方得體。例如,康格老使壞把王鈍女兒擄走,揚言要想你女兒性命,速放我康三,此時王鈍悲憤交加,放了康三,百姓會再遭禍殃;不放康三,女兒性命難保。在王鈍這悲痛焦急中,要用了戲曲中的“帽翅功”。
“帽翅功”是戲曲中“小絕活”。耍帽翅又稱“閃帽翅”,習稱“帽翅功”,是戲曲中官生或袍帶丑利用帽翅閃動來表達角色心理活動的一種舞臺表演技巧。
在舞臺上,一翅停穩,一翅上下閃動或輪轉的,習稱“單翅閃””;雙翅同時上下閃動的,習稱“雙翅閃”;雙翅相互倒換上下閃動,雙翅一前一后輪轉閃動的,習稱“滾翅”。通常通過帽翅的上下搖晃、左右擺動,表現出戲曲人物或歡喜快樂或忐忑不安或痛苦難當的心理狀況。耍帽翅完全由脖頸及后腦勺控制,需刻苦磨練方能運用自如。此外,帽翅上的彈簧也要長短軟硬適度,便于演員控制。
“帽翅功”絕活是為人物的思考、情緒、環境、思維來服務的。戲曲演員是一定要有技巧的,但是不能有了技巧就到處用,為了技巧而技巧是不對的,就是“炫技”。“帽翅功”沒有幾年的功底,是耍不好的,更要運用得恰如其分,要符合劇情,符合人物,也要體現出人物思想、感情。
為了利用“耍帽翅”來表達王鈍悲痛、焦急心理活動,我開始研究怎么來控制這帽子上的兩個“小翅膀”。原以為這功夫就是搖頭晃腦那么簡單,演員只有腦袋動,完全靠巧勁來掌握“小翅膀”,后來發現要想掌握這項本領并不容易。
我每天把官帽戴在頭上,憑借脖頸和后腦勺的控制力,來決定帽翅的轉向。剛開始掌握不好要領,不能很好地控制帽翅,感覺帽翅不聽指揮,練得脖子又酸又疼,難為得只直想哭。
在導演和老師的指導下,我漸漸掌握了耍帽翅的要領,帽翅閃得要有鮮明的節奏,清楚的層次,有單、雙、搓、繞四字要領,不能亂晃亂動。經過不斷的艱苦練習,終于掌握了帽翅功。每當演出時,就會贏得觀眾的陣陣熱烈的掌聲。此時此刻,我覺得自己付出的辛勤汗水和淚水都是值得的。只要能演好戲,付出再多,我都無怨無悔。
多年來,在演出實踐當中,我深深的體會到,“臺上一分鐘臺下十年功”,作為一個合格優秀的戲曲演員必須掌握有極高的基本功。作為一名小劇種演員,想塑造好每個角色,僅有的基本功是不夠的,藝無此境,活到老學到老,只有用心體會深入角色在生活中的揣摩,戲曲來源生活在舞臺的鍛煉,使每個人物常演常新。
今后我一定按照習總書記的要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對黨和國家忠誠,傳播傳承好中國優秀戲曲傳統文化和發展,緊跟時代潮流創作出更多人民喜歡樂見的優秀作品,把太康道情精品劇目送到百姓當中去,讓老百姓真正欣賞到道情戲曲的精品精神食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