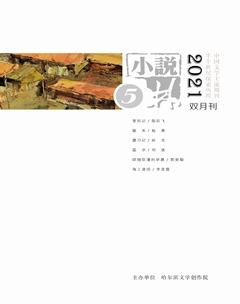回到小說的本質(評論)
好像米蘭·昆德拉說過,“大事就交給上帝吧,我們只關注細節。”但是米開朗基羅也說過,“在藝術的境界里,細節就是上帝。”楊勇的《鋤禾》我讀了數遍,因為只讀一遍太可惜了。能夠成為經典的作品絕對不是閱讀一遍就能體會其中妙處的,《鋤禾》文本是具有獨特意義的,暗流中它展現的是一個大時代的變革。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無論經濟、政治和文化都是一個涌動的,為后來中國發展提供奠基的時代。小崗村的村民已經自發地按下了手印包產到戶,年廣久炒傻子瓜子已經偷偷摸摸掙到了一百多萬,很多人又恢復了已經逝去多年的理想對未來充滿期冀。那段時期,舊體制和新體制交鋒更替,舊觀念和新觀念碰撞沖擊,形成一個波瀾壯闊的宏大畫卷,很值得作家反復書寫。《鋤禾》的獨特性在于,作者從四個平凡甚至卑微的農村一母同胞的姐弟入手,從點滴的可以擰得出水的細節寫起,用密不透風的拉拉雜雜的詩化語言對一個又一個生活細節的展開進而帶動情節,就像每個波濤串聯形成洪波涌起的畫面,而獨特的兒童視角又充滿了神秘的力量,使人總想拉開劇場化妝間的帷幕一探究竟。在閱讀的過程中,時時刻刻在為作者揪著一把心,這種走鋼絲的寫法是否中途要么鋼絲折斷,要么雜耍者失去平衡。而閱讀終結,不由得為作者擊節贊賞,所有矛盾的構建都落實在細節的鋪陳中,它們變得合情合理有跡可尋,作者對于某些細節的把握,甚至可以看成是教科書式的典范。
小說和其他文體的不同在于,小說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我是虛構的,但我也是真實的。虛構不是說謊,小說要回到時代本身,回到人性本身,甚至要像魯迅把生活撕開表現血淋淋的現實,而不是取悅讀者或是某個階層的文本。既然小說是虛構的,那么能夠支撐虛構的力量是什么呢,既然你是虛構的,我為什么還要讀呢?作為寫作者,用扎實的語言書寫扎實的細節,用綿密的細節推動情節,才能使虛構的文本自身邏輯自洽,這樣才回到小說的本質。
之所以重談小說的本質,是因為這個很重要的問題其實被忽略了。被忽略的原因有很多,有一個原因我把它歸結為教育的問題,就是我們曾經的小學中學教材編寫和教師講授中把一種低級的細節當成了高級的細節。譬如,我記得老師反復給我們講一個農民進城后花錢,他的掏、摸、攥、捏等動作,然后告訴學生每個動作表示了心理上的什么變化,這看起來很細節,其實很粗糙,因為把細節描寫等同于動作描寫或是心理表現,等同于照片寫實主義。我和楊勇探討過攝影,我說我很喜歡深瀨昌久的作品,他有同感,那種大顆粒的表面的粗糙其實是很細節化的,它通過一種模糊的細節其實延展了想象上的空間,譬如小說中王小春第一次看到電視機時的樣子。
“一個紅色大鐵盒,頭上有兩根锃亮的白鐵桿兒分立著,像蚱蜢的胡須。王小春跪在大鐵盒面前看,他從一塊灰玻璃里看到自己模糊的影子,他摸著那些鐵鈕兒,一個一個地擺弄。突然,他驚喜地發現,灰玻璃亮了,灰玻璃里在下雪,嗞嗞地響。王小春看著雪花,用手去摸,是涼的,不濕也不融化。周圍的一切都消失了,王小春的眼睛里只有雪花。”
這段細節,調動了視覺、聽覺、觸覺,把一個孩子剛接觸新鮮事物的神奇感覺描繪得淋漓盡致,它使我想起閱讀馬爾克斯《百年孤獨》里的一段情景。
“箱子里只有一塊巨大的透明物體,中間有無數枚小針,落日的余暉照在小針上,撞出許多五彩繽紛的星星。霍塞·阿卡迪奧·布恩地亞看蒙了,但他知道孩子們在等待他馬上做出解釋,于是他大膽地嘟噥了一聲:這是世界上最大的鉆石。
不,吉普賽人糾正說,這是冰。
……
他往前跨了一步,把手放在冰上,可馬上又縮了回來。在煮開著呢,他嚇得喊叫起來。”
這種細節,是一種高級的細節,調動了想象力的細節,它像中國印章的布局,方寸之間,密不透風,同時疏可走馬。
還有一種細節被忽略的原因是寫作者技術太粗糙了。小說是需要經營的,雖然說在敲擊鍵盤的過程中,主人公總想脫離作者的掌控,按照自身的邏輯發展,這是寫作者經常遇到的問題,但是即使主人公的結局和作者預想的大相徑庭。情節和文字也是需要拾掇的,就是中國畫中所說的“大膽下筆,小心收拾”。寫作者本身由于技術的不成熟,往往顧此失彼,而《鋤禾》中,所有的收拾都干凈利落,回味無窮。
譬如黃高麗給王小夏總要多塊糖,“他對崔金枝說,媽,我今天去供銷社買糖,黃叔又給了我十一塊糖,他不是什么好人,你離他遠點兒。王小夏看見崔金枝的肩膀在發抖。”
細節展現人物間的特殊關系和躲在文字后面的情節。
又如:“王小夏用手做成一支槍,在昏暗中四下瞄準,他瞄準玻璃,瞄準花盆。后來,他把槍口對準王小春,他想了一會兒,又挪開了。”
細節表現人性的溫暖,兄弟間平時打打鬧鬧,小矛盾不斷,但是兄弟畢竟還是兄弟。
尤為難得的是,也就是這個文本和其他文本不同的是,兩萬多字的中篇都是由這種延綿不斷的細節推動著行進,連綿的文字一直敲打著讀者的神經,除了王小冬的死亡,沒有什么驚奇而婉轉的情節,沒有傳統的起承轉合的所謂故事,有的只是鋪陳的細節,細致的甚至是絮絮叨叨的不厭其煩的敘事。這種敘事風格具有強烈的先鋒意識和現代感,區別于傳統敘事風格。其實,描寫此段時期的小說很難有新的路數了,從最早的《喬廠長上任記》到后來的《大廠》,幾乎都是一脈相承的現實主義敘事風格。而《鋤禾》這個文本的特殊性在于,所有的情節都是現實主義的,但是經過碎片化和拼接,就變成現代主義的,甚至有后現代主義的傾向。小說用一天的時間來描寫四個兄弟姐妹的生活行為,王小夏逃學,王小冬偷生產隊的東西賣,然后為了所謂保衛生產隊的財產成為烈士,王小春給表姐婚禮押車,始終頑固地向父親討要五元錢后來獲得了一把玩具手槍,王小秋情竇初開借著看電影的理由和情人幽會。一個又一個真實的細節經過作者不厭其煩的敘述在推動文本演繹,作者是下了很大功夫的,也做足了功課,每個細節都不失真。供銷社的布局,八十年代農村婚禮的運作,彼時流行的民謠俚語葷口,老師對當時課文的闡釋,生產隊對村民計算工分,彼時放電影的場景,這些細節的探究甚至上升到了博物學的高度,高度還原了當時的情景,使得每個情景都清晰可見歷歷在目。而這些細節經過線性時間無縫拼接在一起的時候,就產生了獨特的膠片電影效果,所有的場景都是碎片化的,但是每個碎片又都是精致的,獨立的不可分割的。當它們組合在一起的時候,既相互掙扎分裂又彼此相容銜接,構成了奇特的效果。感興趣的讀者可以看下安迪·沃霍爾的《夢露》系列,用絲網印刷技術制作, 每一個細節都是真實而且生動的,但是所有的生動組合在一起的時候,反而表現一種獨特的呆板效果,它觸到的是機械復制時代商業景觀時代的特質。小說中,王小冬之死,隨即東北土地承包開始,這也是那個生產隊時代的挽歌。
《鋤禾》作為一個獨特的文本存在,有被反復閱讀和研究的理由。作者不是從外在的形式感和通常的故事性入手,而是直接從小說最本質的東西入手,從文字表現的細節入手,由此,文本的力量感就尤為強大,深刻程度就更為附加,這同時也給了其他寫作者一個啟示,寫作,歸根結底還要回到小說本質的本身。
作者簡介:孔廣釗,1972年出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黑龍江省作家協會簽約作家,哈爾濱市作家協會副主席。作品曾被《小說月報》《中國文學》選載,出版長篇小說《和我一起蕩秋千》,有作品被翻譯為英文、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