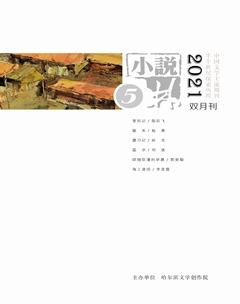海上清明
李美霞
一
臥龍村里有我另世今生的親人。
我大致是在還沒有入學識字的時候,就已經(jīng)能準確指讀出“臥龍村”這三個字了。好多次,母親翻開漆成紫紅色的深洞板箱,探進半個身子,從摞疊著的舊布單子里。翻出一塊漿洗的有些泛黃、僵硬的白布,剪一個長方形。然后坐在炕沿上,用穿好的針線把這塊白布四面繃展后,將它一針一線縫在一個包裹的中間位置上。
鼓鼓囊囊的包裹里,多數(shù)是農(nóng)人新下來的谷米豆子、葵花煙葉。父親用編織袋層層包裹,同樣用針線反復縫接封口,等母親把白布縫到合適的地方,最后一步工序仍是由父親來完成。他右手握一根油性好的圓珠筆,左手仔細比量著白布的長短寬窄,然后一筆一畫將嘴里叨念對照著的十多個字挨個工工整整地寫在白布上去。
“山東省榮成市成山鎮(zhèn)臥龍村? 李世發(fā) (收) ”
前者是父親少小早離的家,后者是父親牽腸掛肚的親人。
這一大串代表著某一個離我十分遙遠的地名的文字,我反復跟著父親誦讀過,其中,我對“臥龍村”三個字更感興趣。
“為什么叫臥龍村呢?”我問。
“因為村子旁邊就是大海,海里藏著祥龍,據(jù)老人們說,曾經(jīng)就有一條龍從成山頭上下來,越過村子飛進南面的大海里,這以后,人們就給村子起名臥龍村。”父親面色紅潤,健壯年輕,還是正當年的歲數(shù)。說這話的時候,他特意把舌根卷了一卷,算是借機溫習一下山東老家的口音。
這種略顯生硬笨拙的口音我是熟悉的。地盡場光、瓜落穗黃的農(nóng)閑時刻,父親總會把掛在墻上的一把舊了的二胡取下。吱吱吜吜調試一番。那是父親考上師范后,全家人節(jié)衣縮食為他購買的一件樂器。遠走逃荒的路上,即使饑腸轆轆、步履蹣跚,他從不舍得丟棄。我們姊妹幾個早已經(jīng)圍坐在父親身邊,等著他一邊拉著二胡一邊教我們唱歌。《山丹丹花開紅艷艷》《沂蒙山小調》,一首一首唱下去,直到月上燈明,風吹星隱。
更多時候,父親會搜索著家鄉(xiāng)的記憶,拍著桌子打著節(jié)奏給我們一段一段誦唱他所能熟記的快書段子。
“當哩個當,當哩個當,當哩個當哩個當哩個當!閑言碎語不要講,表一表好漢武二郎……”
這一段《武松打虎》的經(jīng)典段子,往往壓軸出場,這個時候,屋子里的氣氛更早就被之前的小段子調動起來,鄰里鄉(xiāng)親,端著茶碗的,納著鞋底的,噴吐著旱煙的,編著筐子的,就都湊到院子里來,更有人操起了臉盆拿起了板子,家伙什兒一應俱全,場面就更熱烈了。
父親的記憶極好,百多句的唱詞基本一句不錯,他這時已經(jīng)不再需要親自打板,就解放了雙手,釋放了表情,開始了最精彩的表演。一會兒張牙舞爪做老虎,一會兒威風凜凜扮武松,期間還隨時轉換著聲調粗細、人聲虎聲。敲鑼的砰砰切切漸入佳境,打板的汗流滿面直到手腕酸疼。這時候,父親就完全操著一口地道的山東口音了。人們哄笑著,也模仿著;小聲附和著,也大聲領唱著。進入高潮部分,某一個段子就不得不再來第二遍、第三遍,直到空靈世界里所有的聲音都融進來,鳥語蟲言,甚至連院子里的牛羊雞鴨也紛紛跟著哼叫起來。這種背井離鄉(xiāng)的語言,終于在千里之外的農(nóng)家之夜充沛豐滿,甚至膨脹起來。
春來冬去,我們也總會收到來自臥龍村的包裹。曬得金黃的地瓜干,顆顆飽滿的蝦米,各種魚干、海帶……
收到遠方的包裹,對于我們一家來說都是一件堪比過年的喜事,跟著父親抱著笨重的包裹回家,與路過的每一個鄰人寒暄通報,是值得榮耀與驕傲的。遠方有親,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這種美好,足以讓貧乏的日子活色生香起來。這些散發(fā)著海腥味的包裹里,包藏著一個孩子抑制不住的期待啊。同樣是里三層外三層裹束得嚴嚴實實。母親就用剪子對縫輕剪,封口打開的一瞬間,自是一片歡呼,這些在當年的供銷社里根本買不到、買不起的吃食,讓山東榮成市臥龍村成了我童年最美好的向往。
二
七歲那年,我第一次跟隨父母輾轉顛簸,踏上了山東的土地。之前空泛遙遠的臥龍村,終在千里之外與我相遇。一個靈秀精致的村落,背山靠海,得天垂憐,是一方別樣的存在。
我們選擇農(nóng)閑后的冬天出行。北方早已結冰的溝渠小河,在萬頃荒涼中也已靜止不動,光滑的冰面在太陽光下熠熠閃光。奔波數(shù)日,我卻在這里遇到了生命的另一種流淌。
那一段日子,我每天數(shù)次到海邊去。與上岸的每一朵宛如白蓮的浪花嬉戲,撿拾各種天然迥異的禮物,我甚至可以獨自站在海灘上,遠望無邊無際的大海。大多時候,海面平靜安逸,波瀾無驚,我與它面面相對不知厭倦。到了黃昏時分,鍍金的太陽照在海面上,幾縷微風拂過,碎玉一樣的波紋就爭先恐后向我推過來。而我仍然癡癡地等待,屏息傾聽著海的心跳與呼吸,遠處偶爾劃過的一道長長的波浪,礁石旁隱隱約約的巨大黑影,都讓我的內(nèi)心既喜又怕——也許,那一條穿村而過的青龍,就隱藏在那一派靜謐里,或游動在那一推一送的不安里?
我把腳印幾乎都印刻在這片海灘上。我與這片海素昧平生,卻在內(nèi)心里與之相知甚深,小小的我日日行走在一片壯闊帶來的陰涼中,形單影只如浪花一般存在。我與大海,我與臥龍村,我與一個個操著濃烈的膠東半島口音的親人們之間,融洽的純粹天然、嚴絲合縫,毫無生分之感。
飄著清香的荷葉饅頭隨意盛在竹編的笸籮里,白胖暄軟;滿盆盛放的扇貝只是淡鹽煮過,撒一把在熱騰騰的面條里就是一頓美餐;肉質鮮美的鲅魚餃子被姑媽捏出各種形狀排列成行,爭相蹦跳進沸騰的鍋里;滿車運送的新鮮海帶,拖著長長的尾巴從海灘路過,留下一條條腥鮮的水痕……
我甚至毫不費力地掌握了山東口音的發(fā)音要領。我熟絡卻略帶調皮地與這些首次相見的山水鳥獸打招呼。那時的我,還不能明白,這一次的千里奔赴,之于父親與我的意義都是一樣的,無論我們出走多遠,這一片海,這一處村落,就是我們此生割舍不掉的根脈。在父親呱呱降落在這一間低矮陋室的那一刻起,在他的胞衣埋進大樹下的一方蔥郁那一刻起,他就如一粒種子,在這片土地上刨出一個深深的坑,在這一片土地上留下了屬于自己的記號。此后,時緩時急的浪波、時遠時近的漁火、時動時靜的海面,那一隅風中飄搖的陋室茅屋,那與生俱來的語言,那開滿每個夏天的石榴花、紫薇花,連同父母墳頭枯了又青、青了又枯的蓬草,早已被血液浸泡、然后根根蘗生,讓剛硬的骨頭藤蔓縱深。
每天早上,我必會在早亮的清晨醒來。不論前一晚聊到多晚,大人們必早已在院子里聊天、忙活,似乎從不疲倦。晨曦里,名字被稱作“李世發(fā)”的我的本家姑父,帶著他的兒子跟隨漁船從海上風塵仆仆歸來了。這個海的少年,瘦削沉默,從一出生就理所當然地皈依了這片海,雙眼里就注進一片汪洋。父子倆承包了兩艘漁船,年復一年地將歲月打撈在一片茫茫大海里。
豐腴也罷,貧瘠也罷;出走也罷,歸來也罷。一個人的根脈,總要在屬于自己的一方土地上生根發(fā)芽、開花結果。
時光如銹,歲月結繭。此后多年,我已在異鄉(xiāng)成長為一顆粲然開放的紫薇花,清風搖擺,花瓣仔細呵護著纖細嬌嫩的花蕊。那無數(shù)根蕊,就是一朵花的精神所在。無數(shù)次回到海邊,少年已長成,雙眼里更是波瀾不改,唯見海水日復一日打磨著礁石的棱角,與這一片土地上的人們一樣,任勞任怨,素心安然。
我仍然記掛著這一片海,如同她同樣記掛著我一樣。站在海邊,我無聲,她無語。空靈與沉默就是最好的對話,我們之間,只需默默相對,我只需以一顆遠行歸來的游子最虔誠的心感受這一片海,用最溫柔的目光細細打量這一片細軟時光,足矣。
三
潮起潮落,擊打著人間春秋,
我的臥龍村的親人們,一邊瓜熟蒂落地生長著,一邊隱身不見隨日月升落遁入泥土。故人漸去,流水般經(jīng)過的都是陌生而嶄新的面孔。村東幾十米的成山頭上,纖纖弱苗早已噙葉參天,山路蜿蜒,被風雨修修剪剪卻愈發(fā)旺盛。山的最高峰處,挨挨擠擠的人們極目遠望、一覽勝景。
山腳下的一片偏僻之所,即是父親心頭另一隅記掛。我的爺爺奶奶早已長眠于此。一攏草木,廝守著一處隆起。時光深處,爺爺先逝后奶奶獨領著年方十七的父親外出逃荒。掩面泣淚,暫時背離了這一片大海,在他鄉(xiāng)燃起一縷人間煙火。奶奶去世后,父親將奶奶送回大海邊,送回大海滋潤的地壟田園里,也把自己此生的牽念送回到臥龍村的阡陌縱橫之間。
千里之外,燕去燕來,母親也離開了人間。父親于是在一夜之間就老去了。老去的歲月里河窄海寬,情深杯淺,溝壑之間,盛滿了對故鄉(xiāng)、對親人的追念。
清明,就成了父親繞不過去的悲傷,也盛藏著父親繞不過去的思念。每逢清明,父親就計數(shù)著日子,打量著落寞時間。
“趁我現(xiàn)在腿腳還利索,想在清明前后回一趟山東,給你爺爺奶奶攏一攏墳頭的枯草,圍一圍墳頭的土。”幾乎每一年清明前后,父親都會神情晦暗一段時日,這一段念語,似皈依佛門的弟子虔誠誦念的經(jīng)文。
一個海邊出生的男人,少年離家,此生背海而居,無法不讓他對一片海念念不忘。如今人老孤單,父親內(nèi)心的那座燈塔卻越來越明亮,故鄉(xiāng)的山水,被無盡的思念追著一束聚光燈,在大海深處渾然交匯,明暗輪替。
于是,我們在清明之時又回到海邊,回到一處庭院里,回到一畝田園中,回到默默不語的臥龍村,回到零落陌生的親人之間。
這一次,我深切感知到了一個村莊的衰老,如父親一般,在一夜之間就青春不再。臥龍村仿如留守在大海邊的一個古稀老人,時間在它身上碾下或深如鴻溝或淺如泊水的印記。佇立海邊,腳踏松軟卻堅實的海岸,懸浮的心瞬間嵌入地心,安穩(wěn)妥帖。
四月清明,墳頭的草剛剛生出芽,只等著一場雨過后,再籠蓋這一處人間隱痛。父親雙手緊握著一把平頭鐵鍬,細致認真地將墳堆兩旁的枯草鏟去,再將潔凈新鮮的泥土順堆攏起。
不用轉身,我已看見父親眼里滾出的淚水,折射著爍爍陽光。雙腿跪地,額頭深深地觸摸著一攏青草、一抔黃土,蒼蒼白發(fā)被風撩動吹亂。山的后面,就是經(jīng)久千年未改初衷的大海,就是夢中無數(shù)次呼喚萬千游子的大海。父親的每一次跪拜,無不是一個背井離鄉(xiāng)的兒女對故鄉(xiāng)山水的朝圣,是一個思念成疾的游子對根脈血緣的辨認。
父親很瘦,但腰板直溜。我的眼前浮現(xiàn)出大海上直聳的一葉孤帆。而我,追趕著海浪的腳印長大,如今又何嘗不是行走異鄉(xiāng)的獨舟。寒來暑往,冷暖交替,不過是為激起一朵歲月的浪花積攢力量。生命的本真就是歷經(jīng)風吹雨打不忘江湖河海的奔走,用無數(shù)次的離開、歸來,失去、擁有為自己的靈魂鍛造一處安身之所,山高路遠,通體相連。
香火裊裊,自需清酒一杯。茫茫海上、人間清明,尋祖認親即是千里奔赴的理由。甚幸,我是海的女兒,此生得以端起這杯色澤碧綠的酒。祭天祭地,祭春月海風,祭雪落原野,祭祖先亦祭后輩,祭人間也祭光陰。
歲月流轉,見證根脈傳承。酒香醇厚,每一杯都足以陶醉天地山川。四目對視,我與父親雙手舉杯,將一汪海水一飲而盡。
作者簡介:李美霞,魯迅文學院第三十四期少數(shù)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培訓班(內(nèi)蒙古班)學員,內(nèi)蒙古大學第九期文研班學員。出版小說集《多事之秋》《魂兮歸來》。2005年《紅雨傘》獲得冰心兒童文學佳作獎,多篇散文作品刊登于《文藝報》《散文選刊》《草原》等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