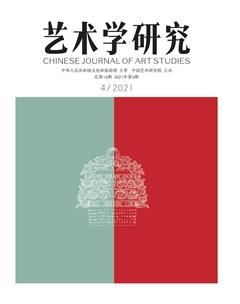重識與正名
曾小鳳


【摘 要】 考察以新潮美術作為起點的“中國當代美術批評”范疇,其“前衛(wèi)性”的本質(zhì)規(guī)定將美術批評本身看作是20世紀80 年代中國前衛(wèi)藝術運動以來所特有的文化現(xiàn)象,從而不可避免構成對20世紀中國美術批評的主體部分—具有鮮明的思想啟蒙和社會批判特征的中國現(xiàn)代美術批評—的挑戰(zhàn)乃至否定。在從“前衛(wèi)性”的反思、批判到“中國現(xiàn)代美術批評”范疇的提出過程中,亟待圍繞中國現(xiàn)代美術的“現(xiàn)代”形態(tài),將問題導向?qū)η对谄渲械摹艾F(xiàn)代性”話語裝置的考察,以此重識“中國現(xiàn)代美術批評”的性質(zhì)和價值。
【關鍵詞】 中國現(xiàn)代美術批評;現(xiàn)代性;批評思潮;正名
從20世紀80年代的新潮美術運動開始,“美術批評”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化現(xiàn)象備受學界矚目,這與“85新潮”最大限度地體現(xiàn)了“批評”的效力有關。其中,以高名潞為代表的一批青年批評家對這場影響至今的美術運動的推動和支配作用,在當時是被公認的。[1]對于這種“批評”效力,易英特別指出:“在1985至1987年這段時間,一批青年批評家異軍突起,在風格的引導、作品的闡釋和運動的總結(jié)上發(fā)揮了顯著的作用,如高名潞關于理性繪畫的理論、周彥對王廣義作品的哲理式闡釋、賈方舟對藝術形式的思考、殷雙喜有關批評的批評,都在不同的程度和角度上對正在高漲的新潮美術作出了理論上的反應,而這種反應顯然比藝術家本人的自我闡釋和宣言要深刻與全面得多。”[2]
正是基于對這種批評思潮之于新潮美術運動發(fā)生和發(fā)展的深刻影響的觀察,易英將“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化現(xiàn)象”的“美術批評”在中國出現(xiàn)的時間放在了新潮美術運動之時:
在中國,美術批評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化現(xiàn)象而出現(xiàn)時間大約是在1985年前后,盡管在80年代初期在美術界曾發(fā)生過有關現(xiàn)實主義、抽象藝術和美的本質(zhì)的爭論,這種爭論作為思想解放運動在美術界的反映,對中國現(xiàn)代藝術運動的形成作了積極的準備,但對于具體的藝術現(xiàn)象大都沒有進行有針對性的批評和總結(jié),如星星畫展、傷痕美術和鄉(xiāng)土現(xiàn)實主義等在中國當代美術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都沒有出現(xiàn)與之相適應的批評思潮。[1]
應該說,易英在20世紀90年代從批評實踐與藝術運動的關系角度所作的觀察,緊扣了以“85新潮”為代表的中國現(xiàn)代美術運動的發(fā)生形態(tài),注意到獨立意義的批評思潮對于這場運動的推動作用,這對于我們從新潮美術中汲取經(jīng)驗和推進美術批評學科建設,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但是,如果從學科的角度來思考中國現(xiàn)、當代美術批評的起點問題,就不僅僅是一個價值判斷的問題,也不僅僅是通過某個藝術運動、某一批評思潮就能說清楚的問題。它必須要上升到更高層次的問題維度,即作為學科的中國現(xiàn)、當代美術批評的內(nèi)涵和外延。其中,最核心的是現(xiàn)代性的問題維度,這是現(xiàn)代意義的中國美術批評作為學科得以成立的邏輯前提。
一、以新潮美術作為起點的“中國當代美術批評”范疇
就易英對“85新潮”美術運動中的“批評”效力的認識而言,在史料上構成20世紀90年代國內(nèi)美術界回顧與總結(jié)新潮美術的一環(huán)。在當時,除了美術界人士對這場運動的成就與失誤、創(chuàng)造與模仿、熱情與盲目等現(xiàn)象的積極解釋外[2],還有大量與之相適應的美術批評的理論反思。后一方面,主要以高名潞1989、1990年組織的兩次“美術批評筆談”最具代表性。[3]其中,與會批評家如高名潞、范迪安、易英、殷雙喜、王明賢等人圍繞“批評的本體意識與科學性”等問題展開的探討[4],最為集中地體現(xiàn)了這一時期美術批評的自覺意識。易英的這篇文章,是對新潮美術運動以來的美術批評的一種總體性述評。在他之前,盡管有賈方舟就“文化大革命”后十年(1976—1986)美術批評所作的“本體意識的覺醒”的判斷[5],以及祝斌按照美術史原則對“建國四十年”(1949—1989)的美術批評所作的批評形態(tài)的分類[6],但這些在易英以“前衛(wèi)性”[7]為基準的闡釋框架中明顯夠不上獨立意義的美術批評。其后,黃專于1999年發(fā)表的《90年代中國美術批評中的三大問題》,又接在易英的《1989—1993年美術批評述評》之后總結(jié)了“1993至1996年間中國當代美術批評的重要理論問題及一般發(fā)展”[8],二者構成了我們今天對以新潮美術為起點的“中國當代美術批評”范疇的一般認識。
從以上論述中不難發(fā)現(xiàn),對“中國當代美術批評”范疇的學理性認識,根源于1989年以后國內(nèi)美術界對已經(jīng)落幕的新潮美術運動的理性總結(jié)。當歷史的車輪跨入20世紀90年代,這場運動的批評家從理論和歷史兩方面對新潮美術進行回顧與總結(jié),本來無可厚非。但當論者普遍從新潮美術運動的批評實踐與歷史經(jīng)驗中尋求90年代中國當代美術的發(fā)展走向時,卻有意無意賦予了這場運動以某種不言自明的合法性。隨著新潮美術的價值觀念被轉(zhuǎn)化為敘述中國當代美術史的“元敘事”,一切圍繞它展開的歷史性回顧和總結(jié)也就自然而然地獲得了某種毋庸置疑的權威。在這種情況下,對新潮美術作為“中國當代美術批評”起點的認識,就不僅是一個簡單的史實問題,更關系到我們對與之相關的“中國現(xiàn)代美術批評”的性質(zhì)判定和價值評估,甚至牽涉到后者作為學科之成立的合法性理據(jù)。
與“中國當代美術史”是在“近代”與“現(xiàn)代”的歷史參照中建立其研究格局不同,“中國當代美術批評”范疇的提出與確立卻是以否定現(xiàn)代意義的美術批評的存在價值為基本前提的。這在易英用“前衛(wèi)性”的價值標準否定新潮美術運動之前的美術批評的認識中,就不可避免地發(fā)生了。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當代美術批評”作為一個研究范疇或?qū)W科分類的合法性,不是建立在其學科甚至學術系統(tǒng)內(nèi)部(從“近代”“現(xiàn)代”到“當代”的歷史邏輯序列),而是因為“前衛(wèi)性”問題深刻地介入其中。也即,中國當代美術批評與中國當代藝術、中國當代藝術的“前衛(wèi)性”問題的內(nèi)在關聯(lián),既是這一學科應該研究的核心問題,也是它賴以成立的基礎。
然而問題在于,為何以“前衛(wèi)性”為本質(zhì)規(guī)定的中國當代美術批評會構成對現(xiàn)代意義的美術批評的挑戰(zhàn)乃至否定?在考察之前,我們首先必須弄清楚“前衛(wèi)性”這個概念的含義。一般認為,“前衛(wèi)性”作為描述“前衛(wèi)”的一種理論話語[1],主要被西方理論家用來考察和解釋前衛(wèi)藝術產(chǎn)生的根源、特點及性質(zhì)。在美術批評領域,以格林伯格為代表的現(xiàn)代主義藝術批評家,對前衛(wèi)藝術及其本質(zhì)做了影響最深遠的規(guī)定。在1939年發(fā)表的《前衛(wèi)藝術與庸俗文化》中,格林伯格是把“前衛(wèi)藝術”看作資本主義社會中反對“庸俗”趣味的文化代表,認為只有“前衛(wèi)”才是創(chuàng)造有歷史價值的高水準藝術的唯一途徑。與西方的現(xiàn)代性敘事是在美學與社會的二元對立論基礎上展開的一樣,格林伯格對前衛(wèi)藝術的邊界及其特征的劃定,同樣是在“前衛(wèi)”與“庸俗”兩種文化藝術形態(tài)的對立關系中實現(xiàn)的。對他來說,“前衛(wèi)”當然不僅僅是一個用于分類的、中性的文化藝術標簽,它暗含價值判斷,同樣也不可避免地暗含價值偏見。
回過頭來看“中國當代美術批評”的“前衛(wèi)性”,它在提出之初主要是作為一種價值判斷的修辭,而不是西方學者用以理性分析現(xiàn)代主義“前衛(wèi)”本質(zhì)的統(tǒng)一方法論。易英有關“前衛(wèi)性”之于美術批評生存價值的觀點,正說明了這一點。在他看來,“前衛(wèi)性”是“批評的生命力”,“批評如果不以前衛(wèi)性(這兒是一種泛指)為對象的話,它就失去了生存的價值,它就只是一般性的指導欣賞的文字和為個別藝術家捧場的庸俗文化”[2]。盡管易英并未講明作為“一種泛指”的“前衛(wèi)性”的具體含義,但不難看出他對于“批評”與“前衛(wèi)性”關系的分析,是從格林伯格《前衛(wèi)藝術與庸俗文化》一文中引申出來的。只不過,在格林伯格那里保持著歷史與邏輯聯(lián)系的“前衛(wèi)”與“庸俗”兩種對立的文化藝術形態(tài),被易英拆解、改造和重組成了一種新的敘事話語,或者說一種具有特定價值邏輯的修辭。在這一新的敘事話語和修辭中,以“前衛(wèi)性”為對象的新潮美術批評獲得了獨立的歷史價值,并開啟了一個我們今天所津津樂道的“批評的時代”[1]。
二、從“前衛(wèi)性”的反思、批判
到“中國現(xiàn)代美術批評”范疇的提出
如果我們承認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當代美術批評的“前衛(wèi)性”標準,不過是某種適宜闡釋新潮美術運動的修辭;那么,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對于當時的批評家和藝術家而言,這種“前衛(wèi)性”的修辭到底意味著什么?借用高名潞的話來說,“在1980年代,一個通常的理解是現(xiàn)代即前衛(wèi),前衛(wèi)即是現(xiàn)代”,而“藝術家和批評家開始頻繁并正式啟用‘前衛(wèi)一詞是自1989年2月的‘中國現(xiàn)代藝術大展(China Avant-Garde Exhibition)起。此展覽的中英文的不同名稱,或許說明了當時我們對‘現(xiàn)代和‘前衛(wèi)的關系的理解”。[2]倘是這樣,“前衛(wèi)”與“現(xiàn)代”這一對在新潮美術的藝術家及批評家那里可以同義置換的概念,恰也意味著二者的理論話語—“前衛(wèi)性”“現(xiàn)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某種不言自明的對等性。當以易英為代表的批評家用“前衛(wèi)性”來規(guī)定美術批評的本體價值時,其本身就已經(jīng)包含了某種“現(xiàn)代性”的想象。只不過,這種以“前衛(wèi)性”為價值指向的“現(xiàn)代性”,已經(jīng)喪失了它的概念規(guī)定性以及由這種規(guī)定性所產(chǎn)生的歷史價值。
這里涉及對兩個層面問題的考察:第一,作為源出于西方的概念,“現(xiàn)代性”和“前衛(wèi)性”的關系是什么?第二,在中國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前衛(wèi)性”為何不能作為美術批評的闡釋立場?就第一個問題而言,馬太 · 卡林內(nèi)斯庫(Matei Calinescu)在他影響甚廣的《現(xiàn)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是把“前衛(wèi)”[3]看作“現(xiàn)代性”的表現(xiàn)之一,認為前者“只不過是現(xiàn)代性的一種激烈化和高度烏托邦化了的說法”[4]而已。與波吉奧利主要從美學特質(zhì)來界定“前衛(wèi)”不同[5],卡林內(nèi)斯庫特別強調(diào)“現(xiàn)代性意識”在前衛(wèi)的起源及歷史實踐過程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他注意到“兩者(現(xiàn)代性與前衛(wèi)—筆者注)從起源上說都有賴于線性不可逆的時間概念,其結(jié)果是,它們也都得面對這樣一種時間概念所涉及的所有無法克服的困境與矛盾”,最顯著的便是悖論式地存在于其自身之中的“文化危機”。[6]這種描述盡管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tài)功能,如把前衛(wèi)、現(xiàn)代性多層面的歷史進程(包括政治、文化、經(jīng)濟、技術和觀念等)化約成了一種以個人情感體驗為主的文化癥狀;但正是在這種包含強烈意識形態(tài)傾向的“文化危機”中,卡林內(nèi)斯庫發(fā)現(xiàn)了二者所共享的氣質(zhì)和稟賦,他稱之為“一種特殊的危機想象力”[7]。
如果說,卡林內(nèi)斯庫主要是從意識形態(tài)、心理結(jié)構和形式語言等方面去界定前衛(wèi)的本質(zhì)及其與現(xiàn)代性的關系;那么,比格爾則主張把前衛(wèi)的歷史現(xiàn)實和描述前衛(wèi)的理論話語分開,認為“前衛(wèi)性”本身的發(fā)生就是一個歷史現(xiàn)象,或者說是一種存在。在《前衛(wèi)理論》的序言中,比格爾首先談什么是前衛(wèi)的理論話語和敘事,以及這個敘事與前衛(wèi)的歷史現(xiàn)實之間的關系問題。與波吉奧利和卡林內(nèi)斯庫都不一樣,比格爾認為現(xiàn)代性、前衛(wèi)性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體制所催化出來的必然產(chǎn)物,而前衛(wèi)(包括前衛(wèi)藝術和前衛(wèi)意識等)的產(chǎn)生就是對它生長于其中的體制的有意識地批判。這種“反體制”在比格爾看來,正是“前衛(wèi)性的創(chuàng)造發(fā)明”[1]。在這里,重要的是比格爾對前衛(wèi)本質(zhì)的定義方式的轉(zhuǎn)移:他并不像波吉奧利和卡林內(nèi)斯庫那樣把前衛(wèi)的意識形態(tài)和美學現(xiàn)代性從它賴以生存的資本主義體制中分離出來[2],而是把這種體制本身及對它有意識的批判作為了前衛(wèi)的歷史本質(zhì)。正是在“反體制”這個關鍵之處,比格爾形成了他用以檢驗現(xiàn)代藝術與體制之間關系的前衛(wèi)理論話語,這就是我們所稱的“前衛(wèi)性”。
綜上所述,“前衛(wèi)”“前衛(wèi)性”及其與“現(xiàn)代性”的關系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前衛(wèi)性”作為描述“前衛(wèi)”的理論話語,它是比格爾從西方前衛(wèi)藝術及其所依附的資本主義社會體制的關系中歸類出來的;第二,“前衛(wèi)性”與“現(xiàn)代性”一樣都根源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文化本身的發(fā)展邏輯,或者說是西方資本主義體制所催化出來的必然產(chǎn)物;第三,離開了“現(xiàn)代性”這個較大的語境,“前衛(wèi)”及其“前衛(wèi)性”理論都是不可想象的。這三點,關系到我們對第二個層面問題的回答。正因為比格爾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體制作為前衛(wèi)藝術產(chǎn)生的根源,因此,他的前衛(wèi)理論也就必須建立在這個體制自身的發(fā)展邏輯之中,這一邏輯就是美學(西方現(xiàn)代藝術的自律性本質(zhì))與社會(西方資本主義體制)二元對立的關系模式。
然而,這個二元論的自律與反自律的理論前提,可能無法適用于闡釋中國現(xiàn)當代的藝術運動現(xiàn)象。這一點,高名潞作出了充分的估量[3],而且即便是被公認為中國前衛(wèi)藝術運動的新潮美術,“前衛(wèi)都是在社會革命和藝術革命的雙重精神烏托邦的氛圍中出現(xiàn)和發(fā)展的”,這種“前衛(wèi)不是疏離社會,而是介入社會和大眾空間”[4],與比格爾所界定的“反體制”的“前衛(wèi)”并不能同日而語。事實上,如果純粹按照西方前衛(wèi)理論的標準,恐怕只有80年代新潮美術運動以來的中國當代藝術才夠得上“前衛(wèi)”的格,而伴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展開的洋畫運動,很可能會像邦尼 · S.麥克杜戈爾(Bonnie S. McDougall)評判同時期的中國新文學運動那樣,“基本上不屬于先鋒派運動”[5]。同樣,以“前衛(wèi)性”作為美術批評的闡釋立場,很可能也會出現(xiàn)類似的認知誤區(qū),其危險在于把美術批評本身看作是80年代中國前衛(wèi)藝術運動以來所特有的文化現(xiàn)象,而將20世紀中國美術批評的主體部分—具有鮮明的思想啟蒙和社會批判特征的中國現(xiàn)代美術批評,排除在了“前衛(wèi)性”之外。這不啻目前20世紀中國美術批評研究中所存在的缺憾。
三、“中國現(xiàn)代美術”的“現(xiàn)代”追問
如何重繪20世紀中國美術批評的“現(xiàn)代性”面孔?我的看法是,任何意義上的“重繪”都必須以重新認識“中國現(xiàn)代美術”的性質(zhì)和它的歷史語境為根本性前提。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這一概念的使用慣例一樣[6],“中國現(xiàn)代美術”既可作為一個學科范疇,也可代表一種在歷史中生成和延續(xù)的美術形態(tài),像潘公凱主持的“中國現(xiàn)代美術之路”指的就是作為特定的美術形態(tài)的歷史,而非一個學科的演進之路。當然,這兩個層面的區(qū)別是顯而易見的,但二者的聯(lián)系也不容忽視:作為學科的“中國現(xiàn)代美術”是根據(jù)它的研究對象—“現(xiàn)代美術”—確立自己的學科邊界;反之,對“中國現(xiàn)代美術”的“現(xiàn)代”形態(tài)的探尋既是這一學科應該研究的問題,也是它賴以存在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一種歷史形態(tài)的“中國現(xiàn)代美術”的起點問題,自然會牽涉到這一學科邊界的劃定。
首先需要指出,“現(xiàn)代美術”概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尚未通行,即便有個別以“中國現(xiàn)代藝術史”命名的著作[1],也主要是在“現(xiàn)代”“近代”的時間意義上理解“現(xiàn)代”的含義,而不是用以劃定一種特定形態(tài)的美術。民國時期普遍通用的概念是“洋畫”“新國畫”“新藝術”“新美術”等,其中的“洋”和“新”字意味著自覺地與“舊”相對立,與我們今天所理解的“現(xiàn)代”這一概念的價值內(nèi)涵有相似的意義。至于這些有著明確價值指向的概念被“現(xiàn)代美術”所整合,其實并不是美術領域的獨立現(xiàn)象,文學領域也是如此。[2]但比“現(xiàn)代文學”取代“新文學”概念更為復雜的是,“現(xiàn)代美術”這一概念的提出,卻是以消解“新藝術”“新美術”的“現(xiàn)代”內(nèi)涵為基本前提的,因為后者統(tǒng)統(tǒng)被劃到了“近代美術”的范疇中。
胡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增訂他初版于1946年的《中國美術史》,或許最能說明問題。他把原本用以概括1912至1940年美術情況的章節(jié)標題“現(xiàn)代的中國美術”改成了“近代的中國美術”,并在其后補寫了“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和新中國的美術”[3]一章。這就潛在地把毛澤東領導的人民大眾的美術作為“現(xiàn)代美術”的開端,它不但對“新藝術”“新美術”的自我敘述構成了有力的沖擊,而且深刻地影響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有關“中國近現(xiàn)代美術”的歷史敘述。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央美術學院1956年設立的“中國近現(xiàn)代美術史”課程。當時在江豐的領導下,組織了一批美術史家編寫中國近現(xiàn)代美術史資料集(如1961年油印的《中國現(xiàn)代美術史參考資料》)、圖譜、史稿和大事年表等[4],對作為教學對象的“中國近(現(xiàn))代美術”的歷史范圍、性質(zhì)、分期做出了清晰的描述和規(guī)定。
然而,一旦用以支撐“近代美術”和“現(xiàn)代美術”劃分標準的革命史敘事開始失去權威;那么,“現(xiàn)代美術”自身就不再不言自明,它需要被重新定義,特別是在起點的限定上。相比文學界自20世紀80年代初就進入重估與反思“現(xiàn)代文學”性質(zhì)的階段[1],美術界對這一問題的自覺明顯滯后,甚至發(fā)生了敘事錯位。或許是因為80年代異軍突起的新潮美術與西方現(xiàn)代藝術存有共通之處,大部分美術理論家對于“中國現(xiàn)代美術”的認識與反思首先是基于新潮美術運動展開的,如高名潞的《新潮美術運動與新文化價值》(1988)便是在“中國現(xiàn)代美術”的闡釋框架下設定“新潮美術運動”的歷史與文化邏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新潮美術”作為“中國現(xiàn)代美術”的新內(nèi)涵,被研究者普遍接受。[2]除了黃專從文化批評的角度指出作為“中國現(xiàn)代美術”的新潮美術運動的“兩難”外[3],呂澎和易丹1992年合著的《中國現(xiàn)代美術史(1979—1989)》更是把“中國現(xiàn)代藝術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4]放在了“文化大革命”后十年(1979—1989)以“新潮美術”為主潮的運動上。
也正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回顧與總結(jié)新潮美術之得失時,包括高名潞在內(nèi)的一批美術批評家對新潮美術的“前衛(wèi)性”本質(zhì)作出了新的認識[5],其所具有的“當代”而非“現(xiàn)代”的本質(zhì)和意義逐漸凸顯成為一種共識。只有當新潮美術的“現(xiàn)代”胎記自行消退后,“中國現(xiàn)代美術”的“現(xiàn)代”才真正成了一個需要思考和回答的問題,而這比文學界滯后了將近20年。自1998年王德威提出著名的“沒有晚清,何來‘五四?”命題后,整個文學研究界的理論熱點顯然從80年代立足于“五四”起源論的現(xiàn)代化敘事,轉(zhuǎn)向了重建中國現(xiàn)代文學整體知識版圖的現(xiàn)代性話語階段。“現(xiàn)代文學”的起點問題,又在新一輪的理論熱點中重新變成了研究者關注的話題。[6]與此同時,美術理論界也開始著手清理中國美術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歷程與線索、性質(zhì)與形態(tài)、標尺與走向等問題,如潘公凱1999年正式啟動的“中國現(xiàn)代美術之路”課題組、鄭工2000年完成的《演進與運動:中國美術的現(xiàn)代化(1875—1976)》即是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只不過,相比文學界基于80年代中國文學“現(xiàn)代化”研究成果基礎之上的“現(xiàn)代性”反思[7],美術界對這兩種理論模式相抵牾的一面顯得認識不足。
最明顯的是,美術界對“中國現(xiàn)代美術”的“起點”這個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問題,缺乏學科層面上的關懷和理論自覺。鄭工在論述“中國美術的現(xiàn)代化”演進時,提出把中國現(xiàn)代美術史的“理論上限”前移至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以便在洋務運動的西學浪潮中確立“中國現(xiàn)代美術的起點”—他命名為“新工藝運動”(1875—1910)。[8]容易引起爭議的,倒不是這種研究邊界的前移與他所概述的三種“中國美術的現(xiàn)代起點”[9]的抵牾與沖突,而是如何在這一“放大”的美術史書寫中確立與之相適應的價值評判體系。這一點,在鄭工以中國美術“現(xiàn)代化”為視野的理論架構中并不自覺。事實上,如果將晚清西學“新工藝”作為中國現(xiàn)代美術的起點,那么它與二三十年代的“新藝術”“新美術”在哪一個價值層面上進行統(tǒng)合,又如何具體落實“現(xiàn)代化”的價值標準,就不惟關系到“中國現(xiàn)代美術”的性質(zhì)與形態(tài)問題,而且牽涉到這一學科安身立命的合法性。因為,說晚清“新工藝”是中國現(xiàn)代美術的序幕或前奏,其實并不會構成對現(xiàn)行的中國美術現(xiàn)代化敘事框架(以“辛亥革命”或“五四”新文化運動為開端)的根本性顛覆,但定位為“起點”則意味著所謂“現(xiàn)代”乃至“美術”的既定指標的失效,它自身必須前移至晚清的論述空間中加以重新界定。然而,在“美術”含義尚且含混的晚清社會,如果僅以“現(xiàn)代化”作為標準的話,我們何嘗不能在比“新工藝”更早的“五口通商”[1]美術中找到現(xiàn)代性的蹤跡?按照這樣的邏輯,“現(xiàn)代美術”的起點就不可能停止在晚清,它還可以上溯到西方傳教士來華的晚明,甚至更早,這實際上無異于取消了學科獨立存在的基礎。
或許是因為在歷來的學科架構中,所謂“中國現(xiàn)代美術”的“現(xiàn)代”不是被納入“中國近現(xiàn)代美術”的研究視野,就是被統(tǒng)合進“中國現(xiàn)當代美術”的格局,所以它自身的起點問題反倒在“現(xiàn)代性”話語的籠罩下模糊不清。就前者而言,如果我們還記得胡蠻特地把民國時期的美術改稱為“近代的中國美術”,以賦予“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和新中國的美術”這一新生的美術形態(tài)以某種不言自明的“現(xiàn)代”內(nèi)涵;那么,20世紀50年代以后出于學科化要求所提出的新概念—“中國近現(xiàn)代美術”,與其說將“近現(xiàn)代美術”建構為一個客觀的認識對象,不如說是應新中國美術內(nèi)部的自我論證的需要。只不過在“現(xiàn)代”本身成了一個可疑之物的90年代,如果還是延續(xù)這種自我敘述的慣例,把1911至1949年之間的美術稱作“中國近代美術”[2],這無疑是強化而不是削弱了一些人為的意識形態(tài)因素。在這種情況下,為中國現(xiàn)代美術“正名”,就不單是一個尋繹現(xiàn)代化敘事框架的過程,首先要厘清的自然是“近代美術”與“現(xiàn)代美術”的歷史邊界及其價值尺度。這樣,問題也接踵而來,“中國現(xiàn)代美術”是如何成為“現(xiàn)代”的?連帶的問題是我們用什么理由把同一個世紀發(fā)生的美術現(xiàn)象納入“現(xiàn)代”之中,或排除在“現(xiàn)代”之外?這種追問,實際上就是有關“現(xiàn)代性”的追問。
四、重繪20世紀中國美術批評的“現(xiàn)代性”面孔
目前,有關中國美術“現(xiàn)代性”問題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是潘公凱主撰的《中國現(xiàn)代美術之路》。在這一“基于現(xiàn)代性反思的美術史敘述”中,潘公凱涉及的不僅僅是有關“中國現(xiàn)代美術”的“現(xiàn)代性”問題,而是由反思西方現(xiàn)代性結(jié)構的角度對近現(xiàn)代中國美術的歷史演進及未來走向進行重估,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以“自覺”為標識、以“四大主義”為基本形態(tài)的“中國繼發(fā)性美術現(xiàn)代性”[3]的理論構想。事實上,潘公凱創(chuàng)構提出的這一理論所引起的反響和爭議也不僅僅局限于美術領域,而是指向了當今中國知識界的理論前沿,回應和介入了自20世紀90年代至今方興未艾的“現(xiàn)代性”文化熱。從這個意義上說,它自身就是這一“現(xiàn)代性”文化熱的產(chǎn)物。問題在于,為什么在“現(xiàn)代性”話語籠罩之下的中國現(xiàn)代美術反而需要“正名”?在此之前,為什么不需要?或者說它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根本不成其為“問題”?這一系列疑問實際上把我們導向了對“現(xiàn)代性”這一構造頗為精致的“話語裝置”(discursive apparatus)的考察。
這個“話語裝置”就是酒井直樹在他的《現(xiàn)代性與其批判》中指出的,“如果不參照前現(xiàn)代與現(xiàn)代這一配對,就無法理解‘現(xiàn)代性這個術語”,因為“前現(xiàn)代—現(xiàn)代”盡管“給人一個紀年性順序的印象”,但是“這個基本上屬于十九世紀的歷史圖式(scheme)提供了一種視角,通過它來系統(tǒng)地理解各個國家、文化、傳統(tǒng)與種族所處的位置”。[1]顯然,“現(xiàn)代”在這一“現(xiàn)代性”的“話語裝置”中不僅是作為歷史中的一個具體階段,而且還成為一種元語言的展示,它具有把“各個國家、文化、傳統(tǒng)與種族”的地方性話語轉(zhuǎn)變?yōu)橐环N普遍的、全球性的話語的功能。然而,一旦非西方國家接受或者不得不借用這種從“前現(xiàn)代”(傳統(tǒng)—筆者注)到“現(xiàn)代”的“過渡敘事”[2],也就意味著離開了“西方”這一參照系統(tǒng),他們很難想象出一種可以作為其替代的別樣的“現(xiàn)代”。事實上,對于何種“現(xiàn)代”的困惑,恰恰是潘公凱開展“中國現(xiàn)代美術之路”這一課題的內(nèi)在動因,正如他在課題緣起中所說:“如何建構中國美術的現(xiàn)代形態(tài)?進一步說,能否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根基上,引申和建構出不同于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藝術形態(tài),一種中國自己的現(xiàn)代主義?這是中國美術近百年來所面臨的最中心的問題。筆者多年來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3]
如果我們把“建構”理解為一種重寫美術史的努力,那么所謂“一種中國自己的現(xiàn)代主義”就是以一種自覺的“現(xiàn)代主義”來讀解“中國美術”,同時又以一種反思的“現(xiàn)代性”來讀解“中國美術”與“西方現(xiàn)代主義”的關系,這是潘公凱探尋中國美術的“現(xiàn)代”形態(tài)的一般思路。然而,細心推敲便不難發(fā)現(xiàn)這種“建構”依然是后殖民理論家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指出的第三世界國家所慣常采用的“過渡敘事”。在這一表述中,作為地緣政治范疇的“中國”與“西方”和作為時間范疇的“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具有了某種對等性,而中國美術“從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的過渡,又必須在以“西方現(xiàn)代主義”為范型、為工具的前提下方可實現(xiàn)。這無異于加強而不是削弱了“西方”在這一過渡敘事中的主導性地位。盡管潘公凱自己對于借助西方現(xiàn)代性話語為中國美術“正名”的困境有著清醒的認識—他稱之為“一種自我纏繞的悖論狀態(tài)”[4],并試圖在“自覺”中確立中國現(xiàn)代美術的自主性;但是,這一課題借由現(xiàn)代主義的話語策略所構成的敘述框架—“四大主義”[5],依然沒能沖決中西之間那種不平等的權力/知識關系。
只要我們把眼光放長遠一點,“中國現(xiàn)代美術之路”這一課題本身無非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在全球化浪潮下,尋求文化自主性的時代要求在美術領域的投射。在這一點上,中國美術的“現(xiàn)代之路”是否就一定是以“自覺”為標識、以“四大主義”為結(jié)構演進變得不那么重要。因為,它的提出乃至引發(fā)爭議[6],都是置身于全球一體化進程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困惑、思考與探索的反映。而類似的有關文化上的自我定位及其走向的討論,在中國近代以來被卷入世界性的現(xiàn)代化進程中就不止一次地出現(xiàn)過。除了“五四”時期那場在“民主”與“科學”旗幟下以“反傳統(tǒng)”面貌出現(xiàn)的新文化運動之外,還有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思想界、文化界關于東西文化問題的論戰(zhàn)(1915—1927)、關于中國現(xiàn)代化問題的討論(1933)、關于中國文化出路問題的新論戰(zhàn)(20世紀30至40年代)等[1],它們共同體現(xiàn)了中國知識分子在西化浪潮和沉重現(xiàn)實的兩難境地中探尋文化出路的自覺。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現(xiàn)代美術之路”課題組圍繞中國美術“現(xiàn)代性”問題展開的一系列研討,正像它的提出者所自覺的那樣,是“由美術史出發(fā)去理解現(xiàn)代性問題,同時也帶著現(xiàn)代性思考切入美術史”,它的落腳點盡管在“美術史”上,但出發(fā)點卻是借由中國美術來反思“現(xiàn)代性”問題,而后者正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用以樹立自主性文化身份的視野和方法。然而,也正因為對中國美術“現(xiàn)代性”的探尋在根本上是指向更宏大的國家文化定位問題,與“正名”密不可分的“中國現(xiàn)代美術”作為一個學科的合法性之“名”,反倒在無形之中被模糊乃至消解了。正是立足于以上考察,筆者認為有必要將“中國現(xiàn)代美術批評”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范疇加以提出。原因是,“中國現(xiàn)代美術批評”的“現(xiàn)代”概念,不僅是一個單純的上承“近代”、下啟“當代”的歷史分期術語,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歷史性的價值概念,關系到我們對作為研究對象的“中國現(xiàn)代美術批評”的性質(zhì)判定和價值評估。
作為一門現(xiàn)代形態(tài)的人文科學,美術學的學科構架離不開對中外美術史、美術批評和美術理論的整體性研究,這是建構理論形態(tài)的美術學學科體系的重要基礎。相比中國現(xiàn)代美術史和美術理論的豐厚研究,中國現(xiàn)代美術批評在批評史、批評流派和批評家個案研究上一直處于美術學學科的邊緣地帶。與“美術史”重在揭示美術發(fā)展的歷史過程和基本規(guī)律,以及“美術理論”展開有關美術問題的理論研究不同,“美術批評”的核心在于以批評話語和觀念推動美術思潮和流派的生成和發(fā)展,三者緊密聯(lián)系、相互促進,構成美術學學科框架的基本內(nèi)容。筆者所著的《先鋒的寓言》,在中國現(xiàn)代美術批評的起點問題上提出“五四”發(fā)生論,認為中國美術批評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與“五四”新文化運動變革中國傳統(tǒng)文化價值觀念的職志相關,它在形態(tài)上具有強烈的否定性、批判性和革命性。[2]正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于中國傳統(tǒng)和社會現(xiàn)實的整體性批判過程中,“美術”才得以與作為特定學科范疇的“文學”相分離,并最終發(fā)展成為一個以繪畫、雕塑、建筑等空間藝術為本質(zhì)規(guī)定的獨立學術門類。而狹義“美術”的生成對于中國現(xiàn)代美術批評的意義在于,它關系著我們對一種獨立形態(tài)的美術批評的認識。這里有兩點格外重要:發(fā)生之初的狀況,除了要考慮民族國家尤其是國家政體、朝代更迭這些因素以外,最重要的是在美術創(chuàng)作、批評觀念和“五四”三者的互動關系中進行總體考量。作為我們理解一種現(xiàn)代意義的美術批評在中國發(fā)生的思想文化語境,這在20世紀中國美術批評的學科分類尚顯模糊的今天,尤為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