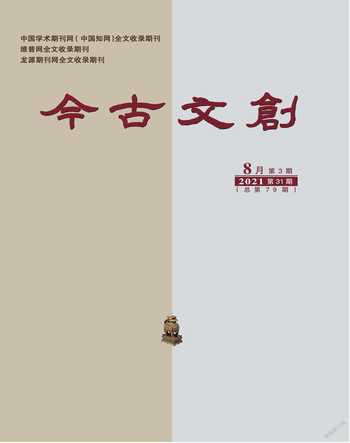國畫構圖研究
閆成龍
【摘要】 隨著科技和文化的發展,民族文化自信和歷史使命感逐漸成為重要的話題,研究國畫的構圖以及其設色對推展國家文化傳播以及大眾對文化認可度有重大意義。本文將以中國山水畫經典作品《桃源仙境圖》為例,較為詳細地分析其構圖的構成、布局、裝飾意味等安排的合理性,為讀者品讀古畫時提供其構圖韻味分析的新思路。
【關鍵詞】 《桃源仙境圖》;構圖;中國畫
【中圖分類號】J212?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31-0098-02
一、中國古代繪畫構圖演變簡述
(一)山水畫歷史演變
綜合出土的文物以及研究史料,中國畫山水元素最早出現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青綠山水也從此開始萌芽,當時的山水仍作為一種背景襯托依附于人物畫。在隋唐時期,山水畫逐漸獨立于人物畫成為一種新的畫種。五代時期山水畫到達一個頂峰,在元代文人更注重山水畫的意境表達,這時產生的文人畫也較多。到了明朝時期,掀起一陣宮廷繪畫的浪潮,下文所介紹《桃源仙境圖》就是繪于明朝時期。
(二)透視方法
中國畫從古至今大多以散點透視為主,這是為了表現巨幅作品和長卷的一種透視形式,這種透視形式需要作者以游代觀,用自己親身游覽的場景以及所見作為參考,把相關元素融合的創作式半寫實構成,中國畫由此意味著要求作者不僅僅是描繪出客觀物體的形態,更要有自己內心的感悟,如李合歡所說:“散點透視和遠近游目的方式在中國畫山水畫中可以大觀小,在花鳥畫中可以小觀大。”
二、國畫構圖美學特征
(一)書畫一體
中國畫區別于大多數其他畫種,是一種有著深厚文化韻味的獨特畫種。其最鮮明的特征是其書畫一體的特殊形式。中國繪畫藝術的書畫統一性上并不是自中國繪畫產生就存在的,書畫一體的特性自元代以后才逐漸形成。中國書法作為一種獨立藝術載體,一般以題詩、落款、收藏書體為主,書法所占畫面的位置也并非隨意書寫,而是一種與畫面的其他對象相互地呼應、協調、密不可分的一種繪畫元素。
(二)注重留白與意境
中國繪畫講究留白,李合歡曾在《試論中國畫的構圖和意境中》中闡述:“即空白的部位要像有畫面的部位一樣做認真的推敲和處理,使得虛處與實處相映成趣,達到‘虛實相生,無曲處皆成妙境’的效果。”
畫面留白構圖不僅是一種視覺的體驗,更多的有一種無形的、超越感官的精神上的感受。可以把畫面的黑白構成抽象為一種韻律節奏,黑白相間代表了韻律的強弱,黑白的分布構成可以想象成節奏的快慢位置,節奏和韻律快而復雜的地方則能體現作者想表達的關鍵位置。
(三)取勢
中國思想文化內斂含蓄的特點造就了很多文學作品的暗示鋪墊風格,這種文化現象必然會對繪畫產生影響,其中欲揚先抑等思想體現在畫面中就是欲左先右、欲上先下等構圖方式,這是淺顯化的易于理解的中國畫取勢思想。其中國畫取勢奧妙之處更甚,打比喻來說,如果作者想畫一個從畫面左到右方向的樹枝,作者不會直直地讓樹枝延伸到畫面右邊,而是讓樹枝向左邊的一個方向的趨勢,然后慢慢向右邊,這樣的方法會讓樹木更有精神,更加有力量,這就是簡單的“勢”的理解。
另外一方面,中國畫自產生文人畫開始,就有了對于畫面主觀性再創造的意識。中國畫講究在繪畫的同時,表達文人趣味在其中。這種主觀構圖的方式在下文分析《桃源仙境圖》會詳細說明。
(四)高遠深遠平遠
宋朝的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提出觀點:“山有三遠:自山下而仰山巔謂之高遠;自山前而窺山后謂之深遠;自近山而望遠山謂之平遠。”三遠代表了作者郭熙對山水畫構圖意境的三個分類;從山下看山頂,這樣的觀察山脈山勢雄偉,高聳入云,稱之為高遠。如與觀察的山取平視角度,則是由近山延展到遠山,一望無際,謂之深遠。如果觀察角度變為整體觀察對象山脈,以游代觀,則可以看出山脈的整體走勢,謂之平遠。
三、《桃源仙境圖》構圖以及意境分析
(一)構成布局
《桃源仙境圖》是一副175×66.7厘米的豎幅構圖的小青綠,其畫面面積中占比最大的是山體。整體觀察這張山水畫構圖可大體分為三大部分,下部分人物聚集的為近景,中間的亭臺樓閣和山為中景,遠處層巒疊嶂的高山為遠景。作者巧妙地將難以表現的“高遠”韻味在構圖上區分為三大部分,大膽地平分這三個層次又各有微妙的變化;當目光游離在這張畫面的云層和背景時,云層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部分;處于近景和中景部分的云和中景遠景間的云一大一小,相互呼應且起到了兩個大作用:1.巧妙地區分遠景中近、近景這三大層次。2.引導人們的第二視線;畫面上方的面積里,作者區分于下方的精巧布局構圖方式,大膽地采用了大面積的區分,大面積的云和大面積的山形成強烈的視覺沖擊,更加大了山云繚繞,巍峨壯觀的視覺沖擊感。
(二)計白當黑
如果把這張小青綠的山水人物當作是實景,云霧背景河流看作是虛景,則更能體會作者安排構圖之巧妙精細,若用簡單的黑中有白,白中有黑則有些淺顯。若把實景和虛景對換之后仍然可以發現;實景虛景在統一之中兼顧變化,作者并不是一心只去安排山水樹木的主體的外形,而是在將山水當作實景的同時又顧及到云霧的形狀,在云霧作為虛景的同時又有嚴謹的外形安排。這張《桃源仙境圖》若虛景實景對調,將還是一張優秀的作品,在品味其中的黑白虛實的同時就能品味其中的魅力。
(三)構成元素
云和山水的構成安排在這里就不再贅述,接著把目光聚焦到云和山石到構成裝飾韻味上;三大部分的實景山水為統一的構成元素,但仔細品味,遠景、中景和近景的山水線條走向卻大有不同,在見到的大部分山水畫中很少能注意到這種韻味變化。遠景的山石走向大體為豎向,線條多為筆直向下,與云層的橫向走向區分明顯又互相襯托,而遠景在整體為豎向走線的同時穿插著斜向的山脈,這里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斜向山不僅起到了統一變化的作用,而且還引出了下面的反方向斜山,也就是中景的左上右下方向走線的山脈,與遠景相同,中景的山脈大體為左上右下走向的同時,也穿插著橫向的山脈與云層、近景山體呼應。看似簡單的布局實則一環扣一環。當分析近景的時候,更能體會其中的奧妙,近景不僅僅是一個視覺第一安排,而且起到了以小見大的功能,下方的近景包圍式的山體安排,與整幅作品遼闊寬廣的意境相反,這樣的對比手法在歷史上都是罕見的。雖然不知道這樣的布局是否為仇英刻意安排,但其起到的作用卻不可忽視。正因為近景的包圍式的山體的收斂含蓄與整幅的寬廣形成的對比,使得其寬廣更遼闊,內斂更含蓄,實在是讓人欽佩其構圖運景的巧妙。
(四)點景安排
中國畫的構圖同時追求畫面的和諧平衡性。若把畫面上下隔開,會發現雖然人物由近景、中景、遠景依次減少,但畫面重心卻不顯得偏下,這歸功于作者仇英巧妙地安排了其他點景來平衡畫面。下方作者大膽地采用亮白色處理人物的衣服,顯得格外吸引眼球,為了平衡這一點,作者在畫面上方云間加入了亭臺樓閣來平衡畫面,畫面很多地方即相互聯系又各自獨立,畫面多一個點景便多,少一個點景便會少,可以說一筆不可多一筆不可少,讓人無法不驚訝于其點景安排的巧妙。
(五)意境淺析
綜合上述四點,可以試著去猜想作者仇英想要表達的意境。首先,作者精心安排了一幅非常和諧的畫面,畫面下方為文人騷客對琴暢談的場景,下方有兩位侍仆或者是童子在服侍這三位騷客。可以發現非常矛盾的一點,自遠景開始,上面的景色中所包含人物的描繪是與近景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上方構圖描繪的人物由下向上分別是拿著行李的農民形象、兩位牽著騾子戴著帽子的人物、一位亭臺樓閣里的詩人。可以明確地發現人物描繪的變化。由鄉村穿著風格走向市井穿著風格,這明顯與下方的人物顯得格格不入。而再看近景文人騷客的背后有著包圍式的山石,上述的一切讓人不由聯想到《桃花源記》,原文為:“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中的這個“從口入”的“口”是否可能就是這個包圍式的山石結構所表現的口呢?作者仇英也許繪畫的內容是帶有故事性的一幅山水,近景表現為真實的存在的場景,描繪文人騷客的暢聊時刻。自中景至遠景開始,便是他們幾個騷客想象的或者說是仇英想象的桃花源記的場景。這種虛實的對比,作者仇英是為了表達什么呢?據文獻記載,仇英處在的明朝時期是一個封建專制嚴重的時代,文字獄、八股取士等文化固化嚴重,而仇英(1498—約1552)正是生活在這一時代背景里,據出土的文物以及史料推斷,仇英出身寒門,幼年失學,原本追隨父輩學習漆畫并以此為生,經過不懈地對藝術的追求,后來才成為明四家,但卻處于文化藝術的黑暗時代,也許仇英是不滿于當時社會的藝術氛圍,繪《桃源仙境圖》來表達自己向往的自由祥和、開放的國度。整幅作品到處充滿浪漫色彩,又不乏對畫面平衡的處理,讓人看到后心情祥和,向往自由,仿佛神游于桃源仙境一般。
參考文獻:
[1]李合歡.試論中國畫的構圖和意境[J].美與時代(中),2019,(10):15-16.
[2]張夢遙.“計白當黑”構圖形式的演變與審美內涵[J].阜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01):150-156.
[3]于皓.仇英青綠山水的摹古與創新[J].美與時代(中),2021,(02):44-45.
[4]陳明莎.仇英《桃源仙境圖》賞析[J].收藏與投資,2021,12,(06):7-9.
[5]李培宇.構成元素在中國畫構圖中的應用[J].流行色,2020,(06):109-110.
[6]李合歡.試論中國畫的構圖和意境[J].美與時代(中),2019,(10):15-16.
[7]朱振華.淺談中國畫的構圖[J].美術教育研究,2017,(1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