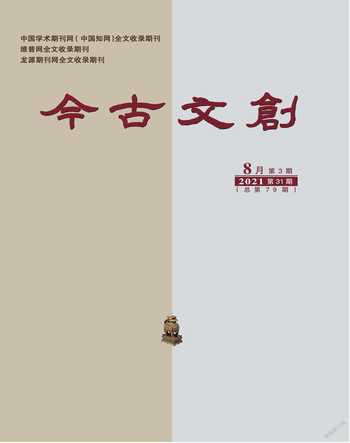語言規劃研究概述
【摘要】 本文概述了語言規劃的概念和定義,回顧了語言規劃的早期發展、研究理論和成果,梳理了語言規劃的研究內容和對象,列舉了語言規劃的研究目標、任務及研究方法,最后討論了語言規劃未來的發展趨勢和研究方向。
【關鍵詞】 語言規劃;概述;研究內容;研究方法
【中圖分類號】H002?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31-0121-03
一、概念與定義
對于語言規劃的概念和定義學界有眾多說法,比較權威的說法是這一概念(language planning)是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語言學家Uriel Weinreich 最早提出。后來該領域的研究者開始使用這一概念并展開深入地研究,為語言規劃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理論基礎,如著名語言學家Haugen教授。實際上不同國家的語言學家一直從不同角度和層面上對語言規劃展開各種研究。
我國語言學家李宇明2010年在其《中國語言規劃續論》中提出語言規劃是政府或學術權威機構為特定目的對社會語言生活(language situation)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干預、調整和管理。從以上定義中可以看出語言規劃都是未來導向的,也就是說語言規劃的政策和策略必須在干預結果產生之前明確下來。他認為語言規劃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語言地位的規劃;另一種是語言文體的規劃(language corpus planning)。其中語言地位規劃的主要目的是確定語言、文字及其變體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不同場合所應該使用的語言;而語言文本規劃的目的則是對現有語言、文字進行完善、規范和改革,以及對沒有文字的語言進行文字創制和對沒有發音的語言或文字進行注音方案的設計等。
二、早期發展及研究流派
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起源于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此階段,被西方國家長期殖民奴役的一些亞非拉國家開始擺脫殖民者對他們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殖民,他們的國家急需重建,民族急需加強團結,社會形象急需重塑。語言作為一個國家或民族的象征,此時一種新的語言就代表著一個新的國家或新的民族。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阿爾及利亞、巴基斯坦、馬來西亞等國家都面臨著國家重建和民族團結的問題,如使用哪種語言作為該國的官方語言,學生應該學習哪種語言等等。由此看來,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是一種后殖民主義現象,有很強的后殖民主義色彩和政治色彩。
還有一些國家后來經歷了大革命和后獨立發展時期,如新加坡、印度、菲律賓等,這些國家決定沿用殖民者國家的語言,如英語,這樣的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意味著“新舊”政府過渡和行政管理和統治的連續性,特別是這些新興國家在國際化背景下需求融入國際社會時顯得很有幫助作用。這一時期的代表性學者有 Haugen、Fishman和Charles等,他們主要關注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
語言規劃對于解決這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很強的實用價值,因此很多學者和語言學家早期研究和關注的焦點主要集中在解決這些問題上,這一時期的代表性學者有 Haugen、Fishman和Charles等。他們在這個階段的研究為語言規劃的研究提出了最初的經典理論基礎,因此這一階段的研究被稱為新經典階段。新經典階段的語言規劃注重和強調個人的選擇,語言規劃者在實施語言規劃時考慮個人因素,以個人理性的自然選擇為出發點,因此這種研究方法也被認為是非歷史、非道德、非政治的。
與新經典階段相對應的是歷史結構主義階段。歷史結構主義注重的是語言的形式和結構而不是語言的社會意義和社會力量。與新經典階段不同,歷史結構主義認為在實施語言規劃時應注重社會歷史因素對語言的影響。這種研究方法考慮受語言規劃影響的語言使用群體之間的社會關系,并認為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所涉及的人都是有政治觀點和傾向的。歷史結構視角關注社會結構和階層,對語言規劃和政策實施對象的選擇加以限制。這種視角下的語言規劃和語言政策塑造人們的行為,比如權利、國家、主導支配權、社會結構(階層)在分析語言政策的時候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三、研究內容和研究對象
(一)研究內容
在現如今的社會發展背景下,語言規劃和語言研究的內容和對象也出現了新的轉變。這些轉變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從研究語言自身到研究語言應用和實踐的轉變。這是指語言規劃最初研究內容最早始于語言本身的研究,例如對語言的文字、注音等文體方面的改革、規范及完善等。這是將語言規劃放在語言學的框架內進行研究。后來語言規劃的研究逐步延伸到語言學以外的背景中研究,如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人類學等。
2.從研究語言規劃的宏觀背景到語言規劃的微觀背景。以往的研究是以國家宏觀層面為背景進行研究,這種研究關注的是政府自上而下的整體語言規劃行為。但隨著社會各個領域和層面的不斷發展,除了國家整體,語言規劃研究和關注的焦點也從國家整體轉向不同區域、群體、社區和組織等局部微觀領域轉變。這些局部微觀層面的語言規劃因社會各個層面的變化和演變呈現出復雜多變的特征,同時在具體語言規劃過程中語言規劃或語言政策的實施不一定是自上而下,甚至是自下而上,這一轉變不但使得語言規劃的內容上更加豐富多彩、涵蓋面更廣泛,也讓語言規劃能更好地服務以往不被人關注的微觀領域和少數群體。
3.語言規劃的領域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演變而演變。從20世紀60、70年代自上而下的國語或標準語言的推廣規劃需要,到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凸顯了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移民問題、政治經濟問題、文化交流問題、商務旅游等問題,語言規劃不斷隨著全球化的進程而快速演變,不斷有新的研究領域出現,這些都與語言的溝通、交流這一最基本功能屬性密不可分。除了上述早期關注和需要解決的國家構建問題以外,也開始轉向關注研究多語現象、少數民族語言問題、方言問題、行業語言問題、政治語言問題、語言教育等問題。
(二)研究對象
隨著語言規劃的研究不斷深入,語言規劃的研究對象日趨清晰明朗。有學者將語言規劃的研究對象歸納為語言關系的研究、語言態度的研究、語言制度的研究、語言群體的研究。
1.語言關系。語言關系是指不同語言之間存在語言機構特點和語言使用功能上的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的關系;語言關系也指不同民族之間由于社會、文化的相互接觸、影響而在語言上呈現出的種種關系。
2.語言態度。所謂語言態度是指社會大眾對某一種語言的語言地位、語言功能、未來演化等語言屬性的態度或看法。態度本身是一種心理上的主觀現象,但就語言態度而言它不僅是一種心理現象,更與語言所屬范圍內的政治、經濟、文化、民族、宗教等社會因素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因此語言規劃將社會大眾對語言的態度視為重要的研究對象之一。
3.語言制度。語言制度是指一套語言規則,但這種規則不是指語言本身的語言規則、語意規則或語法規則,也不是指一個人或一個階級在一定語境下運用語言的修辭規則和語用規則,而是指一個社會共同體用來安排各社會集團相互語言關系的規則。
4.語言群體。一個國家和一個社會內部存在著不同的群體,不同群體內部的語言和外部語言存在著很大差異,這樣就形成了不同的語言群體。對于一個語言群體來說,群體內部的語言具有相對的一致性。
四、目標和任務
(一)目標
語言規劃研究內容和研究對象的多樣性和演化性決定了語言規劃研究目標的多樣性,學界學者如Haugen(1983),MosheNahir(1984),Haarmann(1990),Kaplan和Baldauf Jr(1997,2003)等也曾對語言規劃的目標進行過一系列探討。其中Nahir(1984)根據案例分析將語言規劃的目標歸納為:語言凈化、語言復興、語言改革、語言標準化、語言傳播、詞典現代化、術語統一、語體簡化、語際溝通、語言維持、輔助語碼標準化。由此可以看出語言規劃的目標根據研究內容和研究對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它的目標不是單一的而是多重的。
(二)任務
1.提高全社會的語言交往效率。語言規劃必須著眼全國范圍內整體語言交際效率的提高,整合社會的語言資源,讓社會成員能夠充分地使用各種語言資源,從而獲得更大的語言資源使用效率。
2.提高語言的社會凝聚力。對于民族和國家來說,語言是民族團結、國家統一、社會凝集的基本條件之一。
3.提高本國語言的國際影響力。語言作為傳播溝通的媒介,是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經濟實力、國際影響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推動一國經濟、文化、教育、人文交流、外交、軍事等方面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五、研究方法
語言規劃的研究方法一開始主要采用經驗觀察法、歷史分析法等方法,但隨著社會科學的發展,各個學科和領域出現了新的科學研究方法,由于語言規劃是涉及眾多學科的交叉學科,如人類學、語言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眾多交叉學科,其研究非常復雜,因此不可能單獨采用一種或某幾種研究方法,在語言規劃不同的發展時期,具有不同的研究方法或是不同研究方法的融合。
正如上文所述,在語言規劃是后殖民主義的產物,語言規劃的目的與國家的建立,民族的團結和現代社會的形成密切相關,因此在此時期語言規劃主要采用語言學框架內的研究方法,如Haugen的四重模型(fourfold modle)和克洛斯的本體、地位概念(corpus\status),這為語言規劃的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和理論框架,并對語言規劃中的語言地位規劃、語言本體規劃和語言習得規劃做出了詳細的闡述劃分。
隨著社會的發展,語言問題的社會化現象日趨復雜,如雙語問題、多語問題成為社會關注和面臨的問題,因此研究學者開始使用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語言規劃。如古柏在《語言規劃與社會變化》(1989)提出的語言規劃研究方法,如語言習得規劃(acquisition planning)、語言規劃明細表(accounting scheme)和交互網絡(interaction networks)。這些研究方法的提出使得語言規劃的研究從宏觀到微觀層面的細化研究,這也是社會研究法的一個重要特征。此外,民族志研究法,歷史結構分析法和話語分析法等社會學研究法也常用來研究語言規劃的問題。
1972年豪根在《語言生態學》(the ecology of language)中提出了語言生態的觀點,認為語言具有自身的生命、意志和形式,可以視語言為一種人類的行為加以研究和分析。隨著語言多元化、民族多元化成為社會的熱點話題,研究者開始運用生態語言學研究方法來研究語言規劃。
六、結語
語言不僅僅是交際的工具,更是文化和身份的象征。解決語言交際問題不是語言規劃的唯一目標和任務。因此語言規劃的動機不是單一的,它的背后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民族等諸多因素的共同推動。就語言本身而言,語言是一個不斷發展,不斷完善的動態過程。展望未來,語言規劃的未來發展也將隨著世界的發展變化出現新的研究方向和領域,但不管社會和世界如何發展,語言規劃總是脫離不了社會這個大背景,而語言規劃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或促進社會中出現的這些熱點問題。除了這些宏觀熱點話題以外,少數族群語言社會地位、瀕危語言保護、特殊人群社會用語等局部微觀和少數群體的語言規劃問題也值得關注和研究。
參考文獻:
[1]A Zaidi.Language Planning:An overview[J].pakistaniaat a journal of pakistan studies,2013.
[2]鄔美麗.國外語言規劃研究述評[J].天津外國語大學學報,2012,(02):20-25.
[3]戴曼純.語言政策與語言規劃的學科性質[J].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2014,(06):5-15.
[4]黃曉蕾.20世紀語言規劃研究方法等流變[J].中國社會科學院學報,2014,(02):101-107.
[5]張天偉,吉布森·弗格森.語言政策與規劃的學科屬性及其發展趨勢[J].外語研究,2020,(03):1-4.
[6]姚亞平.中國語言規劃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7]李宇明.中國語言規劃續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
作者簡介:
董亞釗,男,漢族,河南南陽人,碩士研究生,武漢商學院外國語學院,研究方向:商務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