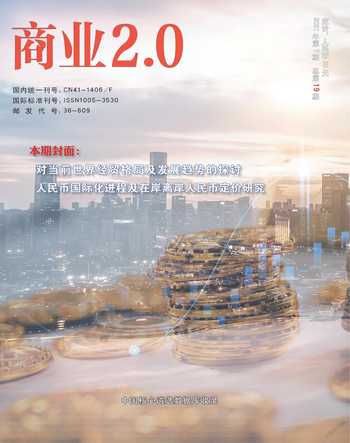民法典離婚家務勞動經濟補償制度完善的人權內涵
摘要:早在2001年,我國婚姻法就已經針對離婚經濟補償制度作出了一系列的規定,但從將近20多年的實踐中也可以看出,這一制度的實施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在應用的過程中遇到了多種多樣的問題和阻礙。新時期,民法典婚姻家庭編中也對這一制度作出了進一步的修改和完善,拓展了這一制度的適用范圍,帶來了十分積極的正面影響,能夠充分體現出民法典的人權價值。對此,本文也將以民法典離婚家務勞動經濟補償制度為切入點,分析這一制度完善的意義,并探討實踐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相應的意見和建議。
關鍵詞:民法典;離婚經濟補償;家務勞動;人權意義;應用問題;改革方法
通常意義上所說的離婚經濟補償制度,指的就是離婚家務勞動補償制度,正式出現在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中。彼時,婚姻法第40條就針對離婚經濟補償制度作出了規定,從具體的內容中可以看出,在書面夫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應當歸各自所有,如果其中有一方因撫育子女,照料老人等原因付出較多的,在雙方婚姻關系破裂時,也有權利向另一方請求補償,另一方也應當予以同意。以上這些也足以說明,離婚經濟補償制度也是順應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
一、分析民法典離婚經濟補償制度新規定的人權意義
相較于2001年的婚姻法來講,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第1088條,肯定了補償辦法由雙方協議的價值,如果雙方協議不成,則由人民法院進行判決,并且,這一條款也否定了,在書面約定夫妻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歸各自所有的合理性。
(一)進一步擴大制度的適用范圍
2001年的婚姻法,把離婚經濟補償制度的適用范圍限制在夫妻分別財產制上,這也與我國夫妻財產制的發展現狀存在明顯的輸入。婚姻法本身就強調,夫妻財產制是婚后所得共同制,婚后共財,也是中國社會傳統觀念積淀的產物。即便是在當下,采用分別財產制的國內夫妻數量依舊很少,案件受理占比并不突出。從實踐的角度來看,絕大部分家庭都不會針對婚后財產的所屬進行約定,即便是有所協商,也大多都是一部分共有部分分別為主,把完全分別財產制當作主線的家庭是少之又少的。這也就意味著,在過去,離婚經濟補償制度的適用,缺乏必要的環境和條件。在新時期,民法典婚姻家庭編把離婚經濟補償制度延伸到適用于夫妻共同財產制的領域內,這就打破了原有的條件限制和瓶頸,給予家務勞動以更為全面的肯定和認可,無論夫妻之間采用何種財產制度,只要一方付出的家務勞動占比較高,離婚時就有權請求另一方予以補償,這也更加適合于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
(二)凸顯出了對女性的救濟意義
從人的自然生理屬性來看,女性本身就具有生育和哺乳后代的天然能力,所以就現實的夫妻關系來講,女性會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操持家務,撫養子女。在結婚之后,無論婦女是否擁有自己的事業,都承擔著比男性更多的家務勞動,在照料子女和家人上也花費了更多的心力。并且,女性應當以家庭為主這一觀念,也是諸多社會家庭的共識。盡管,在觀念和意識形態調整的引導下,男性承擔家務勞動的比重也有所上升,但我國以女性作為家務勞動承擔主力軍的現狀,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并且,在女性承擔家務的時候,他們的配偶也并沒有發揮出輔助和引導作用,并沒有真正加入家務勞動的大軍,女性需要承擔著家庭和社會的雙重壓力。如果女性在家務勞動中花費了過多的時間,他們在工作中就不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這就必然會影響自身的職場發展和經濟收入。所以,民法典對離婚經濟補償制度作出的拓展,更加肯定了女性在家務勞動中的地位,能夠更好的平衡夫妻雙方之間的利益關系。民法典自身的施行,也讓承擔較多家務的廣大女性,有了價值認可的依據,他們也可以利用這一制度,對自身的權利進行救濟,有效處理離婚糾紛和沖突。
(三)推動家庭內部的和諧發展
家務勞動包含的內容是多種多樣的,涉及到日常生活的諸多方面,而且十分瑣碎繁雜,在部分人眼里,家務勞動可能只是一些細小的事情,但如果細想的事情得不到妥善的處理,在日積月累中也會變成巨大的矛盾。再加上,現代年輕夫妻的自我意識更加突出,容易在誰做家務這一問題上產生分歧和爭執,最終導致家庭不和睦,甚至是婚姻關系破裂。而且,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每個人的經歷是相對有限的,如果只是夫妻的其中一方從事反復多樣的家務勞動,另一方卻不聞不問,那就必然會破壞夫妻間權利義務的平衡,容易導致家務勞動方產生極大的怨氣和不滿,最終導致雙方的沖突。在這里,離婚經濟補償制度的延伸拓展,有助于推動夫妻雙方家務勞動觀念的調整,激發出男方主動承擔家務勞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讓男女共同分擔家務的理念,得到進一步的推廣。同時,這一制度也可以讓另一方對家務勞動負擔方產生心理上的體恤,從而實行勞動上的助力,提高婚姻家庭的和諧度,增強生活的幸福感。
二、分析離婚經濟補償制度在司法適用中存在的難點
首先,當事人的舉證是相對困難的。我國民事訴訟向來強調,誰主張誰舉證,離婚經濟補償制度也自然不會例外。如果夫妻其中一方有離婚經濟補償的請求,那么他們就應當提供證據證明自己承擔較多的義務,如果不能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就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然而,相較于其他類型的勞動來講,家務勞動的痕跡要更加隱蔽,很多都是屬于關起門之后的事情,不易為他人所知曉,大多都局限在家庭內部,具體承擔的數量只有夫妻雙方心里最為清楚。再加上,現代化社會的發展,讓群眾的隱私意識逐漸增強,即便是鄰里之間也不一定熟識,也更談不上去關心別人家庭的內部生活,家務勞動不可能保證自己的付出能夠為外人所知曉,也不可能把一切勞動過程都用政治的形式保存下來。再加上,夫妻一方在承擔家務勞動的過程中,往往都飽含對婚姻的期待和熱忱,所以他們主動收集證據的意識也相對薄弱。
其次,補償標準不夠明晰。當下,與離婚經濟補償制度適用有關的標準是相對稀缺的,這就進一步阻礙了這一制度的司法適用。就具體的實踐來看,如何界定一方負擔較多義務?多少才是真正的較多?補償時應當按照何種標準來進行?補償金額的確定需要參考哪些因素?家務勞動的價值應當用何種辦法來衡量?家務勞動中的感情投入又當如何評價?以上這些都會給司法適用帶來明顯的困難,法官在裁判的過程中也缺乏準確的參考依據,擁有巨大的彈性空間。這一缺陷的存在,也會讓一些當事人投機取巧,導致另一方付出的家務勞動在價值上被抹殺,這就與制度拓展的初衷存在明顯的出入。
三、分析離婚經濟補償制度司法適用的方法
(一)推動舉證責任的均衡分配
司法實踐必須要著眼于離婚經濟補償制度的適用核心,重點解決當事人在舉證時面臨的難題。例如,如果夫妻雙方感情不和,而且也處于分居狀態,或者是另一方長期在外地工作,另一方單獨留在家中照顧子女和長輩,那么法院就應當讓當事人收集初步證據,結合當事人的陳述,支持當事人提出的離婚經濟補償請求。如果夫妻雙方處于共同生活的狀態,那么這種情況下的舉證就會更加困難,在這里,法院就可以適用蓋然性占優勢這一證明標準,只要訴訟中的一方提供的證據,比另一方提供的證據更有說服力,那么就應當判定,該方在數據數量和質量上更有優勢,至于證據的精確性不應當多做要求[1]。如果訴訟雙方當事人舉出了完全相反的證據,而且兩者的證據均不足以否定對方的證據的時候,法院就可以結合日常的生活經驗,若是能夠確定提出經濟補償請求方的主張存在高度可能性,那么就應當予以認可和肯定。除此之外,如果當事人針對案件事實確實難以舉證,并且這種情況會影響案件的審理進程的,法院也可以依職權向有關單位進行調查,或者是通過基層走訪收集更多的信息。
(二)履行基本的解釋和告知義務
雖然國民的法律意識在近些年來有了普遍的提升,但仍舊有部分當事人的法律知識相對缺乏,法律素質依舊,存在明顯的不足。就離婚案件處理來講,許多當事人并沒有請律師,自身的文化水平也不高,在這種情況下,要想讓他們完全理解專業法律術語,明確自身的權利和義務就顯得十分困難。對此,法官在調解案件的時候,也必須要履行自身的解釋和告知義務,要讓當事人能夠大致了解離婚經濟補償制度的內容。而且,法官也要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為當事人解釋相關的法律規定和法律術語,引導當事人進一步收集并補充證據。除了案件當事人之外,法官也可以向當事人的親朋好友了解基本情況,對親朋好友作出法律的解釋,這樣也可以進一步發揮出制度的教育作用。
(三)明確補償數額的參考依據
筆者在上文中已經提到過,離婚經濟補償制度在適用的過程中缺乏明確的參考標準,補償數額的確定是相對困難的[2]。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法律就可以充分參照先進國家的有益經驗和教訓。例如,德國民法典就強調,在離婚案件審理時,法官應當考慮婚姻存續的時長,以及因從事家務勞動而導致的學業或者是工作延遲情況,考慮到當事人具體的職業。而就中國來講,法院在確定補償數額時,應當堅持權利和義務相一致的原則,要認真分析夫妻一方投入家務勞動的時間和強度,總結另一方在婚姻期間獲得利益的大小,分析是否生育子女或者是生育子女的數量,離婚之后雙方各自的謀生能力等等。在夫妻共同財產制的引導下,離婚經濟補償數額的確定也需要也需要與共同財產的分割情況相聯系。如果法院再進行具體分割處理的時候,已經考慮了承擔家務較多一方的利益,那么在計算離婚經濟補償數額時,就可以酌情降低,這樣也可以平衡離婚之后的利益。也就是說,法院必須要靈活發揮自身的自由裁量權,充分考慮社會政策,倫理道德,和群眾的價值取向等因素。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民法典離婚經濟家務勞動補償制度的完善凸顯出了我國法律的人權功能和價值,能夠穩定社會經濟秩序,但在未來實踐的過程中依舊需要解決一些問題。本文通過舉證責任的均衡分配,釋明和告知義務的履行,補償數額的多元素考量,這三個角度,論述了民法典離婚經濟交流中補償制度的適用方法,充分結合了我國婚姻家庭的基本現狀,具有理論上的合理性與實踐上的可行性,能夠作為從業人員的參考依據。
參考文獻:
[1]夏吟蘭.民法典離婚家務勞動經濟補償制度完善的人權內涵[J].人權研究,2020(2).
[2]劉若菲.離婚案件中人力資本經濟補償問題研究[D]. 華僑大學,2020.
作者簡介:李源源(1979.9-),女,漢族,河南省鄭州市,研究生,河南檢察職業學院,講師。研究方向:民商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