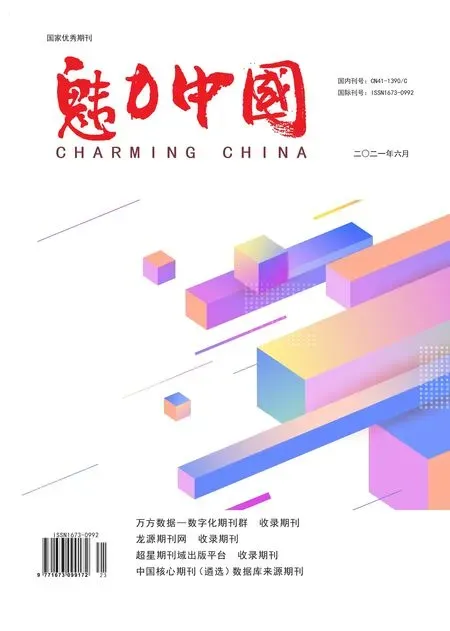品亞歷山大·考爾德的藝術作品
鐘霖 郭諶濤
(華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1)
哲學家薩特在考爾德的作品中窺見了某種生命的狀態,說到“它們以空氣為能源從而得以呼吸,并從大氣層稀薄的生氣之中獲得自己的生命,因而,它們的運動就有著超出一般運動的性質。”
在20 世紀前的傳統雕塑無論是具象的還是抽象的都是靜止不動的,而考爾德打破這一單一局面創造了雕塑的四維空間“時間”的“活動雕塑”。活動雕塑的出現突破了原有呆板的雕塑形式,而這種對雕塑的新的理解可能來自他的家庭世族的影響,也來自他興趣愛好的影響。

人生經歷與創作靈感
考爾德出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未來主義和反現實主義時期的世界,由于考爾德的父親和祖父都是雕塑家出身,考爾德也在雕塑的熏陶下成長。7 歲時開始,已經展現了他在工具方面非凡的能力,小考爾德在幼年時期經常會給姐姐做一些首飾品,并不是單純的珍珠手鏈,更多的是首飾上的創意。
1922 年,他到紐約去學習繪畫。第二年就加入了美國”垃圾箱”畫派領導下的藝術學生聯合會。恰巧未來主義是當時整個美國藝術的熱潮,未來主義宣言表述“透明的玻璃板,金屬板,電線,室內外的電燈,就能夠表現平面,方向和一個新現的半明半暗調子。”[1]
此刻,他的雕塑作品就如按照未來主義所闡述那樣,例如他的其中一幅作品《蝦籠子與活動魚尾》,起初的考爾德總會在一些極其不起眼的,甚至是廢舊雜物中去獲得靈感。采用鐵絲,木塊,破碎骨片,鋁和錫等材料組合,讓作品中的鋼絲和鋁板遇到風時,隨著空氣活動,這個“蝦籠子”就會自行變動位置和形狀,相互碰撞的鋁片發出清脆悅耳的聲音,讓觀賞者誤認為是魚兒游在水中。

這種新形勢的活動雕塑正是采用利用機械的驅動力或空氣的流動等為媒介和材料自身的特殊性使作品具有視覺變化的藝術魅力。同樣因為材料的特殊屬性,作品還可以通過產生不同的音效,讓觀眾沉醉在這視聽盛宴里面。
“動態雕塑”
“為什么所有的藝術都必須是靜止的,雕塑的下一步是會動的”。
——亞歷山大·考爾德
到底什么是運動?在不同的事物或是活動中的“運動”似乎不盡相同但又差不多。我們可以用米老鼠在動畫片中跳舞,它的引擎是動漫科技;舞蹈演員更是可以將旋轉跳躍直接展示在舞臺上,它的引擎就是人體本身;同樣,考爾德的《馬戲團》也表演了一種運動狀態,雖然他的引擎是馬達,它的活動重復,機械而缺少偶然性。[2]

考爾德的“活動雕塑”有的是矗立者的,有的是懸在天花板上,這種可以活動的雕塑沒有具體的擺放方式,可能是為了呈現出一種生物形態的美,也可以是為了使觀賞者產生各種聯想,觀者在運動中的雕塑捕捉視象,讓在展覽中能夠身臨其境的體驗藝術。考爾德運用雕塑隨著氣流變化不斷變化,發出清脆的聲音如清風吹動的樹葉一樣輕輕抖動,讓人沉浸在視覺藝術樂趣之中又能體會到聽覺盛宴。這些與現代公共環境融為一體的藝術品,為凝固的建筑幾何空間增添了一種新的藝術形式。
就好比說考爾德的《鋁葉子》《紅花瓣》作品中,大量地運用鐵絲,鐵葉子,通過焊接的技術來創作,作品也會隨著氣流的不同來展現本是穩定雕塑存在的不同面貌。感覺這種氣流正是考爾德作品“動”的引擎,而他部件的顏色基本上采用三原色來表達,也體現了作品中原本屬于自然的那一部分。
“靜態雕塑”
考爾德“活動雕塑”的相反一面就是他的“靜態雕塑”可能起初有所不解,明明動態雕塑做的挺好的為什么又去做靜態雕塑,或許有著他自己的意義吧。
亞歷山大?考爾德最讓人熟知的作品是《紅鶴》(又稱為火烈鳥)。作品坐落于芝加哥聯邦政府中心廣場上的純紅色巨型雕塑。它們龐大的身軀,仿佛是遠古的動物,又像是鋼鐵的怪獸,顯示出極強的生命活力和激烈的動感,令人精神振奮,展現出雄性的美感,是巨大城市空間中的現代圖騰。這副用鋼板焊接而成的作品高達15.9 米,人們可以在作品下自由自在地穿行,可以算是作品中的流動感。在整個雕塑中考爾德沒有運用直線的剛性來體現雕塑的穩定性,而是借助于斜線和弧線的運動線形來展現形體的空靈感,與廣場周圍的立柱建筑形成鮮明對比,這樣的雕塑與周圍環境形成對比的同時,更像是美國幽默文化的體現。[3]

考爾德的大型公共藝術雕塑作品還有肯尼迪國際機場的".125"、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螺旋"、1967 年蒙特利爾世界博覽會的"人"等等。我認為這樣的大型雕塑作品,不單單為的是成為一種城打破市四四方方建筑的藝術裝飾品,也不僅僅是在所有灰色調調的鋼筋水泥的跳脫的極純三原色,而是想讓人們在這雕塑作品旁邊流動經過時,去發現靜態中的動態感。
到底亞歷山大·考爾德能帶給我們什么?我覺得不僅僅是活動的靜止的雕塑藝術品,而是一種當代藝術下的一種創新和突破陳規,發現新的事物。